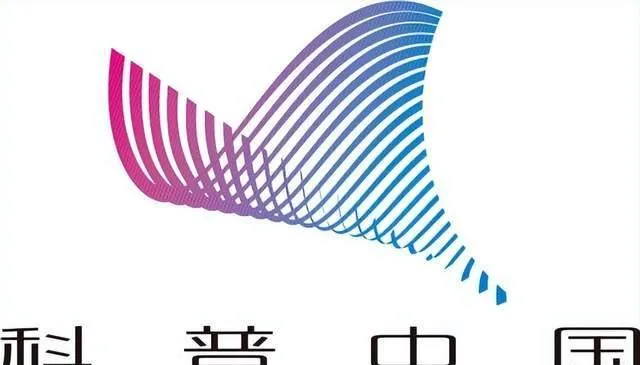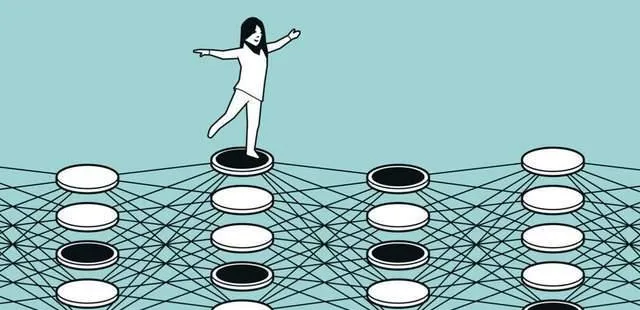
10月8日,202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非常出人意料地頒發給美國科學家John J. Hopfield和有「神經網絡之父」之稱的加拿大科學家 Geoffrey E. Hinton,表彰他們「透過人工神經網絡實作機器學習的基礎性發現和發明」。獎項公布後,物理學和神經網絡的關系成為人們關註和討論的焦點。
本文是Hopfield的人生自述,原題為【在科學中成長】,節選自【成為科學家的100個理由】。Hopfield在12歲之前沒有學過任何科學過程,但他自幼成長在一個鼓勵他自由探索的家庭,中學裏遇到了優秀的科學教師,從此自由徜徉在科學之海。
【成為科學家的100個理由】是一本近百位世界著名科學家(其中諾貝爾獎得主30位)暢談人生的文集。他們講述自己成長的經歷,傾吐對科學、對知識的熱愛與追求,也向年輕一代道出了殷切的期盼。從收錄的近百篇文章能夠領略他們睿智的科學見解,品味他們多角度的人生心得,還可一瞥他們平凡而又充實的生活。
本書現已絕版,【成為科學家的100個理由(20周年紀念版)】近期將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撰文 | John Hopfield
兒童天性好奇。他會戳戳甲蟲看它們的反應,扔根樹枝在小河中觀察它漂多遠才沈沒;他喜歡拆開玩具看個究竟,也會對水流進排水溝便不見蹤影感到驚奇。我生長在一個不但寬容、而且鼓勵孩子大膽探索的家庭,所能記得的最早活動是在廚房的地板上玩鍋蓋,把它們上面沒有擰緊的部份全都卸下來。在我心目中,父親能修好一切東西——屋頂、收音機、水管、電線、單車,也能給鋼琴調音和幹園藝活。孩提時代,只要父親做這些事情,我就會守在旁邊看。父親也會向我講解問題可能出在哪裏,如何才能修好。母親有一台老式「歌手牌」縫紉機,小抽屜裏放了一把調整機器用的螺絲刀。母親允許我用它,只要擺弄完之後放回去就行了。我用它到處鼓搗,自得其樂。很多年後,母親給我講了當時的一件趣事。一位到我家給妹妹看病的醫生一進門,就看見我正把一台帶手柄的老式留聲機拆得七零八落,他立刻出聲制止我。聽到醫生的聲音,母親毫不在意地對他說:「沒關系,要是他裝不回去的話,他爸爸會幫他的!」一句話,當時我在家裏很少受到嚴格的管束,甚至有些「膽大妄為」。至今我還記得,那真是一把漂亮的螺絲刀!另一件讓我著迷的工具是放大鏡,我用它觀察螞蟻,或者把陽光聚焦在紙上燒孔。
稍後,母親開始鼓勵我在廚房裏做化學實驗。我得到了幾個試管、軟木塞,以及兒童化學實驗指南。這些書教孩子們如何用舊電池的鋅皮制作氫氣,如何讓醋和發酵粉在試管中反應而射出軟木塞。書中還描述了硫被加熱熔化後表現出不同的性質,氫氣用火柴點燃時應當發出「嘭」的聲音。我制成的晶體總不如書上看到的那麽漂亮,但晶體的對稱結構還是清楚的。透過動手制作,我還明白了它們的成因。無影墨水是我能在廚房中制造的另一種奇妙東西。與大多數學生初次見到酸性試劑是在化學實驗室不同,父親用紅色洋白菜作試劑,向我展示了它如何隨著溶液酸度的不同而變紅或變藍。
我的電氣設計開始於一對電池、幾根導線和幾個燈泡,印象最深的是在一把釘子上纏繞電線做成電磁鐵,以及自制可在臥室和廚房之間傳遞訊號的簡易電報機。
後來,還改造過結構式套裝玩具。與發明創造的雄心相比,笨拙的手指時常令我感到力不從心,而且手頭可資利用的廢舊零部件也太少。有一次,我找到了一副老式的頭戴耳機,以及一本美國農業部編制的【簡易晶體管收音機制作手冊】。根據手冊,我用頭戴耳機、一塊方鉛礦石 (硫化鉛) 和在紙板筒上繞成的線圈自制了一台收音機。它可以接收遠至75公裏發射台的訊號,而且不需要電池。該手冊發表於1930年,用以指導尚未通電地區的農民制作簡易收音機,以便在農村收聽無線電廣播。後來,我得知單真空管收音機可以收到更遠距離的訊號,於是用零花錢買來真空管,組裝了「更高級」的收音機。可以說,我是在親手制作、改進和維修簡易電子裝置的過程中,了解電子學和掌握其基本原理的。而且,大多數制作只是修舊利廢,花錢其實很少。晶體管收音機最令我著迷的地方是,一些與方鉛礦石晶體相連的電線,竟能將無線電訊號整流為可聽到的聲音。這個問題直到12年後我上了大學才真正弄清楚。
一輛單車也能提供學習的好機會。輪輻斷了、腳剎車無法再調整了,沒關系,我拆開修理修理。裝不回去了,父親總會救我,他會帶我到修車店去。當然,可不是去請人修理——那「太奢侈了」,只是去學點技術和買些必要的零件,回來繼續自己修。
我還用一套組合工具自制過模型飛機。先是做橡筋彈射飛機,後來又把微型汽油發動機裝上了模型飛機。我從改裝中學到了不少東西,後來甚至在修理我得到的第一輛舊汽車時派上了用場。我喜歡閱讀雜誌的科學欄目。偶然讀到一本關於天文學的書,便夢想著能夠作出解釋宇宙執行的科學發現。
在中學接受的科學教育非常糟糕,完全是照本宣科,為教而教。我12歲之前沒有學過任何科學課程。之後的科學教育,老師們強調的只是記憶現成知識,而不帶領我們去實際動手,加深理解。我的這些科目成績都很差。幸運的是,我遇到了兩位真正優秀的老師。一位是生物老師,另一位是化學老師。生物老師要求我們註意事實的組織,而不是死記硬背無關聯的內容。他鼓勵我們尋求生物體之間的聯系,教導學生如何觀察和思考。應當說,這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科學的魅力。高中化學老師則將我們這些十幾歲的學生當作成年人,為我們開設真正的科學講座,指導我們像搞科研那樣做實驗。跟著這些老師,我做了許多兒時在書本上讀到、並一直期盼著能親自動手完成的實驗。猛然間,我成了班上最好的學生。
物理學是探索未知事物及其成因的學科,它尋求關於世界的基本原理、事實和定量描述。一些人沈醉於探究宇宙起源的奧秘,或者極微觀事物的性質。我是在一個對周圍世界充滿好奇的環境裏長大的,所以熱切地想理解和影響自然。最有意思的物理學莫過於按人的尺度去關註事物的性質,並在更微觀的層面上探索事物的結構與內容。
依據上述背景,我進大學後很自然會主修凝聚態物理。我科學生涯的第一個十年,主要研究結晶固體的光相互作用,及其與固體的電子結構和光的量子特性之間的聯系。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許多領域還是完全未開墾的處女地,相關的實驗一個接著一個完成,新的理論很快便能得到驗證。我由此獲得了極好的基礎訓練,特別是在廣泛運用數學模型方面。
隨著對固體物理的理解加深,我轉向了以物理術語描述生態系的研究。事實上,當時這又是一個幾乎無人涉足的領域。漸漸地,建立於物理學之上的關於生命系統的實驗事實多了起來。我以一種不同尋常的提問方式,為此新興學科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我本人也以理論生物物理學研究而引人註目。不過,該領域最重要思想之數學意蘊尚有待進一步闡釋和挖掘。我所做的只是找出其中相對簡單的問題,清楚地加以表達和陳述,並采用便於理解及物理觀察的方式來描述可能的解決路徑。
我發表的首篇關於大腦工作機制的文章,後來成為參照率極高的論文。透過對相互聯結的神經元網絡行為作物理類別的抽象,而將磁性和自旋玻璃這一著名物理主題與聯想記憶心理現象聯系了起來。由此,在神經生物學中引入了計算的概念,並借助於趨向某一不動點的多自由度系統的動態軌跡來進行計算。上述思想如今被稱作「霍普菲爾德模型」 (Hopfield model) ,它已激發了許多物理學家進入神經生物學領域。研究者們的工作表明,神經生物學與物理學關系極為密切,相關的物理模型可以有效地遷移至神經生物學的研究。兩年間,我在參加了多種神經生物學研討會後,把握住了關鍵問題。我在分子生物學領域得到最多參照的論文,涉及「動態校對」,後者是在分子水平上一般通用的校對方法。同時我還率先提出了tRNA和蛋白質合成中的動態校對控制機制。在此,我又提出了一個正確的問題。生物學家可能會問:預期的反應是如何發生的?而我則這樣問:在預期反應與非預期反應非常相似的情況下,為什麽「非預期的」和「不想要的」反應不會發生?由此發現了新的生物物理規則。
我現在的科學興趣轉向了探討「我們人類如何思考」的問題,這是我常用的提問方式。不過歲月不饒人,我恐怕很難圓滿解答以上疑問了。也許有人會說,那是生物學問題還是物理學問題?我想,如此區分其實並無太大意義。就實際研究而言,不妨將物理學定義為「接受物理學訓練者的所作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