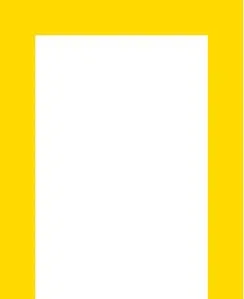
地球是一個奇跡
物種|雲南

美國養蜂人Katie和柯公河谷的傈僳族、藏族人一起養中華蜜蜂,在當地獨特的自然生態裏,他們對蜜蜂的關心正在創造一個個小的奇跡。|國家地理圖片集
午後松林裏,蟬鳴、蜂群和風吹動樹葉的聲音交織在一起。蜂農和國慶正在檢視巢框,要從密密麻麻的蜜蜂中找出蜂王。他突然停下來,深吸一口氣,為了緩解疼痛,他把手指沒進蜂箱防雨板的凹槽,那裏蓄了一點上午的雨水。
養中華蜜蜂被蟄是常事,他通常只是看一眼傷口,在衣服上蹭一下就接著幹活,這次有一點不同,他被蟄到指甲縫了。
當初決定養蜜蜂時,他已經準備好接受被蟄的疼痛。畢竟和蜜蜂所失去的比起來,這種疼痛微乎其微。後來,他發現自己的身體可以慢慢適應蜂毒——起初,手背、手指、臉部被蟄後都會腫好幾天,現在,傷口發腫的情況已經很少出現。
十幾年來,他的疼痛經驗是: 一方面,疼痛程度常常取決於被蟄部位,指甲縫就是最難受的部位之一。 另一方面,在柯公山谷裏,高海拔的中華蜜蜂比低海拔的中華蜜蜂更容易蜇人,他猜這是因為前者更少接觸人類。
讓身體適應疼痛是養中華蜜蜂的第一步。 柯公河谷裏的傈僳族養蜂人在小時候就邁過了這一步。他們住的地方海拔高、耕地少,據說一百多年前,他們的先輩最初抵達這個山谷時就已經在養蜂了。無論是抓野蜂、查蜂箱,或者取蜜,他們從來不戴防蜂手套。
和國慶的這一步比他的傈僳族朋友都晚。他生於一個鮮少養蜂的藏族村子,但從小喜歡和傈僳族朋友去山裏玩,因此能把傈僳語說得和藏語一樣好。
他也從小喜歡吃蜂蜜,但因為怕疼,從沒考慮過養蜂。作為一名木匠,他曾走遍香格裏拉周邊的寺廟,打造藏式木房,或在家具上刻花紋,畫絢麗的圖案。
和國慶養蜂,是Katie走進這片山谷之後的事。後來和Katie去美國的集中養蜂場,他發現西方蜜蜂個頭比中華蜜蜂大,但個個都像寵物一樣,溫順,不蜇人。
「我最初就是很好奇一個外國人能在這兒怎麽養蜂,所以經常去看。然後覺得這件事我也可以做。」和國慶說。結果他一養蜂就養了十幾年,和Katie也從最初的朋友、工作夥伴變成了夫妻。

在美國養蜂世家長大的 Katie自小跟隨家人南北輾轉,學習和適應力極強。在與和國慶結婚後,她每次回到村裏都參與家裏的農活。這片剛剛收獲完青稞的地裏準備種植玉米,Katie就在國慶的指導下用手扶拖拉機翻整土地。 |攝影: 孫曉東,國家地理圖片集

5月是當地植物的大流蜜期,在美國讀博士的Katie回到雲南維西的家裏。公公婆婆會給她做她最喜歡吃的木瓜雞,這也是當地一道傳統美食。|攝影: 孫曉東,國家地理圖片集
Katie的全名是Katrina Klett,她於1987年出生在一個美國的養蜂家庭。也是那一年,一艘從南韓出發的船抵達美國,帶來了亞洲的中華蜜蜂,也無意間帶來了它們身上的蜂蟎。
蜂蟎和中蜂在長期的鬥爭中共同前進演化,使中蜂發展出了一套相應的清潔機制。 但這種對中蜂威脅不大的蜂蟎,對生活在美國的西方蜜蜂來說,是一場空前的災難。
「那一年,美國90%的野蜂都死了。所以在我的成長中,我只見過集約化養蜂,蜜蜂就是牲口,和牛一樣,和雞一樣。而且每年要被蜂農拉來拉去。」Katie說。
她的童年大多是在路上。一群蜂農拖著自己的蜂群進行南北遷徙,每年5到6月在北塔科他州采蜜,9月到10月完成取蜜之後,前往加州為杏花授粉,然後在春季搬到德州培育蜂王。
其中,育王是他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通常,他們會花一年時間從大量蜂群中篩選最優蜂群,然後用特殊的器材檢測它們是否具備「衛生行為」。 這種行為意味著蜂群自身有抵抗力,即蜜蜂在幼蟲尚未孵化時能自己篩選出帶病幼蟲,並進行清理。
他們從這種蜂群裏培育出蜂王,然後賣給其他蜂農。這是一種人類技術和蜜蜂的協同前進演化,蜂群的顯性基因會因此得到改善,但篩選和培育不能暫停,否則蜂群會退回到原來的樣子。
2009年,Katie正在中國農科院實習,被導師派往雲南維西的柯公河谷,在傈僳村子格花箐培訓現代養蜂技術。
「我記得我一下車,還沒和任何人說話,就意識到這裏是養蜂天堂!」她說,「因為我看見到處有蝴蝶、有昆蟲,也看到這裏農業規模非常小,看見如此多樣的植被,以及溫暖的陽光。」
她幾乎立刻就決定取消回國的計劃,留了下來。村民們抽著蘭花煙,圍著Katie和她的蜂箱,議論紛紛。從一位說點漢語的村民口中,Katie得知,村裏14戶人都養蜂,而且每家人都姓「蜂」。

煙霧能夠幹擾蜜蜂之間資訊素的交流,防止蜜蜂發動群體攻擊,因此蜂農在檢查巢箱、分蜂以及取蜜時都會用發煙器噴灑蜂箱。而傈僳族傳統上會用「蘭花煙」來實作這一目的,這是一種後勁兒很足的手工煙葉,傈僳族村落裏經常能夠見到手持蘭花煙的人。
|攝影:
孫曉東,國家地理圖片集

在塔城鎮格花箐村後三公裏的山坡上的蜂場,養蜂人德都用蜂桶培育了中華蜜蜂。用蜂桶養蜂是當地傈僳族的傳統養蜂方式。與現代蜂箱相比,蜂桶養蜂沒辦法仔細檢查裏面蜜蜂的狀況,但好處是不用花費養蜂人太多時間。|攝影:孫曉東,國家地理圖片集
在之後的很多年裏,Katie拜訪了許多養中華蜜蜂的地方,包括越南北部、泰國北部、峇里島、印度南部等。她發現這些地方與柯公河谷有類似的特質:都是多山、多野生植被、少農田,當地人都喜歡用樹筒隨便養一點蜜蜂、幾乎不管理。
橫斷山脈垂直海拔落差大,擁有顯著的立體氣候帶譜。 在同一個山谷裏,可能囊括熱帶、副熱帶、溫帶、寒帶等不同氣候類別。 白馬雪山位於橫斷山脈東部,主要受西南季風影響,以至於這裏的植物區系雖是溫帶山地性質,但同時具備豐富的副熱帶成分。 因此,這裏常常會被稱為「物種基因庫」,或者珍稀生物的「諾亞方舟」 。
柯公河谷位於白馬雪山東南部,是橫斷山脈三江並流地區無數個山谷中的一個,不過,這裏比其它許多山谷都更早通車。公路連線了215國道香格裏拉-維西段和白馬雪山腹地,海拔從2000米擡升到3000米,和國慶生長的柯公村,是這條路上海拔最高的藏族村子,有小規模的梯田,種稻米。再往上都是傈僳族村,地勢陡峭,很少有農田。在他的兒時記憶中,這條路起初是伐木公司為了運輸木材而挖的。在1983年白馬雪山保護區成立之前,山上的大樹已經幾乎被伐盡了。
道路盡頭的施誇底村是柯公山谷海拔最高的村莊,居住著彜族和傈僳族,再往裏就是白馬雪山保護區。和國慶帶領我們在新村和舊村裏逛,認出各種蜜源植物,介紹它們的傈僳語名字。
「施誇底」也是傈僳語,意指長滿大樹的台地。 眼前光禿禿的景象,讓人很難相信這裏曾長滿雲杉和青岡櫟,森林密集得透不過光。 和國慶從養蜂人的經驗,猜想當年的砍伐或許無意中造成了施誇底的豐富蜜源:在大樹被抹去的地方,野薔薇、櫻桃、藍莓、羊奶果、獼猴桃、接骨木、草莓、沙棘等野生植物瘋長,從開春到入冬,輪流開花結果。山裏的蜜蜂、鳥和松鼠、施誇底村民,都仰仗它們帶來的盛宴。
在Katie看來,本土中華蜜蜂與本土植物是共同前進演化的。在柯公山谷,今天的農作物大多是外地品種,受農藥和化肥的影響,這些農作物的花不是中華蜜蜂的首選蜜源。它們喜歡的蜜源植物往往長在大山裏,在林地隱蔽處,花朵小到難以察覺。中華蜜蜂的嘴和舌剛好適合這些小花,又因為單個植物花蜜量太小,它們每次出門都必須造訪各種各樣的花朵,這些來自不同植物的花蜜,就是俗稱的「百花蜜」。
中華蜜蜂和蜜源植物之間是持續的共生互惠關系,後者為前者提供食物,前者在覓食時為後者實作了授粉。整個森林正是因此而熱鬧起來。「如果這些蜜蜂消失了,很多植物也會消失,依賴它們的其它生物也將受到威脅。」 Katie說。
在一項針對瀾滄江流域北部的 中華蜜蜂與其食源的研究 中,研究者 陳順安 等人分析了海拔2200米至2800米的中華蜜蜂所產蜂蜜的花粉成分, 發現中華蜜蜂與多種蜜源植物之間存在供食和授粉的互惠關系 ,這對當地生態多樣性的維系至關重要。

面向河谷的山坡上,一只中華蜜蜂正趴在一朵流蜜期的羊奶果花上,采集花蜜和花粉。中華蜜蜂的蜜源植物 往往長在大山裏 的 林地隱蔽處,中華蜜蜂的嘴剛好適合這些小花 。 這些蜜蜂和蜜源植物在長期的協同前進演化中形成了互惠伴侶關係。 |攝影:孫曉東,國家地理圖片集
外地來的西方蜜蜂無法參與到這種關系中來。 首先,西方蜜蜂不習慣在山區尋找零星蜜源,「它們來到這裏很快就會餓死,」Katie補充道,「或者被胡蜂咬死。因為它們沒有和這裏的植物、動物一起前進演化過。」為了逃離天敵胡蜂的追捕,本土中華蜜蜂的策略是飛Z字形路線,「而西蜂沒有這個經驗和能力,只會直線飛行,所以在這裏,胡蜂可以很快把它們消滅掉。」
由於這種互惠關系,施誇底從柯公河谷內海拔最高、耕地最少、最貧窮的村莊,變成河谷的蜂農眼中最特別的村莊。
2013年,柯公河谷的蜂群中開始出現中囊病。 這種已經重創世界各地中華蜜蜂的病毒,曾導致尼泊爾90%的野蜂死亡。這一年,在柯公河谷,80%的蜜蜂也因此死去,或逃離蜂巢、最後死在森林裏。
沒人知道這種病是怎麽傳染的,主流的應對方法是大量用藥。但中囊病會不斷產生變體,用藥會傷害蜂群,卻不能徹底解決問題。 柯公河谷的蜂農們選擇了一條漫長的道路,他們看著染病的蜂群一批一批死掉,等待蜂群自然地形成免疫屏障,這通常要花好幾年時間 。

白馬雪山保護區裏雲杉聳立的蜂場經常有熊的光顧,為了防止熊吃蜂蜜、並且搗毀蜂桶,當地養蜂人便把蜂箱高高地掛在空中,貪吃的熊們只能望蜜興嘆了。 |攝影:孫曉東,國家地理圖片集

除了熊的騷擾之外,中華蜜蜂也會遭受各種真菌或者疾病的攻擊,這個巣脾裏的幼蟲因為真菌的感染已經死亡,這會大大影響整個蜂巢的健康以及蜂蜜的產量。 |攝影:孫曉東,國家地理圖片集
2015年,情況出現了轉機。那年施誇底的蜜源植物比往年豐富,蜂農們將僅剩的蜂群拉到那裏,希望它們可以活下去。令人驚喜的是,這些蜜蜂抵達施誇底之後,不再死亡或逃逸,盡管病毒還在,但抵抗力似乎開始恢復了。
這20%的蜜蜂最終發展成大量的健康蜂群。 這某種程度上也驗證了Katie目前正在研究的博士課題——蜜源植物的多樣性可能有助於蜜蜂免疫力提升,更確切地說,花粉作為蜜蜂的主要食物,其多樣性決定了蜜蜂所能獲得的蛋白質、胺基酸的多樣性。
對蜂農和科學家來說,中囊病的起因仍舊是謎。唯一能確定的是,這種病如同潮汐, 不會永遠消失,每隔十至十五年,便會重新席卷蜂群 。它是柯公河谷每個蜂農心裏的陰影,但施誇底就像一個象征,為熬過下一波浪潮留下一絲希望。
每次去昆明或大理,Katie總是會遇到有人感嘆她怎麽會在維西生活,「那麽落後的地方……」他們說。還有很多人連維西都沒有聽說過,更何況塔城鎮、柯公山谷。她不認同那種對「落後」的認知:「這裏的傈僳族可能不習慣花心思去裝修房子,或種很多地。但如果跟著他們走進森林,你才會知道什麽叫厲害。」
在Katie帶來活框蜂箱之前,傈僳族已有漫長的養蜂歷史,追野蜂、掏樹洞、用蜂筒,都是沿用至今的傳統技術。傈僳語中有不同的詞匯用來稱呼蜜蜂。比如,喜歡住在森林裏的蜜蜂被稱作「Bia Ma」(音譯),意指「產蜜的女性」;而住在懸崖上的蜜蜂,被稱作「La Bia」(音譯),意指「崖蜂」。樹筒、蜂籠是他們傳統的養蜂工具,前者是一種模仿天然樹洞的仿生裝置,只需放在背陰朝陽處,就常會有蜂群自己搬進去;後者取材於森林裏的竹子,形狀像蜜蜂的肚子。
起初,村民們很難相信活框蜂箱能有什麽建樹,也不覺得需要花精力管理蜜蜂,只是將樹筒放在村子附近,偶爾去看看蜜蜂還在不在裏面。Katie回憶道:「以前他們認為蜜蜂是無限的,如果告訴他們把蜜取完蜜蜂冬天就死了,他們會說,哎呀,沒事,蜜蜂多的是。」
為了證明活框蜂箱的可行性,以及持續管理蜂群的可能性,Katie提議和村民們一起養一個季節的蜜蜂。「我們語言不通,但他們本來就熟悉蜜蜂,一眼就能看懂我在做什麽。」

每個蜂場的蜂農小屋裏,都隨時備好轉移蜂群用的蜂籠,以便隨時發現分蜂的蜂群後進行轉移。很多傈僳族的養蜂人都是木匠,他們根據對蜜蜂的了解自制蜂箱及蜂籠。 |攝影:孫曉東,國家地理圖片集

在短暫地檢查過蜂桶裏中華蜜蜂的狀況後,德都蓋上蜂桶的蓋板,只留下工蜂進出的一條窄縫,隨後騎摩托車趕往他的下一個蜂場。 |攝影: 孫曉東,國家地理圖片集
在這個過程中,村民們開始理解使用蜂筒和蜂箱的區別——蜂筒中的巢脾是固定的,養蜂人只能開啟蓋子估計蜂群的情況,但無法仔細檢查蜂王、病害,也無法判斷蜜蜂是否會分蜂、逃逸。
當活框蜂箱在1851年被發明出來時,人類的養蜂方式從被動變為主動——蜜蜂將巢脾結在靈活的巢框上,養蜂人可以取出來,檢視是否有病害,是否有蜂王,或者空間夠不夠,從而作出相應的管理對策。在Katie看來,如果一個人要把養蜂當成事業來做,用蜂箱是最合理的。
管理蜜蜂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給蜜蜂餵食。 在取蜜時給蜜蜂留蜜,也不一定能保證它們過冬的食物需求。因為每個蜂群的強弱程度不同,對食物的需求量也會不同。因此,如果希望蜜蜂安然過冬,養蜂人通常要在10月中旬檢查所有蜂群,看它們是否儲存了足夠的食物。
就活框蜂箱而言,如果這時還存有兩框蜂蜜,就不用給蜜蜂餵食,整個冬天不再開啟蓋子,直到來年春天。 如果發現存蜜不足兩框,就必須給蜜蜂餵白糖水——一種相對便宜的蜂蜜替代品。 盡管白糖營養價值不及蜂蜜,其來源也可能帶有農藥化肥,但餵食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如Katie所言:「不餵就是不負責任。」
「沒有對與錯,只有合不合適。」每當我們問起養蜂操作細節,和國慶最喜歡這樣來回答。因為養中華蜜蜂其實沒有萬能定律。不同於已被馴化的西方蜜蜂,中華蜜蜂生活在復雜多樣的環境裏,與自然環境有很強的互動性,也常常自然分蜂飛回大山。
蜂農必須是紮根於這個山谷的人,熟悉這裏的一切,才可能很快預測什麽時候會流蜜,什麽時候會分蜂,什麽時候該餵食。這些知識隨時都在變化,不是印在「操作指南」裏的固定數據。Katie也驚喜地發現,村民們從來不對自己帶來的養蜂技術照單全收,而是結合自己的經驗來進行調整。比如,在接受活框蜂箱技術的同時,他們也認為外地蜂箱並不適合本土氣候,堅持要根據自己對蜜蜂和本土環境的理解做自己的蜂箱。
「我起初覺得沒這個必要,因為我沒見過這樣做的。」Katie說,「但是他們一定要試。結果幾年後,我們發現這確實有用。 如果蜂箱比常規蜂箱更厚,蜜蜂感到暖和,就不需要那麽多食物。如果用薄薄的蜂箱,蜜蜂不一定會死,但是你會必須餵更多,成本更高。」
在柯公河谷之後,為了繼續研究中華蜜蜂,Katie曾在不同國家與當地蜂農合作養蜂。每到一個地方,她都會積極地尋求當地人的意見。在長期的合作中, Katie和當地村民之間形成了一種互補關系:由她告訴村民們關於蜜蜂的科學概念,由村民們來告訴她當地到底在發生什麽。 她發現自己「年紀越大越尊重那些知識——以前他們會告訴我一些關於蜜蜂的聽起來不科學的說法,我會不在意。但現在我發現,大部份時候他們是沒有說錯的。」
那些聽起來沒有科學數據和實驗支撐的說法,是村民們對當地環境的直接感受,包括他們從小到大的經驗,以及他們祖輩的記憶。「他們會教我每個季節會發生什麽,下雨太多會怎樣,天氣幹旱會怎樣。所有跟本地氣候相關的知識都是他們教我的。」要在這裏養蜂,她必須依賴這些知識,「而他們從骨子裏知道這些知識。」

高大的雲杉上有一些不起眼的小洞,這是當地養蜂人為吸引蜂群開鑿的人工樹洞,優先選擇背風向陽、周圍沒 有遮擋的開闊高處,讓挑剔的蜂群能夠選擇為它們準備的 「旅館」,待到移蜂時周圍搭上木架,用這種方式逐漸取代之前從野外尋找野生蜂群的傳統方式。 |攝影: 孫曉東,國家地理圖片集
每次跟著柯公山谷的傈僳村民上山,Katie都感覺自己眼中的森林和他們眼中的森林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們可以非常深刻地看到這裏發生了什麽事,或者這裏應該會長出什麽植物。如果餓了,他們會知道這附近長出什麽能吃的。
和他們一起坐在樹上,他們會看昆蟲怎麽飛,然後判斷胡蜂可能在那邊,結果就真的在那邊。而我坐在那裏很努力地看,能看到的只是很多樹葉。如果在山裏出什麽問題,我們可能會死在那兒,但他們可以很快處理問題。非常了不起,現在這個世界沒有很多這樣的人,已經沒有了。」
這種對當地環境的體察是從小積累起來的。過去,傈僳族是優秀的獵人,不必帶什麽食物,就可以在山裏生活很多天。如今他們進山找野蜜蜂,也只是帶一條毯子。山上到處都是他們的食材。他們和山裏的其它生靈一起,切身地體會山裏的變化。
傈僳族養蜂人向岑是和國慶的發小,他們小時候常常一起跑進山裏玩。向岑對蜜蜂的熱愛遠近聞名。他經常感嘆大山的好:「這裏除了竹子和蕨類,所有植物都會流蜜。」現在,他被大家戲稱為「蜂(瘋)子」,和國慶打趣道,「大家都受不了他,因為跟他一講話,句句離不開蜜蜂。」
向岑會走路的時候就跟著父親和爺爺養蜂了。那時候他們家有幾十個蜂筒,所產出的蜂蜜會被儲存在罐子裏,然後一整年用來沾「三吹三打」吃。這其實是在火灰裏面烤熟的玉米面或面粉粑粑,吃之前要吹和打掉表面的灰。當地人戲稱這種傈僳族食物為「三吹三打」。實際上,這種粑粑很硬,在當時目之所及的食物中,只有蜂蜜可以幫助人們咽下去。向岑小時候,最喜歡的食物就是「三吹三打」沾蜂蜜。
抵達柯公山谷不久,Katie就見到了向岑如何在森林裏抓野蜂。在那之前,她只從父輩嘴裏聽說過這種生活。動物行為學家 杜文·戴爾·西利 (Thomas Dyer Seeley) 推測人類追蜂的歷史可以追溯到遠古時期的狩獵采集社會,生活在公元一世紀的古羅馬農事作家 科盧梅拉 (Columella) 已經記載過如何吸引蜜蜂,然後追蹤它們回到蜂群的「潛伏地」。
向岑從小就愛往山裏跑,上過半年學,輟學後主要是在山上放羊和養蜂。抓野蜂的技術,是跟父親學的。 這個技術有兩部份,一部份是跟蹤蜜蜂,另一部份是把蜜蜂帶回家。
「和父親去放羊的時候,他會帶著我去追蜜蜂。先是在樹葉上沾一點蜂蜜吸引蜜蜂,然後跟著它們找過去。有時候一天很快就找到了,有時候一整天都找不到。還要爬樹,很危險。經常肚子餓得連回小屋的力氣都沒有了。」
他所說的小屋,是牧羊人建在森林牧場附近的臨時居所。如今,他在海拔3000米的雲杉林裏有一個蜂場,也有一間小木屋。堆放一些工具、食物,有時他會一個人在那裏住。有一年冬天,向岑在家裏突然感到腹痛,冥冥中覺得蜂場出了事,就好像蜜蜂的警報資訊素翻山越嶺傳到了他身上似的。他急忙上山去,發現蜂場已經被黑熊破壞。現在說起這件事他還會心疼:「老熊吃蜂蜜不可怕,可怕的是吃不完它還會故意打爛其它蜂群。」
從那以後的每個冬天,他都會一個人住在小木屋,吃「三吹三打」,守護蜂群。
向岑小時候的森林裏,樹洞都是天然的,蜜蜂會挑幹燥、溫暖的搬進去。四月正值中華蜜蜂自然分蜂的季節,向岑和父親會去檢視有沒有蜜蜂飛進去。現在森林裏到處都是人工挖的樹洞,這些樹洞通常在很高的樹上、或者懸崖邊的樹上——這也是為了防熊。
如果發現有蜜蜂入駐樹洞,他就會背著蜂籠和籃子爬上去。首先要抽一口蘭花煙吐進樹洞,幹擾蜜蜂的警報資訊素。然後開始割巢脾。必須先割蜂蜜脾,然後割幼蟲脾,因為前者容易破開,蜂群會變得很激動,甚至可能殺蜂王。直到所有的巢脾被割幹凈了,才能開始抓蜜蜂。
蜂籠必須掛在樹洞口,因為需要一邊抓一邊檢視蜂王是否已經進去。如果蜂王已經進入蜂籠,就大功告成了,剩下所有的蜜蜂會自己跟著進去。 向岑的父親告訴他,越強大的蜂群越難抓蜂王,失手是常事。 向岑估摸過自己的失手率,大約是30%。而技術不好的蜂農,失手率大概是50%。 被抓到的蜜蜂會被安置在背風向陽的蜂筒裏,這樣的地方幹燥、溫暖,才留得住蜜蜂。
除了抓蜜蜂回家養,有人有時候也會直接在森林裏取蜜。無論抓野蜂還是取蜜都需要爬樹,但有人曾為了方便,想直接砍掉大樹。「為了那麽一點兒蜂蜜,砍倒一棵上百年的大樹,太不值了。」和國慶說。向岑也覺得可惜極了,不過他最在意的是蜜蜂:「太不值了,樹倒下來的時候會砸死那個蜂群。」 他告訴和國慶,自己前兩天在森林裏碰見有人準備砍倒兩棵樹,他給了那人三百塊錢。「那兩棵樹上的蜜蜂就可以留下來繼續分蜂了。」在向岑眼裏,大樹在,蜜蜂就可以在。

五月下旬的一天,和國慶家的一群蜜蜂自然分蜂了。他及時發現了跟著新蜂王出來的蜂群,用蜂籠 把這團蜜蜂 收進了 新的蜂箱,再用擋蜂板擋住蜂巢出入口,確保蜂王不會逃逸,幾天後這箱中華蜜蜂的狀態將趨於穩定。 |攝影: 孫曉東,國家地理圖片集
此外,向岑還自己創造了特別的養蜂工具和管理策略。在白馬雪山深處的杉樹林中,可以看見一些被串起來懸在空中的蜂箱,這是向岑想出來的防熊措施。以前人們能想到的是在樹洞口安裝鋼鋸,或者把蜂筒放在高處,但沒人想到還可以「在空中養蜂」。
在這個蜂場,還可以看見另一種向岑的獨家設計——我暫且叫它「蜂箱筒」。不同於傳統的橫置蜂筒,這種裝置是豎置的巨大原木。他在裏面放活動巢框,既結合了活框蜂箱和傳統蜂筒的優勢——可以仔細檢查,也可以保溫——還增加了蜂巢空間,以收獲更多蜂蜜。
向岑對管理蜜蜂的策略是從全域的角度出發的。就好像他心裏有一套靈活的演算法,或者一幅復雜的地圖, 讓他能夠判斷每個蜂群應該生活在什麽樣的環境,以及它們之間可以怎樣互為補充 。他以此為依據分配了不同的材料和裝置,以及不同蜂群的位置,讓一些蜂群被養在蜂箱裏、蜂筒裏、「蜂箱筒」裏,還有一些就留在樹洞裏。
「以前是蜜蜂養人,現在是人養蜜蜂。」他說。如今山谷裏的氣候已經不同往昔。縱使最有經驗的農人,也無法預估雨季什麽時候來,或將下多少雨。有時候雨會從三月下到十一月,有時候則會遇上整年的幹旱。在這種情況下,蜜蜂更難生存,養蜂人亦然。
為了應對越來越不穩定的氣候,向岑將蜂群分散在不同海拔和環境的蜂場。 這些蜂場周邊的蜜源植物類別有細微的差別,流蜜期也會因為海拔變化而錯開。這樣的分配降低了養蜂風險,讓他成為在蜂蟎肆虐或天氣幹旱的年月裏,唯一還能收獲蜂蜜的人。
向岑的養蜂技術始於他對蜜蜂的「心疼」。他最喜歡守在蜂巢門口看蜜蜂回家的樣子,可以看一整天。有時候,工蜂會背著花粉停在門口休息,他看見她們的肚子一鼓一鼓的,覺得她們和人一樣,也會累到連連喘氣。他就像描述某個親戚或老友一樣,說:「蜜蜂這種動物,越養越會心疼她們。」
因此,檢查蜂箱的時候他比誰都小心。放巢框之前,他會費勁兒地吹半天,直到所有可能被壓到的蜜蜂已經挪開。於是他檢查蜂箱的時間比別人多出一半。其他養蜂人認為取框和放框時死幾只蜜蜂是可以接受的損失,因為整個蜂群的健康是更重要的。向岑明白這樣的道理,但就是不忍心。
向岑對蜜蜂的關心超越了物種的邊界。當地的森林為蜜蜂提供居所,蜜源植物為蜜蜂提供食物;而蜜蜂為當地植物進行授粉,維護了當地生態多樣性,為人類提供營養豐富的蜂蜜,並增加了當地人的經濟收入;而養蜂人在享受蜂蜜的同時,必須考慮到蜜蜂族群的延續。
這種跨物種的親密鏈條可能貫穿了整個人類前進演化歷史:營養學家 阿麗莎·克里滕登 (Alyssa Crittenden) 認為,人類大腦活動主要會消耗葡萄糖形式的能量,而蜂蜜是人類飲食中葡萄糖含量最高的天然食物。 因此她推測,蜂蜜可能出現在人類前進演化史的所有關鍵節點上,為人類的祖先完成復雜的智力任務提供了營養支持。
人類今天所有的養蜂技術都深入地介入了蜜蜂的繁衍和生存,兩者的命運因此緊緊纏繞在一起。這些介入,對蜜蜂的族群產生了或深或淺的影響。比起移動養蜂人每年拖著蜜蜂為集約化農場提供授粉勞動,很多蜜蜂在旅途奔波中死去,向岑對蜂群生活環境的多樣分配從對蜜蜂的關心和愛護出發的。這種關心正在創造小小的奇跡。
通常,一個人能管理的中華蜜蜂頂多在50箱左右,向岑已經突破了很多人的極限。 「我從沒見過一個人可以養得跟他一樣多。一個人養幾百群中蜂,而且養得那麽好,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Katie說。
在柯公河谷的每一個蜂場,都可以聽見流水聲。無數溪流從山上向下,匯聚成柯公河,然後淌入臘普河,最終在小河口匯入長江上遊的金沙江。
水源附近的草叢、泥地,是蜜蜂的飲水和采水處。天氣炎熱的時候,工蜂不僅需要飲水止渴,還需要采水回蜂巢。采水蜂會將采來的水塗抹在巢房上,以達到降溫的目的。另一種方式是工蜂列在巢門口用翅膀扇風,透過促進蜂巢空氣流通來實作降溫。相反,在寒冷的季節,加熱蜂會透過抖動身體產生熱量來為蜂巢保溫,或者聚成一團來取暖。 巢內巢外的溫度對蜜蜂都性命攸關 :在巢外的婚飛和勞作都需要適宜的氣溫,而巢內的溫度也同樣關乎蜂群存續,低溫容易導致病害和死亡,高溫也會導致幼蟲發育不良或者死亡 。

塔城的山谷裏有幾百種蜜源植物,在花蜜和花粉豐富的大流蜜期,工蜂每天不知疲憊地往返蜜源植物和蜂巢,蜂農會略微改造一下蜂場附近的水源,方便這些疲憊的工蜂隨時補充水分。 |攝影: 孫曉東,國家地理圖片集
蜜蜂復雜的社會結構還並未完全被人類所認識,但目前能夠觀察到的是,蜂王、工蜂和雄蜂有著非常明確的分工。如果將一整個蜂群理解成一個生命體,每一只蜜蜂更像是構成這個生命體的細胞,它們各司其職,維持這個有機體存活下去:蜂王終其一生都吃著工蜂提供的蜂王漿,不斷地為蜂群生育新的勞動力;工蜂的食物主要是花蜜,她們搭建巢房和巢脾,培育和擁立蜂王,或者咬死不合適的蜂王,采花粉,釀蜂蜜,以及守衛蜂巢等,調節蜂巢溫度的工作也屬於她們;雄蜂通常只吃花粉,除了在婚飛期和蜂王交尾,他們什麽都不做。
五月是蜂王婚飛的高峰期,下午在蜂場總能聽見天空中熱鬧非凡,那就是蜂王飛到高空,一群雄蜂正追逐著與她交尾的聲音。等蜂王的受精囊裝入了足夠的精子,她就會回到蜂巢中,用好幾年的時間產卵。如果一切順利,她每天都會產下600到1000個卵。這些卵將孵出工蜂,不斷補充勞動力的空缺, 整個蜂群由此存續。而雄蜂在交尾之後將成為整個蜂群的累贅,為了不讓他們消耗花粉、占據空間,工蜂這時會將他們咬死,或者將他們趕出蜂巢、流浪致死。

每年的夏初蜂巢裏就會培育新的蜂王,蜂王幼蟲的巢更大更突出,稱為 「王台」,和國慶仔細檢視這個巢框上的王台,轉移到新蜂箱之後,它將是新的蜂王。 |攝影: 孫曉東,國家地理圖片集

和國慶在自己蜂場裏一個空置的蜂箱裏,意外發現了一群蜜蜂進駐並開始建巢繁殖,於是將它們轉移到已經放好巢框的蜂箱裏。在轉移好蜂王之後,國慶徒手一把一把將工蜂小心翼翼地進行轉移。 |攝影: 孫曉東,國家地理圖片集

一只中華蜜蜂背著沈重的花粉返回巢箱,如果說花蜜是蜂群的「米」,那花粉便是蜂群的「肉」,在確保蜂群健康方面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攝影: 孫曉東,國家地理圖片集
山谷裏的每個人都感受到了氣候的變化——向岑發現小時候會在冬天結冰的溪流如今不再結冰;而Katie記憶裏十多年前的柯公山谷,夜晚總是寒冷,「如今無論夏季或冬季,晚上都不怎麽冷了。」在越來越不穩定的氣候條件下,蜜蜂的自我調節和更新能力也受到了影響。
和國慶說:「去年整個山谷的蜂蜜都絕收了,因為幹旱,大部份植物都沒有流蜜。蜜蜂沒有吃的,也沒有產出。」而今年的雨季似乎卻提前了,下雨時氣溫降低,很多花沒來得及盛開就雕落了,村民們經歷了一場倒春寒,在五月初穿起了羽絨服。
在大流蜜期,一只工蜂的壽命非常短,它們一刻不停地忙碌,直到翅膀震碎。「差不多20天就全都碎了。」和國慶說。柯公河谷的大流蜜期一般始於五月中旬,分蜂期在四月中旬。傈僳族喜歡把「分蜂」說成「分家」,「和人一樣」,家族人口多了,居住空間滿了,就得尋找新家園。但四月之後的分蜂熱潮是蜂農不願意看見的事,因為分蜂可能導致一些蜜蜂錯過接下來的大流蜜期。蜂群有時會自己進行調節,一些工蜂會在大流蜜期中咬死多出來的蜂王。蜂農能做的是在蜂箱之上加繼箱,給蜂群多一點空間。按照和國慶的經驗,今年五月下旬還不斷有蜂群在分蜂,這可能又是「不正常」的一年。
除了愈加捉摸不定的氣候和分蜂,讓蜂農們更加無法把握的是市場銷售。靠養蜂賺錢,在柯公河谷還只是近十年才有的事。
以前人們只是把蜂筒放在村子附近,蜜蜂是否入駐全看天意。而蜂蜜從來不是一種商品,除了自家吃,頂多還可以贈送和交換。端午節前夕,傈僳族會把他們多余的蜂蜜帶到山下的藏族村莊,用蜂蜜交換一些大米,或者別的物品。這些藏族村莊有端午節用蜂蜜配草藥的習俗,人們認為一起喝下去可以防病害。
剛到格花箐時Katie就註意到,村民們種的玉米僅供自己吃,能售賣的東西僅限於從山裏找到的藥材和松茸。花了好幾年時間,Katie才讓大家意識到蜂蜜是可以買賣的,而且,不同於村民們喜歡的混合著花粉、花蜜、幼蟲、巢脾的蜂蜜,外地市場更喜歡過濾幹凈的純蜜。前者營養更豐富,但也更容易變質。

喇嘛寺村向岑的蜂場裏,他正從巢框上割下新鮮的巢蜜。傈僳族傳統上食物比較簡單粗糙,蜂蜜給當地人的餐桌上提供了難得的營養和口感,因此家家都會養上幾箱蜜蜂,在端午節等傳統節日裏還有互相饋贈的習俗。|攝影:
孫曉東,國家地理圖片集
Katie開始意識到,幫助蜂農不止是培訓技術,也不是直接給錢,而是找到一個可持續運轉的良性市場。於是她與和國慶成立了一家蜂蜜公司,收購村民們的蜂蜜,再推銷到更廣闊的市場。這時他們才意識到,經營和銷售對自己來說,完全是一個陌生的領域。
「或許最好的方式是,蜂農不要百分之百靠賣蜂蜜生活。否則下次中囊病來了怎麽辦?」Katie說,「我能想到的最好狀態,是村民們可以賣松茸,賣蟲草,也賣蜂蜜。然後也接待一些遊學團住在他們家,學習關於蜜蜂和植物的知識。」
後來幾天我們都沒有見到向岑,才知道他去挖蟲草了,又要在山裏待許多天。
在柯公河谷的其它村莊,我們還遇見幾位傈僳族養蜂人,他們曾在東部省份打工,修隧道,建房子,如今為了照顧小孩留在家裏。他們熱心地從樹筒裏割下一塊巢脾來請我們吃,一邊割一邊拍影片直播,觀眾也都是傈僳族。
柯公村一部份青稞已經可以收了。Katie與和國慶在上午割完青稞之後,領著我們去了山上的蜂場。在路上我們碰見了向岑的哥哥,他在森林裏舉著望遠鏡,尋找崖蜂的蹤跡。
蜂場在海拔2800米的雲杉林裏,林地裏,各種植物纏結在一起,不留空隙,很難分清誰是誰。夫妻倆開始檢查蜂箱,Katie愉快地哼著歌。一個巢框上的幹癟蜂卵讓氣氛突然凝重起來,這是典型的中囊病癥狀。
「如果一直下雨這種病會很容易出來。如果開始大量流蜜,有時候就會自己變好了。」Katie說。她相信蜂群感染中囊病,就像人類得感冒,無法徹底根治,但可以靠增強抵抗力來獲得康復。「所以,豐富的花粉和流蜜就是最好的治療。」兩個人神色擔憂地把巢框放回去。「只能等它們自己調節。」她聽起來不太確定,「也許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這裏的蜜源很好。」

Katie與和國慶夫妻倆正在牙灑附近的蜂場檢查巢箱,他們根據巣脾裏蜂蜜的儲存情況判斷是否要在上面增加繼箱,增加單個蜂箱的蜂蜜產量。 |攝影: 孫曉東,國家地理圖片集
作者簡介:格布,寫作、制片、策展。對身份認同、移工權益、種植園經濟等議題感興趣。目前深耕東南亞山區少數民族發展與性別平等問題。攝影師孫曉東,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年度公益攝影師,聯合發起非遺保護公益機構「稀捍行動」,專註於用影像挖掘生態物種和人文傳承之間多元而又共生的內在關聯。
原文刊載於【華夏地理】雜誌7月刊
撰文:格布
攝影:孫曉東
責任編輯:王婷婷
版式設計:Arv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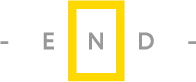
點點 👇 ,謝謝關註。
伸出小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