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巨著型塑重典精神——這樣的事業需要宏富的材料,深厚而坦蕩的見識,對真理的執著和長久的耐心,厚達八百多頁的【李約瑟鏡頭下的戰時中國科學】(湖南教育出版社2024年3月版)正是做到了這一點:它不是為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做史料組譯和人物評傳,而是相對獨立地闡發出何為傳統的中國科學精神,在抗戰這一極端困難的特殊時期,這一精神砥礪得尤為耀眼。
以李約瑟1943-1946的中國調查路線和500多幅珍貴照片為線索,我們重溫了李約瑟艱險又傳奇的調查行旅,見識戰時中國科學的艱辛與傲骨。與【中國科學技術史】所不同的是,我們的閱讀過程不是要在途中追問李約瑟難題(中國為何在近代沒有發展出科學體系),也不是在一個同仇敵愾的大時代去炫耀先人智慧——這都不合時宜。唯一合時宜的是在抗戰這樣的血火年代去追問,我們的科學此時在做什麽,為什麽要做,是怎麽在做,做下去又是為了什麽。哪怕已經有了答案這種追問依然是有必要的,它能夠喚醒更雄渾的自覺與自強。
在這段時間之外,哪怕在李約瑟中國行結束後的八十年間,回答李約瑟難題和總結古人智慧這兩件事情都總有人不停在做。而他的四年中國行所獲得的直觀體驗和東西方文明觀科技觀的劇烈碰撞和融合,卻長時間被知識界所忽略,更何況如本書般細致入微地做歷史呈現。
這段時期的歷史貢獻早有定論:李約瑟之行為戰時中國科技帶來了大量的科技物資和資料,為維持中國科技做出巨大貢獻;向國際社會介紹中國科技狀況和成就,光是他為浙江大學推薦發表在【自然】雜誌上的論文就有五篇;再是向中國提供科技咨詢,各類講座和演講多達123次。但唯有豐富的細節才能勾勒偉大的現實,這正是本書的獨特貢獻:如果沒有了對車轍和風雪的切身體驗,便無以深入當時科技工作者憂患而又堅毅的精神世界,這種精神世界並非由戰亂而起,而是歷由數千年中華文明擔當者所不斷塑造,戰火僅是它不能被摧毀,反而能救蒼生於水火的又一明證。
安貧:被重設的中國科研
當李約瑟剛剛來到中國時,看到的一切都令人震驚。在這之前,他是懷著對中華文明的強烈好奇從英國政府獲得了這一光榮使命。當他開始慢慢熟悉的時候,重新界定了自己的責任:他不是來滿足好奇的,而是必須朝著更深處去下潛,去描述中國科學的歷史圖譜和精神信念。
他看到中國科學的倔強是如此震撼,到處是簡陋和煙塵所不能掩蓋的聖潔光輝:湯飛凡領導的防疫處在昆明一片荒灘上重建,李約瑟記載他們1942年就生產了500萬支傷寒疫苗。利用本地生產的蔗糖和玉米,他們還在1944年培養出中國自制的青黴素,挽救了無數抗日將士的生命。天文學家周長寧有整整四年從未讀過新的學術雜誌,甚至都很難用上電,也在堅持他的研究。

土主廟中的醫藥研究所,雲南昆明大普集,1944年8月28日
還有無數的細節呈現在他的筆記中,他慢慢明白責任不僅僅是記下他們在做些什麽,而且得記下他們究竟是怎麽做的,中間還在思考他們為什麽要這樣做的問題。在西南聯大,因為沒有煤氣,科研所有加熱都用自制的土電爐進行,電爐絲沒有了,就用廢金屬屑代替。為細胞核染色用的蘇木精沒有了,就從雲南土產的植物中提煉。顯微載片沒有了,就用空襲震碎的玻璃。他們失去了所有的物質條件,但僅憑最基本的信仰就能堅持下來。地質所李善邦博士用邊角廢料制造的新式地震儀,取名為霓式地震儀,三年時間記錄到109次地震;中醫藥研究所搬遷到昆明郊區年久失修的土廟裏,就在巨大觀音像前研究,佛像前有石印機,標本和桌子,他們就在這裏編制出了【滇南本草圖譜】;在華西協合大學,醫療小組的資料在轟炸中遺失了,實驗用猴因為沒有資金也放棄了,他們自制的油墨很容易褪色,自制的香蕉水也不足以保護標本……李約瑟不禁感嘆到:「堅毅這個字眼已不足以描述他們,除非我們加上英勇一類的形容詞。」
這果真是一次「意外的旅程」,熟悉科研工作的李約瑟明白科研結果是具有不確定性的,科研過程也是有不確定性的,只是在中國看到的這種不確定因素,因為與優渥的科研環境有強烈的對比給他以巨大的震撼。在這種不確定中,反而誕生出更為確定的人和信仰。地理,氣候,經濟,人文景觀,這些都是構成科技發展的條件。同時歷史也是,他們都是科技文明長河中不可缺少的布景。現實也是,現實會影響長河的緩急,但絕不會改變它的流向。使長河奔流的動力始終是這裏生存的意誌和謀求幸福的欲望。

男孩們曬制過冬用的煤餅,甘肅張掖山丹。
在山丹的一所學校,他看見十來歲的男孩們制瓷、紡紗、刷墻、打煤餅、植樹、築壩、造紙……他們不僅僅是在這裏學習工藝和科技,而是用他們尚未成熟的身軀去承擔一個受難中民族所急缺的一切。照片中,我們可見看見這些男孩無一例外都有散發出油汗的光澤,裸露著風吹日曬的深色肌膚,但他們身上都有永不疲倦的青春活力。
那些粗糙簡陋的房舍和工具,比起侵略者巍峨堂皇裝滿了侵略計劃和滅絕技術的總部大樓,更能代表人類世界的良知和未來生活的夢想。
李約瑟在這裏深刻體會到一種統一的意誌和樂生樂死的情感,這必須使他對中國文化做出更深沈的追問——這是他作為科技使者的與眾不同之處,他曾經夢想成為法拉第那樣因為發明而名垂青史的人物,因有自知之明而轉向為科技史。以人類文明為座標來敘述科技,才能使得自己這種沒有科技成果的研究獲得長久的生命,和被後世不斷感念的寬慰。
樂道:竹的誌節和蔥綠
在古代,中國科技從來就是與文化,生活,思想融合在一起,很少有單獨存在的時刻。李約瑟在考察中反復見證科技中存在的文化意象,這是中國古代科技在精神層面的真實。
比如竹子。
竹子是君子,是士,無論任何時代都是象征中國科技的風骨,以孤直喻節義,以蔥郁照汗青,「未出土時先有節,便淩雲去也無心。」「亭外碧幾竿,清姿耐霜寒。」照片中有四川精耕的田野,河邊矗立著發明於公元一世紀的龍骨水車,高達十米;在自貢李約瑟見識了鹽井使用竹管運送富鹽水和天然氣,管道能夠長達幾十裏;在都江堰,戰時的水利機構就駐紮在李冰廟裏。他註意到這裏會使用竹編固定的石頭來修建攔河壩蓄水。竹子從不因氣節失其風姿,不為合群去其高蹈,理解竹是理解中國文化很重要的一環。

同濟大學的生物學家,童第周(左三),史圖博(右三)、吳印禪(右二)、仲崇信(左一), 四川李莊,1943年6月。
抗戰時期的中國科學工作者精神向度上仍為傳統的君子和士。李約瑟認為,將超自然、實用、理性和浪漫因素結合起來,這方面全世界任何民族都不曾超越中國人,這裏面所包含的思想因素引發他更多的思考。
他接觸到的中國科技工作者不乏李四光、茅以升、竺可楨、華羅庚、童第周等聲明顯赫的人物,大部份都具有光鮮的留洋背景和顯赫的家世。即使是普通大學裏的不知名教授,很多都有過曾在世界一流機構擔任要職和科研骨幹的經歷,以至於他很多次演講都能用德語或者法語直接進行,根本無需擔心聽眾的能力。他們無一例外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選擇共匡國難,都以自身的風骨畫出了遒勁的竹:「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為自全之計。」
照片裏這些科學家在田壟、寺廟、公路、操場和簡陋的實驗室反復出現,表情是一種帶著真摯而溫暖的微笑,而不是在轟炸過去之後新生的慶幸,好像他們僅是在參加一場春天的田野郊遊。這種樂觀通達同樣是一種士氣,就如「泰坦尼克」號沈沒前弦樂隊溫柔而鎮定的演奏,用須臾不可或缺的使命感去求得豐滿的人生。
李約瑟在考察遷往重慶的中國衛生機構時感嘆,即使帶著巨量的資料和裝置奔波上千英裏,也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他說:相比之下,我們英國人中有多少人能夠做到不願在侵略者統治下討取一種舒適的生活,寧願堅持反侵略,而過著艱苦的生活。
天問:中國科技的精神貢獻
李約瑟接觸到的李濟、傅斯年、吳作人等人文學者也給他以巨大的影響,從而為將李約瑟難題上升為深沈而持久的文化追問。
最早的中國哲學典籍裏就提出了一些原始的科技觀,比如【莊子·天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老子】中的「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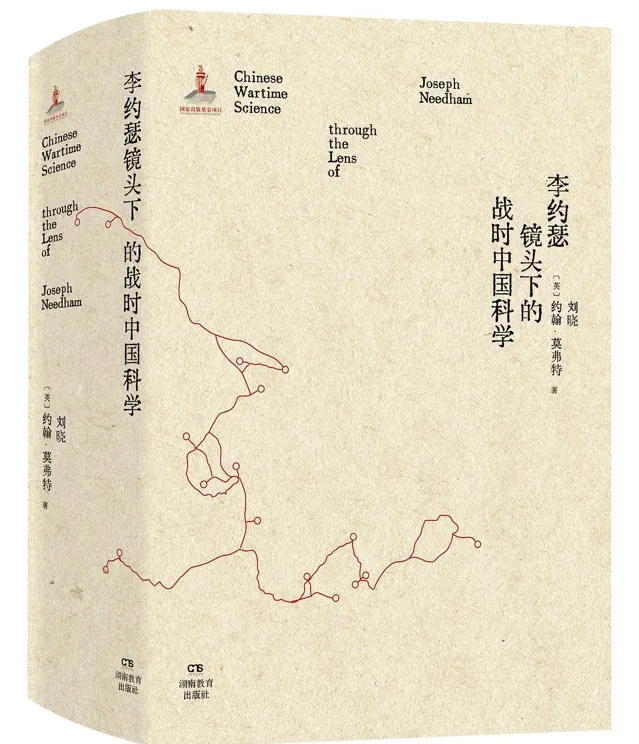
【李約瑟鏡頭下的戰時中國科學】
幸運的是,在尋求道德規範的同時中國哲學也講究通達,必須要圓融地解決人之存在的所有問題,要將人之所害統統變成人之所利。不至於讓偏見去獲得徹底的統治地位,先哲們試圖用「君子之器,不假他人」這一理想掌握技術的力量,也就是用崇高的道德規範去掌握和使用技術力量。這種中國式自然哲學與近代興起於歐陸的實證哲學和力量型哲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前者強呼叫文明去掌握技術,後者強呼叫技術創造文明。
比起後者來,前者的觀念在中國大一統的世系文明中很少有過根本上的變化,即使是近現代的動蕩亦未能將之顛覆。李約瑟見識到的中國科學風度何以始終保持古典式的高尚?司馬光在【才德論】中早有回答:「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這正和波蘭詩人米沃什所說「人類不幸的罪魁禍首是無理性的才智」如出一轍,二戰的慘烈已經在李約瑟的心中證明了,善惡之分何以比科技神力更為重要。
因此李約瑟看見活著的中國哲學始終在滋養著這廣袤大地上的一切,食物的芬芳,霧氣中的水車,拾禾的孩子,趕著大車的西北農民……這種哲學附著在日常生活的恒定點滴中,也灌溉著中國的藝術和科學,他們熱愛自己的生活節奏,安逸,緩慢,知足,友善,也憎恨任何外力來破壞這種節奏,任何制度因素都無法將之剝離。在這裏,連傳授技術的語言和方式都會披上一層綺麗的文采和天命式的肅穆。人們將這種令人陶醉的神聖感稱之為道。
到了考察的後期,李約瑟一度迷上了道教,還給自己取了個道號。
摯愛魯桂珍說李約瑟後來好像變了一個人,,他不再像過去那樣固執,艱難的交通讓他習慣於遲緩,正好悠然欣賞一路的風景,他平生第一次享受無需按照日程表的悠然生活。
驚人的反轉由此發生:他本來打算按照西方的體例和邏輯來寫一套中國科技史,他帶了一面由苛刻學術訓練研磨成的鏡子,用來映照中國。最後卻發現那面鏡子也不是那麽可靠,因為他有了另外一面鏡子來作為對比,那就是古老的中國智慧。那麽,用這面鏡子是不是一樣也可以映照西方,正正衣冠,學學廉恥。或許,這面鏡子能夠反擊欲望早已過載,野心即將焚身的另一種生存邏輯?
這些念頭翻來覆去地重復多了,終於使他從一個探索者、求知者涅槃為一個智者,明白了科學不能以科學的面目單獨地出現。技術並不等同於真理,對技術的迷戀只會墮入道德的深淵:他需要的是一種整體的科學觀,也就是科學之道。
如果站在技術的角度中,只能永劫無間地比拼誰能制造威力更大的炸彈,那麽站在文明的角度,倒是可以得出更加公允的判斷和未來的樂觀。正如江曉原先生指出的,李約瑟來到中國本來是以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為考察物件,卻獲得了整個文明的大視野和思想觀照。
這就是李約瑟中國之行的精神收獲:他本來是帶著西方的評價標準前來考察中國,又反過頭來由中國的文化體系去判斷西方。比起李約瑟難題來,他引發的另一個難題其實更為重要,正如偉大的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在考察南美原生族群之後所感慨的:比起他們來,誰才是野蠻人。
這思想上輝煌的分裂並非瞬間形成的,他的中國朋友,助手,伴侶乃至【中國科學技術史】團隊的所有成員,都給了他巨大的力量和靈感。他在這四年的收獲,需要用整整一生去消化,而他的目標,在他去世後還在源源不斷地進行。
關於李約瑟難題,有一個說法是中國過早(先驗性)地將科技置於「和」的體系之內,而不是爭的體系之內(事實上能夠獲得生命力的中國古代哲學並無爭的一席之地),以至於近代無法誕生科學體系。「和」是中國的道德與節操,是中國的責任與風度,李約瑟在「和」「君子」「道」等概念中只度過了短暫的四年,卻目不暇接地體味著科技的責任和抱負,去體味文明的光輝與雕敝,和一個東方大國的廣袤內心——誠然,這些事情相對於科技要求的精確是難以量化的模糊,而且不接受實驗檢測,只接受個人體驗。但無論對於李約瑟還是我們來說它們都是如此重要:因為科技從來不是脫離文明束縛的飛艇,它是以一身人類裝束的方式體現著人類的風度,人類的行動和希望,還有人類之間的沖突與和解。
世界將取決於科技的價值,而並非科技的力量——這並非在貶低科技的效用,而是用古老的中國智慧去提示:科技將發揮出什麽樣的力量,究竟是生存還是淪陷,是更讓生活更奢靡還是更節制,是更幸福還是更苦難?這終將取決於人類的價值觀。
關於這一點,可以參照馮友蘭先生【為什麽中國沒有科學】一文來做最後的闡釋。馮友蘭先生此文發表於1922年,遠早於李約瑟難題提出的年代。他並沒有從正面回答「為什麽中國沒有科學」這個偽命題,因為這篇文章還有一個副標題,「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將科學問題納入思想問題中做整體的考量,將這個簡單粗暴的質問置於宏大的思想視野中予以解構。說是回答亦可,說是蔑視更為貼切:「如果人類將來日益聰明,想到他們需要內心的和平胡幸福,他們就會轉過來註意中國的智慧,而且必有所得。如果將來他們並不這樣想,中國人四千年的心力也不會白費。這種失敗的本身會警告我們的子孫不要在人心的荒原上再尋求什麽了。這也是中國對人類的貢獻之一吧。」(【中國哲學史補】,中華書局2014年4月北京第1版)
謝明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