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嘉樂(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來源: 【青年記者】2023年第2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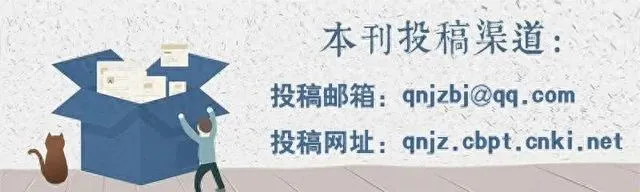
導 讀:
當人的生命終結,留存於網路空間的數位遺產溝通著生者與死者、生前社會與身後世界。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份,而生命已經變得數位化。數位時代人們在虛擬與現實交融的雙重世界中書寫生存的痕跡,數位化生存的神話似乎正在變成現實,催生著人們對數位化死亡新的思考。早在2012年,成立僅8年的Facebook身故使用者就已超過3000萬,據此推算,本世紀末Facebook上的生理死亡使用者將高達49億,遠超還活著的使用者。[1]當人的生命終結,這些以字節形式留存於網路空間的海量數位遺產該何去何從,越來越成為亟待解決的難題。
當肉身隕滅,物理痕跡隨時間煙消雲散,但逝者生前在傳播與互動中產生的資訊被記錄並流傳。數位時代,大數據技術使數據儲存達到新高度,社交媒體記錄著全新的線上連線,抽身於數位世界中留存記錄的「數位幽靈」還原身前社會的可能性越來越高。虛擬世界已經超越現實世界的映像與對應物,深度嵌入現實生活。當數位遺產高度復刻逝者的生前世界,生理死亡不再是生命歷程的終結,而只是一個節點。「數位永生」的理想激勵著學界對數位遺產的廣泛關註,相繼從數位延續(Digital Endurance Concepts)[2]、數位哀悼(Digital Grief Practices)[3]、身後管理(Death Management)[4]和數位不朽(Digital Immortalisation)[5]角度,探討生存與死亡視角中的數位遺產及處置理路,豐富了數位時代生存哲學的研究視域。
本文著眼於數位遺產的傳播價值,將數位遺產視作一種連線生與死的媒介,透過梳理數位遺產在溝通逝者與生者、生前社會與身後世界中產生的論爭焦點,希冀為數位遺產研究提供更多傳播學視角。
數位遺產的概念界定
厘清數位遺產的概念內涵與外延,是理解相關爭論的關鍵。檔案學側重數位遺產的文化內容,將數位遺產界定為「以互聯網為承載形態的文字作品、資料、圖片和影音,形成了一種文化傳承的遺產,為後人留下今日世界的數位化記憶」[6],更傾向於Digital Heritage的概念,多指民族特性、習俗、傳統方面的遺產。法學則強調財產內容,聚焦數位遺產繼承問題。傳播學者近年來也愈發註意到數位遺產問題,從媒介內容強調數位遺產的對話性特點,[7]考察作為媒介的數位遺產如何影響社會與文化機制,又如何改變資訊、死者與生者三者之間的關系與互動。
本文主要觀照肉身離世後以數位形態留存於世的線上遺產,對應Digital Inheritance意涵而非Digital Heritage。盡管其中包羅一些文化和知識的表達,但顯然上升不到人類的高度。因此,本文擇取法學對「數位遺產」的意義劃分,對數位遺產概念界定如下:數位遺產指主體死亡後遺留於線上空間或物理儲存媒介中,以數位形式儲存的資訊[8],包括帳戶密碼等存取資訊、有形資產、攜帶使用者行為及偏好資訊的無形資產以及後設資料等[9],具有經濟、情感和記憶三重價值內容。
生前世界的數位墓藏:主體性的可朽與不朽
數位遺產建構著逝者身後人格的主體性,這種主體效能否在肉體離場後繼續延續,是數位遺產是否可以被繼承的爭論焦點。
(一)數位遺產具有虛擬性
虛擬空間的開放性伴生著權利界定的模糊難辨,尤其是關於逝者帳戶資訊使用權與所有權的劃定問題。德國將數位遺產作為普通遺產來管理,在認證財產內容後即可繼承。但在波蘭,繼承者需根據與已故使用者線上平台簽訂的合約區分帳戶及數據的繼承許可權。由於數位遺產多為虛擬形態,相應的占有、使用、處分、收益過程具有獨立性,其儲存、傳輸、存取等均需經由平台和使用者多方。因此在權責判定中主要有三種觀點:一者,數位遺產應當歸使用者所有,平台和服務商只是提供存放與保管的場所,而無權私自處置這些財產,即社交帳戶所有權應為使用者享有;二者,網路營運方擁有數位遺產的所有權,使用者僅擁有部份由營運方讓渡的使用權,此觀點與當下的平台服務協定更為接近;三者,數位遺產並非應然屬於營運商或使用者,其權責歸屬取決於權利的正當性。
(二)數位遺產具有期限性
數位遺產的保存高度依賴於儲存資源和人類工作負載,將消耗大量的資源。大部份平台營運商仍采取定期清除身故使用者數據、限制數據存取時間等手段處理數位遺產。出於降低營運成本和提高營收的考量,平台營運商認為亡故使用者數據儲存占用過多的數據空間,無限期保有身故使用者數據嚴重損害互聯網企業的長期發展目標。同時,不設期限地劃定數位遺產處置權利容易招致不可控的私密問題,故而數位遺產處理多被劃歸於一定時限內的處理。
(三)數位遺產具有高度人身性
所謂高度人身性,是指數位遺產與被繼承人的人格利益有密切聯系,具有強烈的個體指向內容。
在「數位遺產第一案」中,約翰·埃爾斯沃思在兒子身亡後向雅虎公司申請兒子在雅虎網站的帳號和密碼,但被後者以根據服務協定帳號不可轉讓且這一行為會侵犯私密權為由予以拒絕。最終法官判決雅虎公司將逝者信件帳戶內全部內容燒錄在CD上交予家屬,但保留帳號的存取許可權。在本案中,支持觀點認為本判決符合逝者私密保護要素及遺屬利益,能夠彌補繼承人與平台之間的能力勢差。大衛·文森特則反對稱其忽視私密主體與涉他私密主體缺席的難度和普羅大眾的情形。[10]一方面,逝者是私密資訊的創造者,但遺屬並不一定參與其中。在未經逝者生前明確授權同意的情況下,盲目采取繼承模式,極有可能對逝者私密造成二次傷害,也失真遺屬的人格尊嚴。另一方面,網路中的私密資訊既涉及個人性私密,也有社交中產生的共同私密,亦即涉他性私密。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在2012年柏林女孩地鐵案中提出「高度人身性」的概念,要求Facebook授予過世女孩父母存取帳戶的權利,包括聊天記錄和私密資訊。法官認為,網路帳號也是遺產的一部份,數位遺產不應被區別對待,父母作為監護人有權知曉未成年子女的網路資訊。
著眼於數位遺產的經濟價值,數位遺產類同於現實世界中逝者生前的財富、自傳等作為陪葬品奠於墳冢前,是逝者生前世界的數位墓藏。數位遺產成為一種物質性媒介連通著生與死,是逝者身份的保存物,延續著逝者肉身離世後的數位主體性。對數位遺產的上述特征的不同解讀與處置策略,分別是對逝者生理離世後主體性是否仍能以數位形式存續、能夠存續多久、其逝後的人格權是否得到承認的回應。
生死之間的媒介通道:主體間性的聯結與阻滯
數位遺產是逝者與生者的關系載具,具有情感價值。
(一)跨越生死的情感聯結
網民的數位化生存痕跡在網路時代被記錄為數據或程式碼,形塑著網路世界永恒的意誌存在,具有物質與情感的雙重內容。數位遺產載寫著逝者與親友的生前互動與情感,親友亡故的沈重損失激發著在世者根植內心深處的與逝者繼續保持聯系的欲望。從攝影技術到通訊技術,人們長久以來一直在努力抓住新技術來實作這種聯系。[11]數位遺產取代了傳統葬禮成為數位時代新的紀念活動與哀悼儀式,逝者與生者得以跨越生死空間維系情感聯結與關系共在。
生者在接受逝者由臨終過渡到死亡的轉變時需要經歷喪葬儀式的過渡過程,在此之後,生者仍需在日常生活中度過哀傷期。一部份人清楚地意識到死亡的現實,將其數位遺產作為自身亡故後與在世者的思想紐帶。喪親者可以存取逝者在Facebook紀念頁面等平台的內容,與逝者對話,消除喪親的痛苦。[12]
(二)關系阻滯的負面效應
在哀悼時檢視數位遺物會帶來一種「復雜性哀傷」,讓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難以接受「失去這個人」的事實。讓留世者陷入高度的悲慟中,打亂原本正常的生活軌域和人際關系。沈溺於數位遺物讓他們在現實與虛擬的雙重世界裏閉門索居,漸漸阻滯關系,摧毀社群。[13]因此,一些人選擇「數位火化」(Digital Cremation),刪除所有線上生活的數位痕跡,希望在世的愛人重新開始他們的生活。[14]一位母親喪女後渴望孩子的Facebook資料永遠消失:「這堵‘哭墻’讓我太痛苦了……每每憶及往昔的快樂時光都會加重喪女之痛。」[15]
數位遺產高度分享又高度保密。平台方出於資訊保護與防止權威消解的目的建構起數位遺產與生者、生者與逝者之間的權責邊界。服務商限制或停止提供儲存服務將導致使用者數據消失,為生死關系的長久維系帶來諸多不確定性。當數位遺產的存貯期限結束,生前世界與身後世界的關系徹底阻滯,主體間性也逐漸消解。
數位遺產建構著逝者在生前世界、身後世界的主體性,這種主體性的流動表現為一種傳播關系。而數位遺產作為數位空間連通生與死的靈媒,為哀思者展開記憶的呼喚,傳達生者的回想與思念,將逝者的記憶轉向人間,搭建起生前與身後世界間的媒介通道,建構著生者與逝者、平台間的主體間性。
超越生死的數位來生:數位永生的技術想象
自秦始皇遍尋丹藥始,突破肉身腐朽、延伸生命長度一直是人類不倦追求的目標。基特勒在【留聲機、電影、打字機】一書中提示人們,媒介技術將人類的感知作為數據儲存到機器中,如同禁錮著等待被喚醒的「幽靈」,重塑著人們的書寫與感官體驗,不朽便在媒介景觀的更叠中流傳於世,不斷塑造著死亡的新媒介景觀。[16]
大衛·伊格曼提出死亡有三種形式:「一是身體停止運轉,二是屍體葬入墳墓,三是名字最後一次被人提起。」[17]被遺忘被視作死亡的最後一環,數位媒介和網路技術而「永不安息的逝者」(the restless dead)就是在超越死亡的終結。媒介社會正孕育著永生想象之火種,而依托數據儲存、復刻和媒介融合的數位遺產則燃起永生的希望之火,讓數位時代的死亡變得鮮活。生者借助數位遺產抵抗對逝者的遺忘,重塑逝者存在的意義,死亡在遺忘與記憶喚醒之間迴圈往復,成為一個動態過程。[18]數位遺產浪潮也衍生出數位資產管理服務、客製化線上紀念服務和數位遺產存檔服務等相關產業,用以解決逝者身後數據的使用控制問題,但數據內容本身並沒有發生質變。
當數位技術對認知世界的形塑能力趨於飽和,仿真人體技術再次突破認知壁壘,邁向數位化死亡的新景觀。基於人類在網路空間的海量數位痕跡學習,利用人工智慧和影像處理技術創造的模擬人體能夠以虛擬人形式模仿逝者生前的反應,提供視、聽、觸等直觀而又自然的即時感,讓離場的具身在技術時空裏繼續承擔其生命角色。
脫胎於逝者數位痕跡的虛擬化身正面臨諸多倫理質詢和技術挑戰:數位痕跡的保存與再利用方式是否正當合理,尊重已逝者的主觀意願?如何判定這些數位遺產的歸屬、使用與繼承權責的主體?離場具身的數位再生也帶來對生者的再創傷,傷痕在不斷觸及中反復提醒著哀傷的存在。數位永生在賦予此在追憶生命、釋放感情時,也一定程度上放大著某種悲情,更加令人難以釋懷。[19]生理的死亡和虛擬活躍的社會生存之間的二元論,定義著今天的逝者的地位。對於離世者而言,他們更傾向於拒絕讓渡自己的數位痕跡換取數位永生,而不是成為數位幽靈。[20]
結 語
數位空間的死亡經歷著「停滯」「消失」和「被遺忘」三個過程。停滯在現實世界體現為生命的逝去,主體性不能再發揮作用(Disabled);在網路世界則體現為數據不再更新,社交平台沒有本人的動態。消失包括資訊的消失與關系的消失。被遺忘指關於逝者的記憶消失,線上紀念活動就是為了抵抗這一消失。
身體會死,但數據可以永生。在數位化死亡的過程中,數位遺產成為一種技術靈媒,溝通著生者與死者,生前社會與身後世界,對死亡進行重塑與抵抗。數位遺產讓我們重新思考身體與靈魂、真實自我與數位自我、真實世界與虛擬世界之間的關系,數位永生更是這個時代的新神話,與此同來的卻是人文的噩夢。數位媒介推動普通人的死亡向數位化死亡轉變,不啻中介化逝者、喪親者與陌生人之間的互動,數位技術創造出的虛擬個體幻象更讓中介化記憶為數位化永生提供土壤。[21]面對這一極具誘惑力的神話,我們既要思考如何消解人類中心主義的桎梏,探尋技術具身下人與技術共生的可能;又要抵抗技術的過分蔓延,警惕數位文化的失範以及私密侵犯和「技術便車」現象[22]。
參考文獻:
[1]hman C J, Watson D. Are the dead taking over Facebook? A Big Data approach to the future of death online[J]. Big Data & Society, 2019, 6(1).
[2]Nansen B, Arnold M, Gibbs M, et al. The restless dead in the digital cemetery[J].Digital death: Mortality and beyond in the online age, 2014: 111-124.
[3]Blower J, Sharman R. To grieve or not to grieve (online)? Interactions with deceased Facebook friends[J]. Death studies, 2021, 45(3):167-181.
[4]Volos A. Digitalization of Society and Objects of Hereditary Succession[J]. Legal Issues in the Digital Age, 2022, 3(3): 68-85.
[5]Savin-Baden M, Burden D, Taylor H. The ethics and impact of digital immortality[J]. Knowledge Cultures, 2017, 5(2): 178-196.
[6]章戈浩.傳播與媒介研究的死亡盲點:一個生存媒介研究的視角[J].全球傳媒學刊,2020,7(2):21-34.
[7]陳剛,李沁柯.穿梭時空的對話:作為媒介「安魂曲」的數位遺產[J].新聞記者,2022(11):31-42.
[8]牛彬彬.數位遺產之繼承:概念、比較法及制度建構[J].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05):76-91.
[9]Haworth S D. Laying Your Online Self to Rest: Evaluating the Uniform Fiduciary Access to Digital Assets Act Note[J]. University of Miami Law Review, 2013,68(2):535-560.
[10]大衛·文森特.私密簡史[M].北京: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20:5-6.
[11][13][15]伊萊恩·卡斯凱特.網上遺產:被數位時代重新定義的死亡、記憶與愛[M].張渺,譯.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20:3,5;48;44-46.
[12]姜紅,胡安琪,方俠旋.生死界面:與逝者的數位「交往」[J].傳播與社會學刊,2022(62):69-103.
[14][20]Sisto, D. Online afterlives: Immortality, memory, and grief in digital culture[M].MIT Press, 2020:79.
[16][18]基特勒.留聲機電影打字機[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60,146,11.
[17]大衛·伊格曼.死亡的故事[M].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9:111.
[19]劉琴.生死疊合:離場記憶的情感仿真、擬化同在與數位永生[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2,44(09):33-42.
[21]周裕瓊,張夢園.未知死,焉知生:過程性視角下的死亡與傳播[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3,45(2):1-10.
[22]理察·揚克.機器情人:當情感被演算法操控[M].上海:文匯出版社,2020:1.
本文參照格式參考:
王嘉樂.在網上死亡還是永生?——生死傳播之間的數位遺產論爭[J].青年記者,2023(22):112-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