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這個初夏的夜晚,某些古老的禁忌被打破了,百年間的世界發生了一點點改變。一度禁錮的殿堂向那些曾經無法進入這裏的人敞開了大門,這個夜晚屬於她們,一群不給領導泡咖啡、更喜歡討論科學的女人。
文| 查非
我可不是來泡咖啡的
漫長的學術會議正在進行中,坐在現場的唯一一位女性發現總有人跟她使眼色,有的人瞪她,有的人沖她擠眼睛,還有人端起杯子跟她示意,她過了好一陣子才反應過來,這是在告訴她——現場沒有咖啡了。
在雲集了大科學家的會場裏,她不止一次接收過這樣的眼色。但是,她並沒有給他們泡過咖啡。後來,她養成了一種自己的應對方式,每當大家不約而同地望向她的時候,她就沖著他們微笑,提醒他們另一項事實:「啊哦,今天我來這裏可不是幹這個活兒的哦!」
說起這個故事的,是坐在我對面的是
熱內維耶芙·阿勒穆茲
(Geneviève
Almouzni),她是一個性格爽朗的法國女人,每次收到她的信,落款都是一個瀟灑的G。她講起咖啡往事的樣子,像在講一個笑話,事實上,聽到這個故事的感覺的確是在聽一個笑話——為了表彰來自世界各地的傑出女科學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每年評選「世界傑出女科學家」,由獨立的國際評委會從全世界350名候選人中選出來貢獻最大的五位女性科學家,代表歐洲地區、北美地區、亞洲及太平洋地區、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非洲和阿拉伯國家,她正是2024年的得獎者之一。她是一名分子生物學家,自1999年以來一直在居禮研究所主導研究。
也就是說,當她被丟眼色泡咖啡的時候,她早已是一名成果卓著的研究者。她發表過超過220篇論文,擁有5項專利,她所引領的研究揭示了蛋白質在細胞核內包裹DNA的過程,這對於如何理解發育、疾病乃至癌癥是至關重要的突破性發現。作為法國癌癥研究最重要的領軍人物之一,她能帶給科學界的價值遠比泡咖啡重要。
後來我漸漸發現,這個笑話竟然屬於絕大多數女科學家。期間我見到了另外幾位獲獎者,盡管文化不同、背景不同、性格不同,但當一個女人成為科學家,坐在會議現場的遭遇竟然驚人地相似,唯一的區別是在歐洲和美洲她們會被叫去泡咖啡,而在亞洲的版本是,你怎麽不給領導倒茶?
在初夏的巴黎,主辦方設計了很多環節——走紅毯,釋出會,聲勢浩大的頒獎典禮——讓更多人看到她們,重視她們,告訴世界,她們是科學的明星。這是一場科學界的頒獎典禮,也是一場別開生面的聚會,當全世界最聰明的五個女人坐在一起,沒有一句陳詞濫調能從她們眼前溜過去,她們總能敏銳捕捉到現實中的微妙偏差。正是她們指出來,女性處境並不總是在進步,在某些學科和地區,也存在著倒退。
五位科學家全部來自生命科學領域,但她們的視野並不局限於自己的小世界,她們會在討論中提出,雖然生命科學領域性別分布顯得更平衡些,但很多其他學科的性別差距並沒有被打破——在全球範圍內,女性在物理學研究生中的比例一直低於20%,工程學畢業生中的女性比例只有28%,而在人工智慧領域,女性僅占專業人員的22%。
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場活動發生在法國科學院,會場裏坐著來自世界各地的評委會成員,在頒獎禮前一天的晚上聆聽獲獎者詳述各自的研究進展。主持會議的是白發蒼蒼的知名免疫學家阿蘭·費希爾(Alain
Fischer),他讓出了主席台的位置,在全場的掌聲中,邀請女科學家們上台分享。
坐在台下看到這一幕時,我想起了另一個聰明的女人——瑪麗·居里。1911年初,就是在這個地方,當時的法國科學院評委會投票否決了她的院士申請,理由是法國科學院從未有過女性院士,當時參加投票的法國物理學家甚至斷言,「女人不可以加入科學院。」居禮的小女兒伊芙在寫給母親的傳記裏清楚地記下了當天的投票會,主持人召集會議時故意大聲說:「大家都進來吧,女人除外。(Let
everybody come in,women excepted.)」
正是在那一年年底,瑪麗·居里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她不僅是全世界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女性,也是全世界第一個兩次獲得諾貝爾獎的人,還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獲得兩個領域諾貝爾獎的女性。就在法國科學院否決她的院士資格的時候,她已經在其他五個國家的科學院當選了院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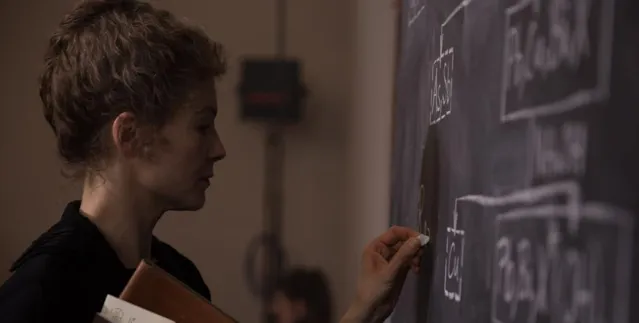
圖源電影 【放射性物質 】
100多年後的法國科學院,歷史在這個夜晚發生了小小的更新。幾位獲獎者依次分享她們的智慧,那是一個遠比咖啡和茶更有趣、也更有意義的世界:
——羅絲·萊克(Rose Leke)是非洲和阿拉伯國家得獎者,她今年77歲,作為一位免疫學家,她的努力大幅改善了非洲地區妊娠期瘧疾的治療效果,也為根除脊髓灰質炎和改良非洲的疫苗接種提供支持,她的存在也成為當地年輕女科學家的楷模;
——娜達·賈巴多(Nada Jabado)徹底改變了兒童癌癥的治療現狀,正是她首次發現人類疾病中的組織蛋白突變(oncohistones),引發了癌癥研究領域的根本性變革,她也因此成為了北美地區傑出女科學家代表;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科學家代表是顏寧,她的卓越研究推進了癲癇和心律不整等多種疾病的相關研究,並指導了疼痛症候群的治療;
——
阿莉西亞·科瓦爾陶希
(Alicia
Kowaltowski)長得非常瘦,但她最喜歡討論的話題是肥胖,坐在她旁邊可以聽她講上整整一天的「人到底是如何變胖的」。她所研究的粒線體生物學能夠幫助人類更好地理解能量代謝對於肥胖、糖尿病及衰老的影響,她的研究也讓她成為了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得獎者;
——歐洲得主正是G,她喜歡把DNA比作一張樂譜,她喜歡用不同細胞的不同樂譜來解釋她所領導的染色質動力學研究,如今的她是居禮研究所榮譽主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卓越研究主任,這裏也是歐洲最前沿的癌癥研究和治療中心。
主席台上的女科學家們神采奕奕地講述自己的研究,台下一次次為她們鼓掌。顏寧在開場白裏專門提到,環顧科學院的這個房間,墻壁上所有的紀念雕塑都是男性。而那晚第一個發言的恰好是來自居禮研究所的G,她的另一個身份是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的主任,這是在1926年諾獎得主讓·佩林號召改革法國科學體系後建立的一個科學組織,佩林是居禮夫婦的好朋友,他推動這場改革的原因之一正是為了破除居禮夫人所遭遇過的偏見。
在這個初夏的夜晚,某些古老的禁忌被打破了,百年間的世界發生了一點點改變。一度禁錮的殿堂向那些曾經無法進入這裏的人敞開了大門,這個夜晚屬於她們,一群不給領導泡咖啡、更喜歡討論科學的女人。

圖源電影【隱藏人物】
「直到現在」
我問了所有人同一個問題,你有沒有因為身為女性科學家而遭遇過偏見?不是過去,不是職業之初,不是幾十年前,而是「直到現在」——直到現在,直到你們已經做到了行業頂尖的位置,直到你們已經用研究成果證明了自己的獨特價值,你們是否還會遇到女性困境?那些煩惱在一個人走到頂峰之後,是否依然存在?
聽到這個問題後,她們都笑了起來,然後用不同的經歷告訴我同一個答案:當然存在,直到現在。
一個典型的例證來自2024年北美地區「世界傑出女科學家」獲獎者娜達·賈巴多(Nada
Jabado)。她的研究領域是兒科腦腫瘤,這是一條充滿困境的道路。這個世界上投身醫學的人很多,選擇兒科的是少數;研究腫瘤的人很多,能夠研究腦瘤的是少數,尤其是兒童腦腫瘤,全世界參與其中的人加在一起也是一個很小的基數。我想知道,為什麽她願意選擇這條少有人走的路,而她又是如何在一條窄路上堅持走到了最後。
她熱情地讓我稱呼她Nada,她喜歡穿有鮮明設計感的衣服,講旗幟鮮明的觀點,談話時常常暢快大笑,告別前熱烈地擁抱對方。她身上有一種蓬勃的生命力,和一種本能般想要迎難而上的勇氣。
我們的對話裏有許多的哈哈大笑,盡管她所講述的都是坎坷。Nada剛開始探索兒童腦腫瘤是在2003年,那時候她年輕、熱情、期望能做一番事業,但是十分孤獨。研究兒童腫瘤的人本就是少數,而更多人研究的是兒童白血病,因為白血病只要抽血就可以獲得檢驗標本,但是腦腫瘤的取樣非常艱難,當時幾乎沒有人知道路在哪裏。成人的治療經驗無法幫助兒童腦腫瘤的研究,它們癥狀不同,腫瘤生長速度不同,甚至連腫瘤長的位置都不一樣。如何取樣,怎麽用藥,沒人知道正確答案。那時候Nada總是碰壁,常常要發1000封信件,才能零星收到一兩封回復。
在這條窄路上,孤獨有時來自研究本身,有時是性別帶給她的。她去參加會議,分享自己的研究觀點,台下往往沒什麽反饋。過了一會兒,她聽到另一個人把她的觀點重新講了一遍,仿佛是自己的新發現,而台下的人也會應和,仿佛是第一次聽到這個觀點。這種情況一次又一次發生,更重要的是,這種經歷也曾經發生在G身上,我們開玩笑說,這是科學世界的「選擇性失聰」。

圖源電影 【放射性物質 】
孤獨貫穿了Nada職業生涯的全程,直到現在。Nada說,她也養成了自己的應對之道,就像G會笑著拒絕泡咖啡,她也會用幽默來對抗這種漠視。每次遇到這種狀況,她就站出來捍衛自己,「我很高興地發現,原來需要兩個人把同一件事說兩遍你們才能聽得到!」
我問她,真的有進步發生嗎?她想了想說,「還是有進步的。過去主席台上只有我一個女性」,她笑了起來,「現在有兩個。」
房間陷入了短暫的沈默。再次開口時,Nada講起了她的困惑,現在她覺得,公平是一個復雜的概念。在今天的科學世界裏,通常沒有一個人會公開承認自己歧視女性,但現實經歷常常讓你忍不住想,這是為什麽?她到一個亞洲國家出差,見證了當地一位女性研究員如何漂亮地完成了困難研究,輪到要公開發表的時候,上台發言的卻是她的男上司。這讓她感到不公平。但也有時候,她也見到過反例,明明把機會給到了女性研究員,對方卻沒有做好準備,自暴自棄地搞砸了一切,進而加深了對女效能力的誤解。在這個復雜的世界裏,帶給她困境的有時候是男性,有時候苛待她的恰恰是女性。想要追求進步,往往不是一條筆直向前的道路,裏面總有許許多多的曲折。
說起這些事的時候,她突然停下來問我,「其實我也對你很好奇,我想知道,你是怎麽樣走到了今天?你都經歷過什麽?」
坐在房間裏的我,某種程度上像是她們的影子。今天的科學界依然是男性占多數的世界,科學報道也不例外。正是因為如此,坐在她對面的通常是男性,坐在我對面的也往往是男性,走到最後的人很少是女性。我們對於彼此的存在都很好奇。和她一樣,我也會對自己的經歷感到困惑:當我寫了好稿子,別人評價我「寫得像個男人一樣」,這是誇獎嗎?同樣是報道突破性發現,大家問男性科學家是如何做到的,問女性科學家卻是讓她自證這個數據沒有造假,他們的提問不一樣跟性別有關嗎?我去參加科學決策層的會議,茶歇的時候兩個研究員跑來找我確認,「你是服務員嗎?」後來我才知道,我的存在讓周圍的人感到費解,他們不明白為什麽會有一個女性不去給領導倒水,而是一直記筆記。
我把我的困惑告訴了Nada,為什麽一個坐在科學世界裏的女性,大家會預設她會負責泡咖啡、倒水,預設她做不好研究、寫不好稿子?為什麽這種應當屬於上個世紀的想法直到今天仍在?為什麽此時此刻房間裏的她不能是一個跟你同等重要的研究者呢?
Nada聽的時候一直在點頭,「你的故事讓我很難過,因為我也經歷了一模一樣的事情。我有兩個女兒,我希望她們能夠活在一個新的世界,相信自己可以做任何事,不用被人當成男人去誇贊,不用被人忘記是一個女人。你知道我們應該做些什麽嗎?我們應當繼續走下去,走到最後,讓他們看到你的存在,看到活生生的例子,他們也會發生改變的。」
Nada把這個叫做「展現多樣性」。「當你看人類的DNA時,你會發現,它們本質上是一樣的,恰恰是那些我們不同的地方讓人類這個族群變得強大,人與人的差異不是互相攻擊的武器,它是一種證明,證明了多樣化是一種美,是真正的生命力。」
她的確做到了。她所領導的團隊在全世界最早發現人類疾病中的組織蛋白突變(oncohistones),這一發現徹底改變了癌癥研究範式。她的突變也被世界衛生組織納入突變裏,成為了全球範式。人們開始重視她的發言,雖然依然會有人選擇性失聰,把她的發言自己說一遍,但有時候已經不需要Nada一個人面對了,台下越來越多人會站出來糾正,「這一點Nada剛剛已經講過了。」
發生在Nada身上的故事證明了,女性困境很難消失,也沒有什麽特效藥,不管你選擇了什麽職業,也不管你晉升到怎樣的位置,這種苦惱可能永遠伴隨著你。直到現在,會場裏缺了咖啡的人還會下意識地望向房間裏唯一的女性;直到現在,依然有人在女性發言階段出現失聰;直到現在,依然有只屬於女性的天花板,其中一位參會者在考慮職業晉升的時候聽到的回應是不解和意外,「你怎麽還在考慮向上走?你現在這樣已經走到頭了,該知足了,上面是男人的位置。」
但是,重點不在於自己遇到了什麽,而在於你打算怎麽辦。這是我拼湊出的她們的經驗——她們在不同的年紀,不同的處境下,以不同的方式應對過。有的人會抗爭,也有的人會忍耐,其實並沒有標準答案。其中一位告訴我,現在的她會站出來反對,但她也忍耐過,尤其在她資歷尚淺、非常年輕的職業起步階段,面對冒犯時她也會笑一笑,保持沈默。因為那時候的她還不足以一個人抵擋一場沖突,更重要的是,那不是她的首要任務。現在的她可以選擇發聲了,她也覺得自己有責任為更多女性的處境發聲。
「重要的是,你要記住,當你遭遇了偏見,它並不是你的錯,這些偏見也不能左右你是一個什麽樣的人。這些偏見恰恰定義了對方的狹隘和無知。」她說,唯一能夠給你定義的是你自己。

圖源電影 【末路狂花 】
蓋一座新的房子
巴黎的夏天時常有雨,天氣也依然陰冷。這場女科學家的聚會行至尾聲,最後一項活動,是面向全世界直播的圓桌會議,她們再一次聚在一起,討論女性在科學界所遭遇的隱形偏見。
台上嘉賓剛講完「提高女性榜樣的可見度」,提問環節馬上有人站起來說,他也希望讓女性發聲,但現實中這根本辦不到,他說他參加高層論壇時發現演講者全是男性,他專門問過主辦方,對方告訴他,他們的確邀請過女嘉賓,可是「所有女人都拒絕了」,他把這種狀況歸結為「女性的領導力問題」,他的提問聽上去更像是一種考驗:「我想問在場的各位女性科學家,對這種會議級別很高、女性全都拒絕的情況,你們有什麽好辦法嗎?」
第一個回應的人是G,「首先,請問你們一共邀請過幾位女性呢?」
全場哄笑中,台下伸手比劃了一個四,G向觀眾攤了攤手,「我想你也知道答案了吧。」
緊隨其後的顏寧以更耐心的方式解釋說,「這個我也觀察過,像我們這樣較為活躍的發言者,往往會源源不斷地接到各種邀約,但我們的時間有限,不可能對每一份邀請都說Yes,也許你們應當發掘更合適的候選人。」五個人紛紛出主意,「方法很簡單,不要固守同一份名單嘛」,「要不要試著改掉陳舊的習慣,不要才找這麽幾個人就放棄,再努力一點吧」,「你們也可以大膽地邀請更年輕的人,她們同樣出色,很可能會有更有趣的觀點」……
這讓我想起了另一位得獎者,另一個堅持自己主意的女人。五年前,古生物學家張彌曼獲得了世界女科學家大獎,那時她在頒獎台上用英語、法語、俄語、德語致感謝辭,全場掌聲雷動,下台的時候她徑直走回座位,把獎杯落在講台上。回國之後,電視台請她去錄節目,現場有人問她,給您這麽大的獎,為什麽您下台的時候沒拿獎杯呀?那一年已經82歲的張彌曼直截了當地回答,因為我老了啊,老了愛忘事,所以就忘了拿啊。編導把這段掐了沒錄,讓人又問她一遍,給您這麽大的獎,最後為什麽沒拿呀?您好好想想。
那一年,我們是在她的辦公室講起這件小事的。坐在那間整整齊齊擺滿了草魚化石的辦公室裏,窗外是北京下了班的黃昏,張彌曼不服氣地講著,她是如何讓這段片段最後也沒播成的,因為她堅持自己的想法,不願意為了外界壓力改變,「他們想讓我說,我沒拿是因為淡泊名利。我沒說。我的確是老了所以忘了。我說的是事實。」
在今年的「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活動上,圓桌會最後一個提問來自一位正在求職的博士後。她說自己的面試總是不順利,人們總是要求她改變,一個基本要求是,「要像個男人一樣去說話」,要強勢,要敢下結論,要多強調自己的貢獻,但她不習慣談話時滿口「我,我,我」,也不習慣獨斷專行去下結論,反思和質疑才是她相信的科學精神。這種現實和理想之間的差異讓她困惑,她覺得自己能夠在科學的世界存活,靠的是「運氣」,但是她現在有了女兒,她不希望自己的女兒長大後想當科學家也得靠「運氣」,但她卻不知道該怎麽辦。
提問者說話的時候,台上的嘉賓全都在搖頭。Alicia第一個回答她:「你就按照自己的樣子講話就可以,做你自己,如果我在面試評委裏,我一定會聘用你。」
「但是他們沒有聘用我,所以,我想只能是我來改變。」

圖源電影 【漢娜·阿倫特 】
Nada緊接著解釋,「也許你會失敗一次、兩次、三次,但這並不是最重要的。你要記住的是,如果你不是真實的你,面試將永遠不可能有意義。一個偽裝的自己是無法在科學工作中存活下去的。也許你太想要假裝像男人一樣,那個真實的你沒有閃耀出自己的光。找工作並不容易,也許你應該更客觀地審視自己的面試,影響你的關鍵因素是否真的只是表達,也許你展現出了某種不適合工作的弱點,你去關註那些更值得提升的能力,這才是我們能做到的。」
G支持了Nada的觀點,「聽取批評意見是很重要的,但這不意味著我們要按照那些聲音去改變自己。你也可以反過來去改變他們,堅持自己的樣子,讓他們看到另一種可能是什麽。我們可以用自己原本的樣子去扭轉局勢。」
告別之後,我又重新去參觀了居禮博物館。在居禮夫人最喜歡的小花園裏,我回想起這五個人,想起她們說過的話。我在想,她們是靠什麽走到了今天,到底是什麽塑造了今天的她們。我開始意識到科學偶像這個詞的真正含義。我想她們能在今天走到頂尖,不是因為她們努力成為了誰,而恰恰在於,她們在這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上,一步步成為了自己。這個世界無數次教導她們變成另一種樣子,換個專業,改改脾氣,不要這樣跟領導說話,「像男人那樣」。她們能夠留在台上,恰恰因為她們沒有變,自始至終,她們始終是她們自己。
這是我在見到這五個人之後最深的印象——你可以以自己原本的樣子成功,你不必成為任何一個其他人。很多女性並非不優秀,只是在那些咖啡、哭泣、批評、選擇性失聰的聲音裏,她們沒能走到最後。這條路最大的阻礙其實是懷疑,懷疑自己是不是 足夠好 ,懷疑這條路是不是有出口。你會遇到很多困境,但你依然可以活下來,以自己的樣子走到終點。
科學會獎勵走到最後的人。直到今天,瑪麗·居里依然不是法國科學院院士,而她去世接近半個世紀之後,法國出現了第一位女性院士瑪格麗特·佩裏(Marguerite
Catherine
Perey),她正是瑪麗·居里的學生。得知獲得第二次諾貝爾獎的那一年,居禮夫人的身體狀況並不是那麽好,但她還是堅持去了瑞典的頒獎現場。她帶著自己的長女艾琳娜(Irène
Joliot-Curie),在那個輝煌的現場,女兒見證了母親面對質疑後的堅持。艾琳娜堅持了下來,成為了1934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就在居禮博物館的後面,是居禮夫人的小花園。她生前最喜歡的一件事就是從辦公室走出來,倚著欄桿看著花園裏的植物。她的花園因為她的存在變得特別,因為她喜歡不同,花園裏漸漸有許多她專門訂購來種子、精心培養長大的花。一個世紀過去了,花園裏如今開滿了鮮花,從居禮夫人的辦公室走出來,不同的花以各自的樣子綻放,這是一種復雜的美,就像這些發生在科學世界的故事,一些女性獲得了成功,以她們本來的樣子。
 「
世界傑出女科學家獎
」
的頒獎典禮上,五位女科學家和評委們一起慶祝。
受訪者供圖
「
世界傑出女科學家獎
」
的頒獎典禮上,五位女科學家和評委們一起慶祝。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