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荒」:不間斷的身心體驗
對「開荒」這個字眼,許多玩家應該都不陌生。它的原意指「在荒蕪的土地上面開墾」。「開荒」一詞較早出現在【晉書】中的【良吏傳】:「導化有方,督權開荒五千余頃。」陶淵明的五首【歸園田居】其一,「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應該是我們更加熟悉的詞源。隨著數位時代到來,電子遊戲取得了快速發展,「開荒」在遊戲中有了特殊的語境化的意味,它主要指玩家在新的遊戲環境、伺服器或副本中進行首次探索或挑戰的過程。
和現階段的一些快節奏遊戲或掛機放置類遊戲不同,「開荒」對時間、精力和隊友的要求更加嚴苛。玩家必須有固定時間、充足精力,身邊必須有靠譜隊友,才能完全達成「開荒」的目的。每一個有過開荒體驗的玩家應該都對那段經歷記憶猶新:和公會或現實中的朋友約好共同挑戰一個新版本的副本,開荒的過程伴隨著一次又一次的嘗試。玩家有時無功而返,有時滿載而歸,更多的可能情況是,玩家成功挑戰了副本之中的若幹BOSS,卻沒有完全透過副本。但這應該不成問題,因為這個副本中已經留下了開荒玩家的足跡——CD(Cooldown的縮寫,是一種重要的遊戲機制,它指玩家在完成一次副本後需要等待一段時間才能再次進入該副本的冷卻時間)。在下一周伺服器維護前的這段時間,玩家們可以繼續在副本中開荒。筆者至今還記得玩【魔獸世界】和公會隊友一起開荒太陽井、黑暗神廟和冰冠堡壘的場景。公會會長提前對需要挑戰的副本及其BOSS做「背調」,組織、安排具體的開荒事宜,包括副本小怪、BOSS技能、各職業如何配置才能提升開荒效率。在開荒過程中,會長還要提醒隊員須註意的地方,在「重復死亡」的過程中還要扮演心理咨詢師調節某些隊友瀕臨崩潰的心態。而在一些難度較高的團戰中,外掛程式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讓玩家規避一些可能導致減員甚至團滅的風險。在一次又一次的嘗試之後,團隊成員形成了一定的默契,伴隨著副本的最後一個BOSS倒下,開荒也告一段落。
「開荒」一詞可以非常形象地形容玩家對於未知副本的挑戰,副本是荒地,開墾者即是玩家。如果人們希望荒地變為沃土,不花費時間精力在這土地上面是不行的,遊戲開荒亦如是。在正常的遊戲設定來看,遊戲的時長和開荒順利與否呈正相關,人們在開荒中花費的時間越多,取得的成效就越高。相信有玩家或多或少會在開荒過程中冒出過這樣一種想法:如果可以一刻不間斷地開荒,那該多好。確實有玩家這樣做了,他們認為大型多人線上遊戲(MMORPG)的魅力就是開荒。所以他們沒日沒夜地開荒,但是這樣會對人的身體健康造成極大的消耗——人的生理總會有極限,隨著陣陣困意襲來,玩家只好稍作休息。
對於能一刻不停進行開荒的渴望,不由讓我們聯想到克賴瑞的一本小書——【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在書中,作者強納生·克賴瑞向我們描繪了一種極端情況——7天24小時不間斷工作的場景。書中提到:所謂「24/7」是一種由資本擴張引發的常態,一個重要的特征是,「人類生命大體上已經被裹挾進了沒有間歇的持續狀態,不停地執行就是其準則」。並且「這種時間不再流逝,處於時鐘時間之外」。[1]這個場景在形式上和開荒類似:都要求一刻不停,都需要高強度地進行身心活動。盡管遊戲中的開荒和克賴瑞所說的「24/7」仍有差異,但這些說法卻可以為我們理解開荒中玩家的身心體驗提供有益的參考,我們的討論也從這裏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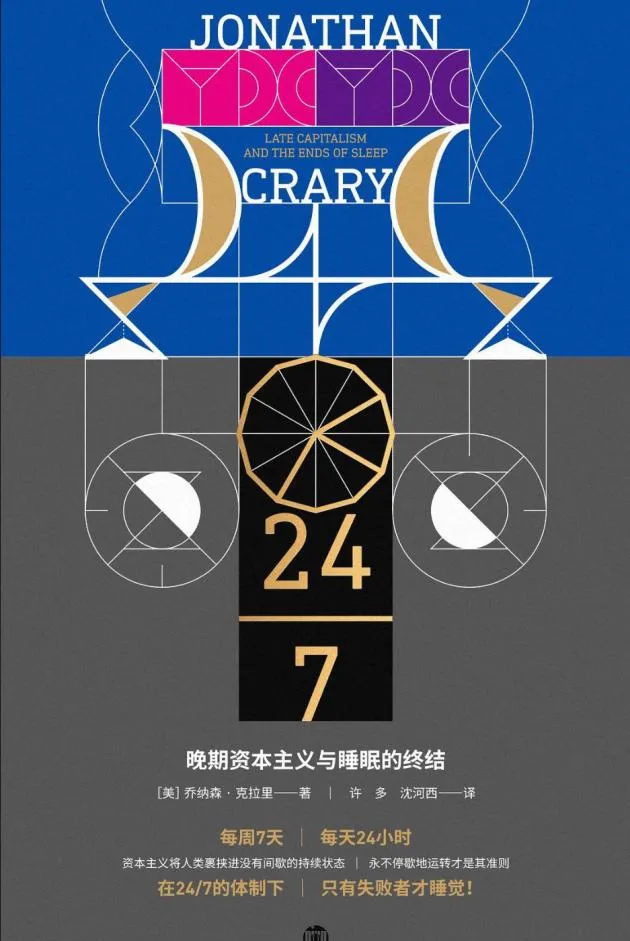
強納生·克賴瑞:【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
開荒中的「時間」與「主體性」問題
如果詢問一個玩家,「開荒」是什麽?那麽大概的回答會是「重復」以及類似的話語。從表面上看,或者說從一個客觀的視角來看,開荒就是玩家重復進行透過關卡的嘗試,其間伴隨著不計其數的失敗,是一個「嘗試-失敗-再嘗試-成功」的過程。不同的是,前三個環節是過程,而最後一環是結果。此外,玩家事先並不知道在前三個環節需要耗費多少時間——影響成功的要素太多了:對遊戲本身的理解,自己的狀態,隊友的狀態,電腦、網路是否正常,甚至諸如BUG等偶發因素,都會在不同情境下影響開荒的結果。這使得遊戲本身超出了如艾布拉姆斯【鏡與燈】裏所談的那四個要素——作者、世界、作品與讀者,成為了在文本敘事層面之上的互動媒介。
在克賴瑞看來,「重復」所對應的概念應該是「24/7的無時間性」。圍繞著這種無時間性而來的是「同質化」以及「人類生活世界」和「開機後的世界」發生沖突等情況——「24/7」抹掉了任何暫緩期限和變幻不定的重要性或價值。[2]在開荒時,我們每個人看上去都和機器一樣在高速運轉,做著似乎是千篇一律的事情。一旦開荒的戰鬥打響,現實世界的一切似乎都已和玩家無關,玩家所進行的是屬於遊戲世界的活動,經驗的是虛擬世界的事件。對於可以進行「24/7」不間斷開荒的渴望則進一步弱化了玩家對時間和空間的感知。不僅如此,這種弱化還會讓潛意識中的一些內容不自覺地散溢到現實之中,做出一些讓旁觀者看來「匪夷所思」的舉動:手裏捧著泡面,目光緊盯著螢幕,生怕指揮「點名」時,自己因不在而被「踢出」開荒團隊;因為隊友的一次失誤導致BOSS血量剩下1%而滅團,不禁破口大罵,久久不能平靜;開荒成功之後拿到自己心儀已久的裝備而高興得手舞足蹈……如果你去網咖觀察一陣,以上所說的事情似乎是較為常見的。而玩家對時空感知的弱化進一步導致了主體性在一定程度上的懸置。
對於這些活動,玩家給人最直觀的印象是「忘記了自己是誰」,他們對於自己的認識在某些時候變得模糊了起來。一個平時很冷靜的人可能會在遊戲中大發雷霆,甚至是變了一個人。傑米·馬迪根(Jamie Madigan)就探討了玩家「糟糕的」遊戲行為,他認為玩家在遊戲之中會出現「去個體化」的情況,一方面是減少的社會責任感——「你看不見我」,另一方面是削弱了的自我審視——「我看不見我自己」。[3]前者部份歸咎於匿名機制,後者則源於在遊戲中因長時間付出而帶來的亢奮、沖動的情緒。馬迪根關於相關問題的解決方案似不屬於本文的探討範圍,但他所談「去個體化」的問題實際上足以引發我們的思考,讓我們在對「去個體化」的認識當中反思自身在遊戲體驗過程中的主體性問題。

【魔獸世界】副本開荒
「開荒」中的「時間」與「主體性」之思
(一)差異化的時間體驗
遊戲開荒,對個人而言是時間的消耗,但另一方面是點卡(網路遊戲常見的計費卡模式。全稱為「虛擬消費積分充值卡」,是一種用於遊戲充值的卡。玩家透過購買點卡,獲得相應的遊戲時間、虛擬貨幣或其他遊戲內資源)的消耗。從個體來說,開荒滿足了玩家主體性的確證,但從另一個角度,玩家多體驗遊戲,最開心的當然是遊戲開發商。資本迫切需要增殖,數位資本自然也樂於看到玩家在遊戲中進行越來越多的消耗,甚至是永久性的線上,24/7的時代「使無間歇、無極限的工作觀念被認為是合理的,甚至正常的」。[4]遊戲會不斷激發玩家的欲求,它透過關卡設計、畫面設計甚至情感設計,試圖將玩家「安排」到一個業已圈定好了的框架之內,讓即便是「高玩」們自以為的「盡在掌控」也變得「盡在掌控」,看似自由的操作早已被納入「無處可逃的自我管控」,而陷入一種「選擇和自治的幻覺」之中了。[5]
克賴瑞對於電視上癮的描述與總結可以說十分精彩,在他看來,電視沒有辦法讓人從快速麻木中得到滿足,「你會慢慢滑向一種空虛的狀態,然後發現很難再從中抽離」。對於技術產品的上癮,讓人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無悲無喜的放空狀態,幾乎感受不到任何情感張力」。他後來對於暴力電腦遊戲的論述說,它「很快導致你的反應變得千篇一律,不再能感到愉悅,只是被一股重復的力量驅使著,反復做著同樣的事」。[6]這一方面對於防止遊戲沈迷自是起到了警示作用,但這不禁讓我們思考,如果電子遊戲真的是千篇一律,大家反反復復做著毫無差別的事情,又如何能開荒成功呢?彼此形成的「默契」又在哪裏呢?
答案是:時間。柏格森曾經用音樂對「綿延」概念的進行描述。簡而言之,我們不是突然就感受到音樂的美的,我們在「這個時候」感受到的那個音符如此的動人,是因為這個音符之前所有音符的鋪墊。誠然像【命運】【拉德斯基進行曲】等似乎有一種一下子就把人抓住的魔力,但不可否認的是,許多交響樂更加符合起承轉合的敘事邏輯,讓人在音符的積累過程中逐漸獲得審美體驗。回到我們對於前面問題的論述,24/7的時代是沒有人情味的,在這個「永恒的狀態」之下,人的生命動力變為了工具內容,因而它是冷漠的。如果從遊戲本身的執行機制來看,它的確迫切地需要貫徹其「不停執行、沒有間歇的準則」,它處於一個「機器世界」當中,它本身也是一個「機器世界」。但玩家的參與讓這一切發生了改變。也許遊戲可以被操控,遊戲中的體驗也能被操控,但是玩家實際上可以在遊戲之中自由活動,他們的自主參與使得遊戲時間成為了一種「有鈍感的、綿延的時間性」,也讓開荒成為一種並非完全無法暫停的狀態。開荒看上去當然是在反復做著同一件事,許多難度很高的關卡都需要玩家經歷成百上千次的嘗試才能透過,而這種嘗試自然首先是一種重復。我們和他人討論開荒的過程,最常提起的就是「次數」,次數直接相關的就是實體層面的時間——20、50、100個小時,甚至更長。但這種口頭上的描述真的是全部嗎?當然不是。在BOSS倒下,開荒成功的那一瞬間,除了時間以外,還有玩家在開荒過程中產生的各種體驗:好奇、憂慮、謹慎、激動等。這些情緒構成了玩家們情緒的匯聚:加深了對副本、BOSS情況的了解,強化了對自己職業的理解,與隊友之間的配合也越來越默契。這些不是簡單的次數、小時數能反映出來的。真正決定最後結果的,是在時間之中發生的上述「改變」的積累——這像極了綿延時間產生的效果。「還有時間存在」也許是更好的形容。
換句話說,是不是所有人經過「100個小時」或更多次數的開荒就一定能透過關卡?不一定是這樣。舉一個在【魔獸世界】中常見的例子:開荒成功後的第2周,2團牧師有事出去了,從1團「借調」過來一個經驗豐富的主力牧師,這周的副本卻非常不順利,大家發現這個牧師對團隊情況很不熟悉,一些原來團隊成員看起來非常容易的任務,在他那裏卻要大費周章,可是這位治療者明明是已經跟著1團一直從開荒打到速推的,他在開荒過程中的時間以及經驗遠比2團任何一個人都多,這就能夠說明一些問題。從表面上看是這位剛來的團員不熟悉團隊情況,和其他隊友無法形成「默契」,但默契的關鍵是什麽呢?是彼此之間在心靈上的共在體驗,是長期在遊戲之中形成的情感及「心流」的交匯,這些都需要長時間的積累。更需提及的是,這100個小時應該說是充滿差異化的,且不說玩家會在這100個小時的現實中有著這樣那樣的境遇,對於遊戲的理解不僅有對文本的體驗,即「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萊特」,還有沈浸體驗以及互動體驗等,這些體驗交織在一起,又由遊戲時間為媒介連線到了一塊,主體的體驗在時間之中發揮著作用。那麽,對遊戲差異化時間問題的思考似乎就成為了激發主體性之思的契機。
(二)主體性問題的解決——一個美學維度
在克賴瑞看來,睡眠具有深刻的「曖昧性」,因而無法被操控以及被工具化。在佛洛伊德構成作者主體的「我」之中,作者的虛構和想象被認為是「白日夢」。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夢」原本應該是在夜間發生,是曖昧性發生的正常場合,但作家及其作品當中被認為是虛構和想象的成分卻在「光天化日」之下顯現了出來。可是,虛構並非虛假,想象也絕非空想,它們都是有著對於現實的典型性的關切的——「成功的文學虛構制造出的形象體系遠比日常生活集中、凝練、扣人心弦」。[7]如果我們接著現象學美學的角度來看,審美被茵加登、塔塔爾凱維奇等人視為一種間歇性的夢,即審美本身是一種或專註或做夢的狀態:「美感經驗或許是夢想與專心的綜合,或許單獨是夢想或專心。」[8]遊戲中的藝術元素便能夠達到這一目標,筆者在拙著中就談到了彩蛋「是一件精心設計,有明確意圖的藝術作品,可以激發人們的情緒,並且以多樣的形式激發著人們的不同情感,甚至可以讓人感到震驚」,並且有著空間美學和情感表達的審美意味。[9]而開荒則更是交織著「理智態度」與「感情態度」,雜糅著「主動姿態」與「被動姿態」。盡管對於心理分析和現象學來說,如「潛意識」、「懸置」等說法仍然存在一些爭議,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在審美過程中的確有復雜的主體性存在其間。過去我們一度認為,我們需要用理性來時刻提醒自己不要脫離現實,同時用感性和情感來感受看似虛擬的遊戲,但同前文所說,當虛擬與現實的關系在主體性中復雜地絞合在一起時,現在我們是否能夠認為,遊戲當中也既存在著清醒的操控,同時也存在著曖昧的抵抗呢?與此同時,遊戲又能否同睡眠一樣,成為克賴瑞口中「碩果僅存的一道屏障」?[10]
從美學維度來思考主體,還會很容易地延伸到梅洛-龐蒂所說的「身體-主體」的層面。美學有著超越的維度,這種超越不是一蹴而就的,超越至終極的「生命意義」的現實基礎是存在者不斷尋求並持續獲得的意義的點滴,再具體明白甚至「俗氣」一些則是眼耳鼻舌無時無刻不在對五色、五味進行著的搜尋。在這個過程中,一系列問題出現了:好吃是什麽?好看是什麽?這讓我們一下子想到了一個在句法上具有同構性的問題——「美是什麽?」可理念和先驗的維度對於理解具體問題來說並不是萬試萬靈的,常見的情況是,人們只有觀看到、觸摸到、聞到具體事物,這些問題才清楚明了了起來,生命意義亦如是。
在體驗遊戲的過程中,人們會獲得不同的感觸:遊戲的音樂、畫面、劇情敘事都在透過不同方式達到讓玩家獲得一部份生命意義的目的。那麽遊戲便為「生命意義」這個本來難以把握的問題提供了一個具體的落腳點,讓它在某個或某些層面被觸及。當然,和主體性相關的問題也隨之而來。很多人認為,命運應當完全由自己掌握,但生命中確實有一些東西是個人無法控制的。同時也應該認識到,有太多人的生命如浮萍般不定,卻也有看似脆弱的生命仍舊以堅強的意誌抗爭著命運。可以說對於主動/被動問題的探討也代表著人們對於生命意義的追問。遊戲中同樣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玩家自以為是主動的行為實際上早已有了被設計好了的註定的結果,而一些看似是無意識的、不在規定動作之內的、充滿偶然性和事件性的行為卻是主體性力量的展現。開荒似乎呈現出了更加復雜的情況,一方面是遊戲裏業已確定好了的副本路線、BOSS技能和裝備掉落,另一方面是成千上萬的團隊玩家為了達成目標而在過程中絞盡腦汁地「各顯神通」。
用一個現象就可以解釋這個問題。不少老玩家為什麽總說「我更喜歡開荒,不喜歡速推」?他們當然不是為了「找虐」也不是喜歡「受虐」,而是因為,當一切還處於主體層面的未知狀態時,是有無窮無盡的可能的。從齊澤克的角度來看,開荒作為「事件」的發生,是具有完全的偶然性的。當進入速推階段,一切都處於完全可知的狀態時,不少玩家也授權以更加切身地明白他們正在「被操控著」,因而會產生和開荒200次還沒有通關的那種沮喪完全不同的倦怠情緒(後者同時也是許多遊戲最終衰敗的命門)。這個問題從主體性上說是可以理解的,盡管如果從宏觀視角上來看,無論是開荒還是速推,好像都是被操控的過程,但相對主義的答復並不能一勞永逸地解釋主體在不同過程的身心體驗。有一點是確定的,開荒過程也是一個「似被動的主動」與「似主動的被動」交織在一起的過程,如同審美過程中審美主體與審美物件的那種互相交融、難以割舍的關系一般。這不由會引發思考:這個過程是否可以成為人們探尋生命意義過程的恰切隱喻?能不能說,開荒讓人們在遊戲中的主動性發揮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甚至是極致?
余論
最後,不妨引入筆者的親身經歷。在筆者的開荒經驗中,有兩位記憶猶新的團長。一位是ID叫「高哥」的團長。由於開荒時團隊成員很容易產生情緒波動,他特別擅長緩解團員的心理焦慮,他喜歡說的一句話「夥計們,心態啊!」包括筆者在內,有不少公會成員後來都和他成為了現實中的好朋友。後來我們知道,他現實之中有過豐富的人生經歷和工作經歷,能夠讓他以一種不同的視角去看待遊戲當中的問題,對於開荒,他的理解大概是,「包括開荒在內的遊戲問題都是人的問題。」
另一位是魯姓大哥,和前面的情況完全不同,他在某遊戲公司工作,並且還參與遊戲的設計和開發。他在開荒之前對於攻略的理解非常到位,總能非常「精準」地預測到BOSS要施放的技能,並提出如何應對。他總說的一句話是,「如果要我設計,這裏的技能應該是這樣的……」。進入他的團隊,團員似乎總能比較高效地完成開荒。現在看來,他們對於遊戲的理解似乎是對前面問題的一個集中概括:開荒究竟是一個什麽過程,是對遊戲機制的外部剖析還是人本身的內部理解呢?二元論的觀點能否一勞永逸地解決身心體驗的問題?依照傳統的二元論,如果單純理解遊戲機制,人的作用似和工具無異,而如果意識到自身的情緒問題而加以調整,人即「作為意識存在」。在身心一元論的角度上,梅洛-龐蒂強調身體和意識之間無法分割的關系,他提出了主體的具身狀態,指出「我是我的身體」,他不僅把身體、意識同現實生活聯系了起來——「除了體驗它(身體),即接受貫穿身體的生活事件以及與身體融合在一起,我沒有別的手段認識人體」,還將個人的主體性同個人與他人的主體間性聯系到了一起。對於「開荒」而言,玩家個人第一次進入到遊戲、意識到有他人存在,並開始和他人進行合作,就逐漸將自己的意向傳給他人,遊戲世界在我與他人面前共同呈現了出來,這「模棱兩可的存在方式」以及關系「都隱隱約約地重新處在和包含在一個唯一生活事件中」。[11]開荒中的身心體驗實際上亦可以被視為身與心在時間、審美和他人之間發生的一種並無特定指向和固定方式的身體與心靈的融合。
最後須指出的是,我們當然不應過分誇大「開荒」的作用,在一些人看來,「開荒」所帶來的毋寧說是身體的嚴重消耗甚至透支,有相當一部份源於虛榮心的滿足,源於無法言說的欲望,因而不少人會產生「24/7」的遊戲沖動。但在遊戲當中,我們也的確會看到在開荒過程中、在設計者與玩家之間發生的第一次碰觸,它是一個開始,讓玩家在有限的時間裏體會到無限的意味:開發者的良苦用心,遊戲之中的多樣化的美感,以及也許短時間裏都不太會在現實中了解到的那些生命法則……
這麽說來,也許「開荒」所「開」的,是身體與心靈的「荒原」。而又如克賴瑞在另一部著作——【焦土故事】當中所擔憂的那個要點,即人類的如同情心、愛和痛苦等情感體驗及其具有的「獨特性和不可言說性」[12],是否亦能透過「開荒」過程中的身心體驗來加以維系?
參考文獻:
[1] 強納生·克賴瑞. 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M]. 許多、沈河西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12.
[2] 同註釋1,第46頁.
[3] 傑米·馬迪根,鄭博航. 為什麽謙和的人在遊戲中會變得狂躁[J]. 文化藝術研究,2023(04):74-82+115.
[4] 同註釋1,第16頁.
[5] 同註釋1,第66頁.
[6] 同註釋1,第121-122頁.
[7] 南帆. 文學批評手冊:觀念與實踐[M]. 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148.
[8] 瓦迪斯瓦夫塔塔爾凱維奇. 西方六大美學觀念史[M],劉文潭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385
[9] 見拙著【遊戲美學研究視域下的個案分析】,北京:九州出版社,2024:97-102.
[10] 同註釋1,第105頁.
[11] 莫裏斯·梅洛-龐蒂. 知覺現象學[M]. 姜誌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257.
[12] 強納生·克賴瑞. 焦土故事[M]. 馬小龍譯,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113.
*本文系山西省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計畫「遊戲學視域下的數位美學研究」(2023W126)階段性成果。
王齊飛(文藝學博士,太原師範學院文學院講師)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