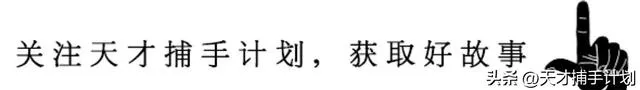
你上學的時候挨過老師打嗎?
我挨過,還不止一次。
我初中有個老師,是全地區優秀教師,因為帶出來的班級升學率奇高,但她有個特點,就是特別愛體罰學生,班裏沒人沒被她打過。
不是意思意思的那種體罰,而是真正的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摧殘。
拿鐵尺子打手心,用手擰大腿根都是輕的,記得有一回上課,當著全班的面,她薅起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的頭發,把兩個人的頭重重撞在了一起,只因為上課聽寫,這兩個人都沒默寫出來。
撞擊聲發出來的時候,所有人都傻了,包括我。
有學生家長告過,但學校只是給被打的學生調換了班級,老師卻沒被處分,大概是學校和其他家長都覺得,只要學習好,老師的管理手段不重要。
但老師打人真的只是為了學生好的一種手段,而不是發泄自己內心的暴力嗎?
不僅是老師,在親密關系裏,濫用暴力也會被各種借口粉飾,由此產生的一些結果,讓人後怕不已。
獄警白參曾管理過一個犯人,就喜歡打孩子。他在冬天讓兩個女兒滾出家,用火鉗燙大女兒後背。而當地人都習以為常,沒人去管。
只有孩子知道自己生活在暴虐的陰影中。為了逃離這種生活,大女兒制定了一個大膽的反抗計劃。
9歲的染染站在山頭眺望山間重現的綠意,她剛剛度過人生中最寒冷的冬天,那年冬天父母雙雙入獄。
她一度以為,逃出了父母的虐待後,噩夢就結束了。

我第一次見到染染是在深山老廟中,她和一位僧人一同生活。
那是2016年的中秋節前夕,山中秋意已深,柿子、核桃、紅棗等山中野果沈甸甸地掛在枝頭。偶有涼風吹過,會有黃葉翩翩起舞。
我們轉過一個山坳,又穿過一片森森樹林,終於見到一個遍布雨銹的寺廟。
門頭漆字斑駁,依稀能看出「火神廟」三個紅色大字。兩扇殘缺的木門歪歪斜斜地敞開著,台階布滿青苔,細膩濕滑。整個寺廟仿佛被神佛遺忘一般,孤零零地立在那裏。
我們走進去時,染染正坐在院中,對著一大盆衣服奮力揉搓。看見我們進來,她興奮地從凳子上跳起,濕噠噠的小手在衣服上胡亂抹了幾下,跑過來一把抱住一位同事的腿,親昵地蹭了幾下腦袋。
染染的表現讓我有些意外。這哪裏像一個11歲、童年受過重大創傷的小女孩?我心裏默默把這一切歸功於青燈古寺的熏陶,和收養染染的僧人的教導。
染染父母入獄後她就跑到廟裏,銷聲匿跡近兩年,直到被我們監獄和向陽之家的人找到。向陽之家是專門無償代養服刑人員子女的公益組織,和我們監獄建立著長期合作。
向陽之家的人多次嘗試勸服染染下山,都被染染和僧人拒絕了。向陽之家只好慢慢接觸染染,不時去山上看望她。而這是我第一次隨同前往。
方一踏進門檻兒,迎面而來的便是一尊怒目猙獰的火神像,背生六臂,高舉長劍,居高臨下的向下怒視。左右紅漆對聯,上聯掛:高舉天上正義火,下聯曰:燒絕世間不良人。
這恐怖莊嚴的場景和言辭狠惡的對聯,不禁讓我心中惴惴。
和往常一樣,染染還是反復強調,自己在這裏過得很好,不用一直來看望,「幹大(大讀二聲,幹爹的意思)對我很好。」
一個僧人怎麽能變成了染染的幹爹?
從廟裏出來後,我們帶染染下山,去到了十幾公裏外的鎮上,染染才算釋放了孩子的天性。
在我們一行人的陪伴下,她在街上好像出籠的小鳥,雀躍不已。東瞅瞅西逛逛,仿佛來到了大觀園。
但面對一切需要消費的活動,她統統拒絕,並且搬出一堆正經的理由,遊戲機使人沈迷、溜冰場烏煙瘴氣等等。
下午四點,向陽之家同事打算買些菜,讓染染帶回去。方一走近市場,便見門口的攤主們和染染熱情地打著招呼,「染染,好久沒見你們出攤兒了呀,位置還給你們留著呢,你姐姐呢?」
聽到有人說姐姐,染染一下子情緒黯淡下來,默默尾隨著我們,一直到購買完東西,也未發一言。

染染和姐姐是重組家庭的姐妹,這個重組家庭的父母非但毫不契合,反而是火星撞地球。
染染的母親是村中出名的潑婦,好賭博。在她又生了一個兒子之後,母女倆都被父親趕出來了。
那時染染7歲,母女倆漂泊無定。後來經媒人介紹,母親嫁給了繼父。
連最簡陋的結婚儀式也沒有,染染和母親就來到了新家。用繼父的話說,「咱們都是二手的了,還整那沒用的幹啥」。
繼父,年近四十,有點謝頂,後背微微佝僂,看起來像老實村民,其實是個暴虐的酒鬼,沒多少清醒的時刻。
每次喝醉後,他都向孩子發脾氣,稍不如意就對染染一頓打。母親也不管。
不過幸運的是,在黑暗的歲月裏,命運給染染漏下了一絲光,就是她新結識的姐姐。
染染第一天來到新家,吃過第一頓團圓飯,正要收拾碗筷抹桌子,卻被一雙粗糙有勁的小手攔住了。
「你放著別動,家裏這些事兒都讓我來,你快看書去吧,看書才是小孩子的事兒。」姐姐說話像長輩一樣,但只不過比染染大4歲。
姐姐叫彩妮兒,枯黃的頭發隨意挽著一個馬尾辮。面容清秀中帶著幾分粗糙,眼睛裏總是透著光,身材單薄卻帶著倔強的力量。
之後,姐姐承擔了家中大部份的家務,也忍受了父母的大部份打罵。
但忍耐帶來的只是變本加厲的打罵,姐姐開始因為越來越碎瑣的事挨打,比如飯做晚了、豬又瘦了、喝酒回來飯放涼了等等。
姐姐也有求助過鄰居。起初她大聲的哭喊會招來鄰居,但鄰居的到來不但沒有改善境遇,反而讓父親下手加重,鄰居也被罵走。
村中打罵孩子很自然,「莫管他人事,各掃門前雪」是再正常不過的村中契約,沒人覺得這是個大問題。再加上吃力不討好,總被這對父母罵走,鄉裏最後也不再勸慰,只是對這姐妹保有一份同情。
久而久之,姐姐便不敢再奢望鄰居的幫助,而是自己想辦法改善境遇。
她帶著妹妹,利用空閑時間掙錢,比如上山采藥材、野果到市場上賣,或者給市場攤主打工。她們用賺來的錢補貼父母的酒錢和賭資,能少挨一點打。
每個清晨,姐姐會備好一家人的飯,騎著自由車帶著染染上學。一路上姐姐大方地和村民們打著招呼,笑著應對大家的誇贊。
通常是在不斷的「彩妮兒越來越懂事兒了」之類的誇贊聲中,兩人騎車疾駛出村莊,奔向鎮上的學校。
出了村子,騎行在鄉間的林蔭道上,姐姐就會放下老成的面孔,像孩子一樣放聲唱歌和大笑。陽光把姐姐枯黃的頭發映成了光絲,偶爾掃過染染的鼻子,有些微微發癢。
姐姐還會突然加速嚇妹妹一跳,炫技失敗時兩人只得跌入草窩。
一陣嬉鬧後,染染總會瞥見姐姐衣服下面逐漸密集的淤青。
染染後來才知道,姐姐之所以能忍耐,是因為心裏在醞釀一個反抗計劃。

在每個周末售賣瓜果藥材的收入中,姐姐都會預留一部份存起來,用作兩人的「逃跑資金」。兩年來,已經存了差不多五百塊。
而且姐姐在打零工的時候,也已經打聽好了路線,對附近的大城市有了初步的了解。
兩年內姐姐從來沒有向染染透漏這個計劃,直到那個冬夜,父母的無情讓姐姐徹底寒了心。
夜晚來臨前,姐妹倆拎著雞蛋準備回家做飯,但妹妹卻把雞蛋弄破了。
姐姐回家把這事攬了下來。當她拎著一袋子蛋液,告訴父親還能抓緊時間炒盤菜時,換來的卻是父親一記重重的巴掌,然後是一頓拳打腳踢。
染染看不下去,坦白了。但這反而加重了父母的怒火,因為他們覺得被騙了。現在姐妹倆共同成為了父母發泄的物件,一場打罵從傍晚持續到了夜晚。
聽著妹妹的哭喊,一向倔強皮實的姐姐猛然爆發。她站了起來,一把拉住妹妹,喊著要走,要離開這個家。父母看著長能耐的彩妮兒,停下了手中的掃把,將二人踹到門外,並重重的鎖上了門。
那時正值寒冬,妹妹瑟瑟發抖,姐姐看不下去,最後只好央求爸媽開門。然而屋內的爸媽對此毫無回應,熄了燈準備睡覺。並警告她倆再叫門打擾他們睡覺,一定打死他們。
夜漸漸深了,院子裏開始上霜。姐姐抱著染染坐在墻角,顫抖不已,染染的嘴唇已開始發青。姐姐沈默許久,突然想到了什麽,把染染從地上拉起來,悄悄地摸出了家門。
姐姐想帶染染去一座深山老廟,就是染染現在居住的這座。
這是姐妹倆此前在一次采藥途中遇到的。那時僧人對姐妹二人很熱情,很慈祥,邀她們進院歇息,並奉上了熱水瓜果。在他的指點下,姐姐最終找到了草藥產地,對此她們滿懷感激。
之後的采藥途中,姐妹倆就經常去這間寺廟,也跟僧人熟絡起來,僧人漸漸了解了姐妹的不幸。
他總說,如果有一天你們忍受不住時,可以來這裏避避難。
這一次「雞蛋事件」被父母毒打後,姐姐想起了僧人的這句話。只是當走到山路入口時,姐妹倆停了下來。
當時山裏已經起霧,黑壓壓的樹林嘩嘩作響,仿佛有夜行的動物穿行其中。白色的霧氣在漆黑的山間盤旋起舞,不時傳來夜鸮的叫聲。
平時走過無數次的小路,突然不再熟悉,仿佛通向黑暗的地獄。她們害怕了,猶豫很久,姐姐緊握著妹妹的手,轉身回家。
那一夜,是染染畢生難忘的夜晚。凍得麻木的她被姐姐拉進了豬圈,一陣惡臭嗆得她有些清醒,繼而想吐。但隨即感受到的,是豬糞的溫暖。
姐姐拉著她一腳深一腳淺地走到豬圈角落,踢醒了夢中的白豬,在它睡覺的稻草間挪出一絲空隙。
白豬對整日餵養它的姐妹倆哼唧了兩聲,翻身繼續睡去。就這樣,姐姐倚靠著白豬,抱著染染,在臭氣熏天的豬圈中,度過了一夜。

或許是豬圈的一夜讓姐姐徹底心涼了,那之後姐姐告訴了染染自己心中深埋已久的計劃,「默默忍受的生活沒有盡頭,你必須得讓它結束。」

染染很意外,但也理解,因為姐姐這些年來一直在給她講「自由」的故事。
染染記得很清楚,在那個黎明,在清晨的薄霧之間,姐姐講了王小波【綠毛水怪】的故事。
聽完整個故事,染染印象最深刻的是女主人公變成像海豹一樣的水怪,找到了那個神奇、自由的海灣世界。
染染望著噴薄欲出的朝陽,心神迷醉,不斷地纏著問姐姐,真有那樣的地方麽,我們能變成那樣的人麽?姐姐堅定地給出她肯定的答案。
後來染染從姐姐的口裏,染染時常聽見「王小波」、「海子」、「顧城」等奇奇怪怪的名字,也時常聽見「人的痛苦源於無能」等難以理解的話。
姐姐平時家務活很多,所以她總是利用黎明在山中采摘的空閑時間讀雜書,那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時刻。在山石草木間,晨霧未散之時,姐妹倆在山間歡呼雀躍,宛若枝間小鳥、海中之魚。
那時的妹妹愛在樹叢東竄西竄,姐姐則捧著一本書,靜坐在樹葉招搖下的光斑中。
主動學習的小孩可能是每個家長所奢求的,但在那對暴虐的父母的眼中,學習好根本沒用。
當村裏人表揚姐妹倆,說她們老考第一時,父母說女孩念完高中就行了,早點打工幫家裏掙錢。
妹妹也想過去打工,說自己掙錢給了父母,他們就不好意思打罵姐妹倆了。
但這個想法被姐姐一口駁回,說她們都要好好上學,「染染,你不能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取悅別人上,生活的希望在山的外面,我們得自己走過去,找到它。」
姐姐說,出去後,自己會找到藥材市場打工,染染則繼續上學。但兩人需要先租一個小房子,最小的那種一個月只要兩三百塊。加上路費和第一個月的開銷,姐姐算過了,再攢上兩個月,應該就夠了。
這一次,染染聽完了姐姐的計劃。她起初有些退縮,但在這幾年暗無天日的生活裏,姐姐一直是染染的指明燈,即使害怕,染染也決定追隨她的腳步。
如果不是後來發生的那件事的話,染染可能已經和姐姐一起逃出深山了吧。

幾天後的一個夜晚,醉醺醺的父親和母親難得沒有吵架,早早入睡。
冬夜寒冷難耐,家裏唯一的取暖方式就是一個燒煤球的鐵皮爐子。燒煤球很麻煩,因為三四個小時就要加一次火,而這任務自然落到了姐姐頭上。
那天晚上姐姐換完煤,縮排被窩繼續睡覺。但可能是煤球濕度太大的原因,姐姐剛睡著沒多久,煤球爐熄了。
屋裏的溫度漸漸下降,凍醒了酣睡的父母。父親憤怒異常,起床檢視。聯想到前幾天的睡豬圈事件,父母二人認定這是姐姐故意報復。
於是父親把睡意朦朧的姐姐拖出被窩,抽出煤球爐邊的火鉗,狠狠抽打著姐姐後背。打累了,便喝令姐姐趕緊把火生著,然後自己又上床繼續睡覺。
染染在被子裏蒙著頭,聽著姐姐的慘叫一直哭,但不敢做些什麽。等外面沒聲了,染染就在被子裏等姐姐回來,可等了很久卻毫無動靜。
染染下床,走到客廳一看,發現姐姐正呆呆地伏在爐子旁,背上被燙爛的血肉和衣物粘連,一道道傷痕觸目驚心。
染染擔心地搖晃幾下,姐姐才漸漸回過神來,叮囑染染快去睡覺。
她乖乖去睡覺了,但不知過了多久,睡眼惺忪的她又突然被姐姐從被窩裏拉了出來。
姐姐在嘴邊「噓」地比劃了一下,示意她別睡了,默默地幫她穿好衣服,拉著出了門。染染追問,姐姐敷衍地說要帶她去網咖。
屋外漆黑一片,隱約有蟋蟀的叫聲。空氣寒冷的仿佛冰片,吸到鼻子裏有清脆的碎裂聲。兩只小小的身影就在漆黑的小道上哆哆嗦嗦地走,一個皺著眉頭滿臉困惑,一個皺著眉頭滿懷心事。
終於姐姐開口了,說再也忍受不了了。姐姐告訴妹妹,決定把逃跑計劃提前。
妹妹沒想到來得這麽突然,大腦一片發懵,心中湧出無數個「但是」,卻不知從何說起。但她想到姐姐方才遭受的毒打,以及一直以來對姐姐的信任,她還是慢慢堅定了下來。
四周漆黑寒冷,小小的染染牽著姐姐溫暖的手,一步一步向鎮上走去。走出村外,走過田地,走過樹林,走過樹葉的嘩嘩招手,走過青蛙的呱呱作別。
但慢慢地,染染發現,姐姐的手越來越緊,開始冒汗,腳步開始放緩,眼神也開始猶豫。染染想,難道姐姐不想跑了?
就在這時,姐姐猛地轉身,說在走之前,要回家辦件事兒。
回去的路程格外快。當姐姐開啟門的那瞬間,染染驚呆了——
用作排放一氧化碳的鐵皮煙囪不知何時已經從窗外耷拉在了屋裏的地上,像一條垂死的蛇。本就濕氣較重的煤球,迅速在屋裏彌漫出煙氣,充斥著一股刺鼻的味道。
床上的父母已經臉色烏青,母親甚至開始微微吐白沫。
原來姐姐想制造意外,讓父母煤氣中毒身亡,只是在最後時刻她反悔了。
姐姐趕緊拿起爸爸手機撥打了120。在看著父母被安全帶走後,姐姐又帶著妹妹悄悄溜走了。
兜裏存了兩年的500多塊還在,父母也暫時不會追上來。當姐妹倆走到鎮上時,紅彤彤的太陽剛剛升起,霧氣消融。

一切都是姐姐來操持,她雖然也是第一次獨自出門,但早已在心中把所有環節過了幾百遍。
然而,再細致的預想,也抵不住意外。
買票時,姐姐被告知,近期嚴查身份證實名購票,以打擊愈來猖獗的人販子。任憑姐姐如何哀求,售票阿姨也不為之所動。
這條平時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執行的規定,此時卻成了姐妹二人的攔路石。
姐姐沒有沮喪,她拉上妹妹,打算去鎮外大路上攔過路車。
一輛一輛的汽車駛過,卻沒有車為這對姐妹停下,留下的僅是濺起的灰塵。
就在姐妹倆心漸漸沈入谷底之時,一輛警車在她們面前停了下來。原來車站售票員阿姨看著姐妹倆形單影只,舉止可疑,叫來了警察。
警察把她們當作普通離家出走的孩子,說要送姐妹倆回家。
姐妹倆被強行關進了警車,姐姐絕望地哭鬧著,拍打車窗。
派出所同誌不明白姐妹倆為什麽如此抗拒,而當染染坦白了擔憂後,警察只是輕松地說,「這有啥呀,到底是自己爸媽,有啥事兒都能過去。你倆放心,警察叔叔給他們講,不會打你們的。」
妹妹單純相信了。姐姐後來也沒有再哭鬧,一路上靜靜地望著窗外。只是在臨近村子時,她攥緊了手,指甲仿佛要紮進手心。
到家時已近傍晚,父母在醫院輸液治療後已經回家。面對警察同誌的叮囑,兩位腆著笑臉不斷地答應。但送走警察同誌後,他們轉身就變了臉色。
染染先被趕出屋外,屋裏隨即傳來姐姐淒厲的叫喊聲,和父親的怒罵聲,「燒個爐子都不用心,煙囪掉了都不知道,還能幹點啥!差點害死老子不說,還想跑!長出息了,讓警察來教育老子!」
姐姐的哭喊一陣一陣傳來,染染哭著拍門,卻毫無反應。
她起身跑出院子,朝警車離開的方向追去。但警車早已走遠,濺起的煙塵都已平靜。
染染絕望地跑回家,發現鄰居們三三兩兩圍著門口在勸說,得到的回應卻是母親惡狠狠的叫罵和姐姐更加慘烈的叫聲。鄰居們紛紛搖頭,散去回家,也散去了染染最後的希望。
天漸漸黑了下來,也許是父母打累了,姐姐的哭喊聲漸漸低了下來。門咣當一聲開了,染染沖進了屋子,父母並沒有理她,累得雙雙倒頭睡去。
姐姐癱倒在地上,毫無意識,臉上已經腫得青一片紫一片,看不清面目。
染染怕吵醒父母,抱著姐姐只是默默流淚。她試圖把姐姐抱到床上休息,卻實在難以拖動,而姐姐又無論如何叫不醒。染染只能從床上拖了被子下來,把兩人裹著,互相取暖。
到半夜,染染才發現,姐姐越來越冷了,無論自己抱得多緊裹得多厚都不起作用。染染開始害怕。她用電視上看到的方法,試了試姐姐的呼吸。
沒了。姐姐死了。
染染痛哭,吵醒了爸媽。染染找到手機準備打120,卻被母親一把奪過,「你要是讓外人知道姐姐被打死了,我和你爸爸都得坐牢,剩你一個人在外面遲早餓死!」
染染已經哭得說不話。一直以來,姐姐就像黑暗生活中的一點燭火,倔強地跳躍,卻從未熄滅,給染染指點著方向。她對姐姐無比信任,堅信姐姐會帶自己逃出這裏,而如今,在即將奔向光明的時候,這點燭火熄滅了。

父母連夜去鎮裏置了一口小棺材,說家裏有人發急病死了,急需埋葬。棺材放到家裏,兩人又急匆匆背著鏟子出門了。再回來後,已經天光大亮。
染染木然地看著父母操作著一切,一夜無言。和姐姐在一起的三年時光如走馬燈一樣在腦海中閃現:姐姐帶她采摘和販賣山果的快樂時光,給她講綠毛水怪的故事,描繪外面自由的世界,信誓旦旦要帶她走出大山......
染染呆呆地隨著父母走出門,面對鄰居們七嘴八舌地詢問,染染沒有說出父母教給她姐姐病死的謊言。
她放聲大哭,「姐姐被打死了!」
接到鄰居的舉報後,警察很快抓捕了染染的父母。審訊的過程進展很快,面對鐵證如山,兩人沒有多做抵抗,就供述了案情。父母分別被判死緩和無期。
染染後來被鄰居們暫時收養,但是有一天她偷偷逃進了山裏,消失了近兩年。

我和染染的繼父有所交集,是在他剛剛入獄不久後,向陽之家的一次活動中。當時,我和染染還素未謀面。
在向陽之家同誌的集中排查中,發現他家中僅剩的幼女不知所蹤,委托我們詢問調查。
我將該犯叫來,他漠不關心地表示他也不清楚,向女子監獄服刑的妻子寄信詢問後,那邊也表示入獄之後再無孩子訊息。
我和他沒聊太多,因為我不想和這個人有太多交涉。打死女兒的他在監獄中無愧疚,還說自己差點被害死,而且並不想打死她是被她害了。被我訓斥後,才用種討好的語氣說,是自己不對。
向陽之家的人最後親自上村子裏尋找,打聽很久後,有熟識的鄰居提供線索,說山上有一個破敗寺廟,少有人往,只有一個僧人主持著香火,聽染染姐姐說過以前總上那玩。向陽之家這才找到了染染。
原來,當年姐姐離世後,鄰居們雖然同情染染,但畢竟不是自己的孩子,也沒有誰完全承擔領養的責任。那段時間染染只能在鄰居家之間輾轉。
更讓染染受不了的是,鄰裏之間總會談到這場悲劇,也總有人詢問染染,但他們的關懷成了染染的枷鎖。
染染想到了那個寺廟,想到和尚曾說,可以把那裏當作自己的家。於是某一天,她帶著姐姐給她做的草帽、書包還有姐姐的舊書,自己偷偷跑到了山上。
染染告訴了和尚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並表示自己想要居住在廟中。和尚過去就一直鼓勵姐妹倆來廟裏,這次也欣然同意了。
在隨後近兩年裏,染染從未下山,飲食靠著和尚去山下做法事、化緣而得。作為報酬,染染承擔了做飯、洗衣的責任。
閑暇時,她就看姐姐的舊書,去姐姐以前帶她去的地方。後來她說,自己在這與世隔絕的環境中,慢慢恢復了。
隱居許久,最終還是被向陽之家找到。當時的染染有些驚魂未定,面對向陽之家同誌的細心安撫,只是一味地往她幹大身後躲,一言不發。
當向陽之家同誌跟僧人普及相關收養政策,沒想到在聽到幹爹不是血緣關系,不是法定收養人的時候,和尚直接發飆了,「誰再逼染染離開,我就和染染一起撞死在寺廟台階上。」
染染面對這樣的爭執嚇壞了,不由得哭鬧了起來。向陽之家的同事們只好作罷,決定先行離開,以後再徐徐圖之。
這場勸服不知不覺持續了一年多。
好在讓人欣慰的是,染染變得開朗了,也不再回避村民們的關懷。之前,有村民來到廟裏時,染染為了不讓別人發現,總是躲起來。
染染後來還經常跟著僧人去山上采野果賣,或者去山下化緣,過著入世出世、讓人有些羨煞的隱居生活。
就在我們所有人以為染染悲慘的命運已經結束時,卻發現她又落入了另一個噩夢。

染染的幹爹是火神廟唯一的僧人。
我之前總想不通,火神廟是道教的,怎麽會由一位僧人主持?但我一聯想到染染的轉變,還是不由得對他心生敬畏。
不過第一次見到他時,幾乎打翻了我心中高僧的形象。
他沒有一般僧人的祥和,面孔滄桑,頭上已經長出了寸許發茬,穿著粗布的灰色僧袍,汙漬點點。見我們進來,他冷冷地打了個招呼,就在一邊抖落雞毛撣子上面的灰塵。

向陽之家的同誌跟僧人談染染下山念書的事,但話未說完,就遭來對方惡狠狠地打斷,「想都別想!這是我閨女,只有我會對她好!甭想送點東西過來就想把閨女奪走!」
染染趕忙拉著向陽之家同誌走出屋子,小聲勸慰並再次強調自己在這挺好的。而後堂屋裏隱約還傳來「幾把!草!」之類的咒罵聲。
我是生平第一次見到這種滿口臟話的僧人。
此後一段時間,染染成長還算順利。12歲時,僧人依著承諾,讓染染在鎮上上了初中。
剛開始一切正常,染染每天清晨和村中小夥伴們結伴上學,傍晚歸來玩耍,周末也重操舊業,帶著小夥伴們摘果采藥,再去鎮上擺攤賺錢。
染染還攢下零用錢給向陽之家的同誌買禮物,帶他們逛市場,並老練地笑著說,「買什麽不,提我打折。」
但上學半年左右,向陽之家楊主任發現,染染由穩重慢慢變成了沈默寡言、思慮重重。
有一次染染甚至難得地跟楊主任打聽了向陽之家的生活,言辭間透出一絲向往。
楊主任心中微動,趁機又加以勸說。染染沈默了許久,才開口拒絕,說幹大年紀大了,自己在身邊有個照應。
楊主任心中的擔憂難以消除,下山時便跟村民們打聽,得知染染最近下山少了,周末也很少約夥伴們去鎮上玩耍。問她怎麽了,她總以學業重、壓力大來解釋。
楊主任作為女人,天性細心敏感,告訴染染有什麽事情隨時給她打電話。
終於在一天晚上,楊主任接到了染染的電話,那邊隱隱傳來哭腔,「楊奶奶,我是染染,幹大最近不知道怎麽了,晚上睡覺時,一直……一直摸我。」
原來,染染和和尚住同一間屋,分別睡兩張床,相隔一米左右。近來,和尚到晚上時經常來到染染床邊,問她累不累,身體舒不舒服,借此在染染身上亂摸。
染染那時小,還沒太明白是怎麽回事,只是隱隱覺得不對勁。後來她去看書,間接從老師、同學那了解到了究竟是怎麽回事。
當天晚上楊主任就帶著警察去了廟裏,直接抓捕和尚,然後把染染送去做了體檢。幸運的是,生理上染染並沒有受到傷害,但是心理上的創傷,可能需要時間來撫平。
另一邊,刑警同誌們的審訊工作也在進行。和尚剛開始支吾應付,堅稱和染染只是父女之情,所作所為或許有些親昵,但沒有任何無恥思想。
一份網上通緝令讓事情清晰了起來。

僧人只是個假和尚,他的真實身份是逃竄的強奸犯。
十幾年前,他是南方臨省的一個農民,遊手好閑,三十出頭,沒媳婦,便跑到省城打工,結果掙來的錢全花在了風月場所裏。
臨近過年他沒錢買票,找工友借錢卻被拒絕,而那些夜夜笙歌的小姐們自然也沒再理會這個打工仔。
他決定幹上一票。作案物件早已想好,就是那些娛樂場所的小姐。自己落到如此境地,跟她們脫不開關系。更何況她們賺錢多,下班晚。
他找了一把水果刀,用毛巾蒙了臉,在胡同裏埋伏到後半夜,對一位落單下班的姑娘實施搶劫,並進行侵犯。威脅其不許報警後,迅速逃離。
事後他匆匆逃回老家,憑借搶來的財物勉強過了年。年後他偷偷回到之前的工地,打聽到附近並沒有警察查案。
那之後他便故技重施,混跡在附近各大娛樂場所,作案數起,犯下搶劫、強奸婦女的累累惡行。
最後終於有受害人報案了,而當警察找到工地時,他偷跑了,溜入莽莽大山。
他耐力頑強,在山中摸索攀行,一路吃野果喝泉水,走了幾百公裏,翻越數座山頭,來到了那個破敗的寺廟。
他本意是進去找些食物,沒想到這裏久空無主,但物事兒齊全,便給自己剃了度,偽裝成和尚留了下來。而警察同誌們後來上山搜尋無果,只好在網上釋出了通緝令。
過路村民發現寺廟重開了香火,上前詢問,他撒謊說是來自南邊的遊方僧人,路過此廟,覺得緣分到了,要留下主持香火,倒也編得天衣無縫。
這些年來,寺廟地處偏僻,少有人來,從來沒有惹人懷疑。一直到他對身體開始發育的染染起了心思,猥褻後被舉報,才終於落入法網。
假僧人究竟什麽時候動了心思就不得而知了。他說自己只是一時邪念起,警察後來也沒有再就這一點追問。
但我猜測,他在山中初次和姐妹倆相逢,過分熱情的邀約可能就帶著目的。
我又想起染染給我描述過的那個永遠也忘不了的寒冷冬夜,她和姐姐不得不睡豬圈的那個寒冷冬夜。姐姐曾經帶著她,踏在寺廟入山的路口——
那時霧氣盤旋、夜鸮鳴叫,大山黑暗沈默。姐妹倆幾經徘徊,退了回去。

半年之後,我以個人名義去向陽之家探望了染染。
楊主任和我說,剛把染染接到向陽之家,因為怕觸碰到她心理創傷,別的異性老師都沒有接近她。楊主任把染染當做自己女兒,每晚親自陪著睡覺,有將近一個月。
「你再也不會回到山村了,你跟那個地方將再也沒有關系。所以,把所有不好的事情都丟在那裏吧,再也不用去想了。」楊主任對她說。
染染不說話,只是低著頭。
楊主任又說,社會上總有一些壞人,他們是可惡的,法律最終會懲罰他們,遇見他們不是你的錯。你要懂得離開他們,離開過往。如果一直沈浸在過往,豈不是在用別人的錯懲罰自己?
染染這才點點頭,小聲地說知道了,但依舊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
往後的日子,楊主任讓染染安心在向陽之家學習,還鼓勵其他小朋友主動跟染染玩耍。
向陽之家裏面全是服刑人員的子女,染染慢慢發現,其他小朋友的命運都很淒慘,她也不是最慘的那個,但別人都恢復了,每天開開心心上課。
周末,楊主任組織孩子們去郊遊,特意給染染講歷史人物的故事,鼓勵她磨練堅韌的性格。
慢慢的,染染開朗起來,還主動跟楊主任說,自己什麽都明白了,會珍惜現在的生活,努力地好好活下去。
在我來的時候,染染已經好了很多,除了不太喜歡和同學們打鬧之外,生活社交已趨於正常。
她喜歡獨自看書,安靜思考,聽著音樂發呆。看到我來,她放下手邊的書,笑著招呼我在走廊坐下,跑進屋子給我倒水。
風穿過廊道,拂起她的頭發,陽光在發絲裏跳躍。她跟我炫耀起她的學習成績,像個未受折磨、天真的孩子一般。一時間,我所有安慰的話都說不出口。
染染給我展示了她的書,都是姐姐的舊書。它們從家中輾轉到了寺廟,再到向陽之家安定下來。書中的力量也從姐姐手裏傳遞到了妹妹身上。
看望結束後,染染堅持把我送到院子門口。她站在門口,眼前一片開闊,遠處城市的建築盡入眼底。
她指著一處醒目的建築問,「叔叔,你知道那兒是哪裏麽?那是殯儀館,我把姐姐的骨灰從山裏帶了出來,暫時住在那裏。我想姐姐知道,我們從大山裏出來了,這裏是文明的地方,這裏有我們希望的生活。」
她看出了我臉上的擔心,寬慰我說她早走出來了,現在特別好,「我看了越來越多的書,才越來越明白姐姐當年的勇敢和堅強。姐姐給我講過的故事我都看了一遍,她當時最喜歡的一段話我現在也特別喜歡,我讀給你聽吧。」
她站在山腰的一片緩坡上,風吹著她的頭發,她看著山下的城市:
「天色微微向晚,天上飄著懶洋洋的雲彩。下半截沈在黑暗裏,上半截仍浮在陽光中。那一天我二十一歲,在我一生的黃金時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愛,想吃,想自由,還想在一瞬間變成天上半明半暗的雲......」

染染和姐姐都非常喜歡王小波。姐姐曾對染染說,「人的痛苦源於無能。」這句話出自王小波的【關於幽閉型小說】。
這篇文章裏提到一個故事,有一個可惡的海員長,整天督促海員們洗甲板。海員們雖然討厭這樣的生活,但他們沒辦法,四周是汪洋大海,要想不幹,只能等船停靠碼頭。
王小波說,中國舊式家庭的女人,就像汪洋大海裏的船,無法靠岸。
也許姐姐正是看到了這裏,才猛然醒悟,想要有一個美好的未來,必須要擺脫自己家庭的束縛,並做出了逃跑計劃。而當她告訴染染「生活的希望在山的外面」時,也將心裏的願望傳遞了下去。
染染最後走出了大山,在向陽之家過上了希望的生活。她靠的不僅是別人的救助,更重要的是自己沒有逆來順受。
這很像【關於幽閉型小說】裏的另一句話,「要努力去做事,拼命地想問題,這才是自己的救星。」
(文中部份人物系化名)
編輯:林老鬼 馬修
插圖:娃娃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