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卷,似乎是當下大部份人的共同感受。
但我們又究竟在卷些什麽呢?
2013年,美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發表了一篇文章 【談談「狗屁工作」現象】。 文章中,他把那些不該存在卻耗空了人生的工作稱為「狗屁工作」。
一石激起千層浪,格雷伯的文章引起了蝴蝶效應:它在網站上獲得了100萬點選量,幾周內就被轉譯成10多種語言,在各國的雜誌上轉載。無數人給他留言,認為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卻令人心累。
這讓格雷伯感到驚訝,卻也發現,在這篇文章被發表之前,「無意義的工作」泛濫的社會現象幾乎沒有得到系統性的關註。
他決定繼續研究,最終寫成了 【毫無意義的工作】(Bullshit Jobs) 一書,告訴深陷「無意義工作」的打工人,在思考意義的同時,也可以獲得一份開解自身的「藥方」。
【毫無意義的工作】
▽

這本【毫無意義的工作】被視為當代年輕人的精神嘴替,道出了「椰菜」們的心聲,中文版出版1年多已經,獲得了近萬讀者的好評。
今年,阿信出版了大衛·格雷伯的另一本新書—— 【規則的悖論】 。
【規則的悖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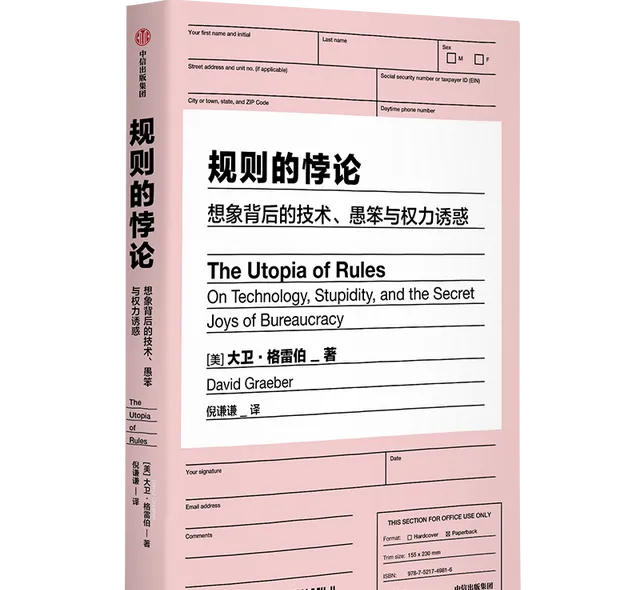
今天,阿信專門為你邀請到了 史丹福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雪光 ,為你做一次新書導讀。
本書的主題剛好涉及到周雪光教授的研究領域,多年前,周教授讀了格雷伯與他人合著的 The Dawn of Everything ,留下了深刻印象。
順雞尋蛋,周教授又找到了【規則的悖論】。
格雷伯提出,「我們亟須一種針對官僚制度的左翼批判。本書準確而言並不能為這樣一種批判提供大綱。… 這是一部文集,每一篇都指向了一些左翼對官僚制的批判可能采取的方向。」
不出所料,這本書帶有格雷伯的標誌性特點: 鮮明立場加激情色彩 。
周教授說:
作者有廣闊的視野、淵博的知識和敏銳的觀察,超越了通常的學術場域來看待官僚制,從生活經驗常識、學科知識、到哲學思辨,匯成有沖擊力的語言,讀來頗有新鮮感,刺激想象,不時引發我「對話」的念頭。
本文作者:周雪光
先說一下關鍵詞的轉譯。
作者的主題,在英文中是「bureaucracy」,是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在20世紀初提出的一個分析概念,有兩種中文轉譯,一是 官僚制 ,二是 科層制 。兩種轉譯在中文中都有廣泛套用,我自己過去也都采納過這兩種譯法。

周雪光
近年來,我更為清楚地意識到中國歷史上的官僚體制與韋伯意義上的bureaucracy有重要的區別,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有必要在行文討論中將這兩者區別開來。
官僚制一詞體現了中國歷史上特有的官-僚要素特色,而科層制則近於關於科-層結構的直白刻畫,與韋伯的原意更為吻合。
所以,我以為將「官僚制」保留為描述中國所特有的官僚體制所用,而將「科層制」用以描述韋伯筆下所描述的bureaucracy理想類別。
這本書的中文譯者選擇將「bureaucracy」譯為官僚制(譯者另加註腳,說明另外一種譯法)。為了便於讀者閱讀中譯本,我在這個讀書筆記中仍然采用「官僚制」這個譯法,這樣不會給讀者造成困惑。
但請讀者註意,本書 (以及本讀書筆記) 中的「官僚制」一詞,乃是指韋伯意義上的科層式正式組織 。
這是18世紀以來隨近代國家和資本主義大生產而興起的一種新型組織形式,集中體現在近代以來的政府組織形式上,與中國歷史上的官僚體制形似實異。
作者從「官僚制」一詞在各類書籍中出現的頻率展示,在二戰後頻率扶搖直上,直到1970年代末開始下降。
作者說,官僚制組織暴露出諸多弊病,例如官僚作風、效率低下,等等,一度引起各種批判聲討。但是,官僚制在二戰後得以大力發展,已經廣泛深入社會各個領域,以致今天人們已經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
作者提出了「 全方位官僚化 (total bureaucratization) 時代 」這一概念。美國在二戰後的世界地位,其官僚體制在世界各地有了廣泛傳播。

作者討論了美國官僚制的一系列特點:公域政府組織與私域企業組織的邊界模糊,更為重視效率管理,政府制度猶如公司制度。作者的討論著眼於政府組織,但也不時地將公司組織囊括其中。
這一過程——公共和私人權力逐漸融為一體,充斥著最終旨在以利潤的形式攫取財富的規章條例——尚無一個名字。這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這些事之所以會發生,很大程度上緣於我們缺乏談論它們的方式。
作者認為,美國政府全方位官僚化的趨勢是近幾十年開始的。
這不僅僅是一次權力重組,而且是一場文化變革。在此背景下,金融和企業圈子裏發展起來的官僚技術(績效考核、焦點小組、時間分配調查……)得以入侵教育界、科學界、政府等其他社會領域,並最終滲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追蹤這一過程的最佳線索或許是它那套語言。這些圈子裏首先出現了一種奇特的話術,滿是光鮮又空洞的用詞,諸如願景、品質、利益相關者、領導力、卓越、創新、戰略目標或最佳實踐。
這類機構總是創造出一種共謀文化。重點不在於某些人有辦法打破規則,而在於衡量一個人對組織是否忠誠,某種程度上就看他是否願意裝作視而不見。當官僚邏輯擴充套件到整個社會範疇時,我們全都開始配合演出。
作者有一個重要的觀察。
在1980年代以來,西方官僚制組織有一個重要的轉變,即隨著列根、戴卓爾保守主義上台,試圖對政府組織進行改造和重組,政府組織理論也隨之發生了變化,誘發了新公共管理理論的興起,其主要內容是將越來越多的「市場原則」「市場激勵」和基於市場的「問責程式」納入官僚制本身的框架。
回頭來看, 所謂新公共管理理論對美國政府運作實際上並無太大影響 。
在美國,公共管理領域沒有得到很大重視,新公共管理理論沒有進入組織學研究的主要文獻。
但這一理論取向似乎對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政府演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這一思路影響下,政府越來越像公司,政府領導越來越像老總。其他各類組織也有類似演變趨勢。
如今大學裏的學生把導師稱為老板,可以說是現實的一個折射吧。
當然,我不相信一個外來的學說理論本身會有這麽大的作用。如果它真的發揮了影響,那應該是它迎合了官僚體制內部的需要。
作者興趣廣泛、知識淵博,在討論中將日常觀察、時事故事、學術理論信手掂來,若讀者不熟悉這些事件資訊,可能會眼花繚亂,難以跟上作者的跳躍思緒。仔細讀來體會,不時有洞見閃爍。在這裏擇一二討論一下。

大衛·格雷伯
其一,作者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官僚體制的一大特點是生產沈悶無聊,簡單的文本、單調的程式,無意義的過場,等等。
官僚知識其實就在於綱要化。在實踐中,官僚程式總是意味著無視真實社會生活中的所有幽微之處,將一切都簡化為預先構想的機械化或統計學公式。
作者感嘆道:
無怪乎這一切可能會令人類學家絕望。人類學家為密度所吸引。我們手頭的解釋性工具最適於在復雜的意義之網中穿行——我們尋求理解紛雜的儀式象征、社會戲劇、詩歌形式或親屬關系網絡。
而在官僚制單調枯燥的表格列表和程式中,學者們能夠解釋放出怎樣的想象力呢?
這讓我聯想到,學者們對官僚體制的研究大多著眼於事件過程,而不是日常程式,或許原因正在於此: 規章程式就像一個黑洞,隱去了活生生的實際過程和內容 。然而,正是在這些日常程式中隱藏著官僚機器運轉的密碼。
過去200年間,占支配地位的官僚制組織最深厚的遺產,就是把這種理性、技術手段和兩者最終服務的非理性目的間的簡單割裂變得如常識一般。
在國家層面上是這樣,公務員的榮譽感源自找出最有效的手段去貫徹本國統治者碰巧設計的國家命運——無論其根植於弘揚文化、帝國征服、追求真正平等的社會秩序,還是謹遵【聖經】律法。在個人層面上也是這樣……
作者寫道,官僚制和暴力密切關聯。
我想論述的是,暴力,尤其是結構性暴力(我是指普遍存在的、靠威脅施加身體傷害為根本後盾的社會不平等形式)造成的情境總是傾向於促成我們對官僚程式的慣常印象,即一種有意為之的盲目。
暴力能促成專斷的決定,由此避免更平等的社會關系裏特有的辯論、澄清和再談判。
與此相對的另外一點是,
我也堅持認為,從這些最富戲劇性的層面切入暴力,很容易忽視這樣一個事實: 暴力及其造就的情境的一大顯著特征就是非常無聊 。
在美國監獄這樣暴力至極的場所,最惡毒的懲罰形式僅僅是將一個人關在一個空房間裏長達數年且無所事事。像這樣清空一切交流或意義的可能性,才是暴力及其所作所為的真正本質。

其二,作者的一個觀察: 在二十世紀後半段韋伯、福柯大受歡迎,他們的很大一部份吸重力在於他們對官僚制的態度 。
事實上,有時我感覺整個20世紀只有這兩位聰明人發自內心地相信官僚制的力量在於其有效性。也就是說,官僚制的確行得通。
韋伯將官僚式組織視為理性在人類事務中的化身,明顯比其他形式的組織優越太多,恐要吞沒一切,將人類囚於了無生趣的「鐵籠」(iron cage)之中,盡失精神力與個人魅力。
福柯的理論更具顛覆性,但這種顛覆對官僚權力有效性的揭示有過之無不及。在他研究庇護所、醫院、監獄和其他物件的著作中,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健康、性、工作、道德,以及我們對真理的概念本身——原本都不存在,不過是由這樣那樣的專業或行政話語造出來的。
借由治理術(governmentality)和生命權力(biopower)等概念,他主張國家官僚制最終形塑了人之存在的基本參數,與個體的關聯之緊密遠超韋伯想象。在福柯那裏,一切知識形式都成了權力形式,主要透過行政手段形塑我們的思想和身體。
其三,作者另外一個有趣的觀點:
事實上在支配關系中,通常是從屬者實際承擔起了理解相應的社會關系如何真正運轉的工作。
也就是說,當權者對被支配者不甚了了,而後者對當權者卻了如指掌。
這裏的道理是,權力使人任性,無需關心權力接受者的感受,但後者因為其利益風險而不得不細心領會和解讀來自權力的每一個微小訊號。
或許這是另外一種類別的資訊不對稱,在這裏,象征資源的控制與反控制,觀念建構與常識直覺與之間的互動,微妙且意味深長。
作者是西方左派思想的重要學術代表和代言人,因此不難註意到作者的鮮明取向,特別是反對當代強大國家機器的立場。正因為此, 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極為尖銳、很有啟發性的觀察和觀點 。
我提出一些想法,與作者的觀點「對話」。
作者在第二部份討論了官僚體制對科學創新的抑制和扼殺,所依據的例子是在二戰後那些科技蓬勃發展年代的許多科學預測至今沒有實作。但是,從作者的討論可以看出,他對科學與技術領域實際過程和推動力的知識了解實在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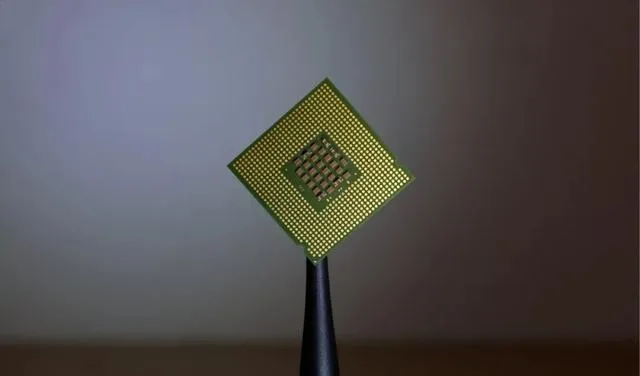
作者寫道,
一種怯懦的官僚精神已然滲透進智識生活的方方面面。許多時候,它被一套充斥著創造力、主動性和企業家精神的話語所遮蔽。
但這套話語毫無意義。最有可能提出新的概念性突破的那類思想家最不可能獲得資助,而就算他們在這種情況下仍然取得了突破,也別指望找到什麽人願意跟進他們最大膽的探索方向。
這些方面的確可以舉出很多例子,作者的判斷不無道理。但是,也可以想到許多不同的例子。
舉兩個我知道的在美國學術界的例子。
其一,組織學家馬奇在一次學術大會上提出,在研究資金與研究人才兩者之間,研究人才是更為稀缺的資源。所以,不應該是研究人才去追逐研究資金,而是應該相反,研究資金去追逐研究人才。
會後,一個基金會找到馬奇,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並願意資助他的研究工作。在隨後的多年裏,馬奇一直得到這個基金會的資助。
其二,在一次研究專案稽核會上,主持人力主將一位諾獎得主的申請專案拿掉,他的理由是,這位申請人雖然過去在這個領域做出了優秀工作,但多年來沒有新的重要進展,把資金給他的專案,是對納稅人不負責任。
我想說的是, 在社會中,有著其他超越官僚制的創新動力 。
作者寫道,對蘇聯的最終勝利並沒有真正導向「市場」的支配。它最大的影響僅僅是鞏固了從根本上持保守立場的管理精英的支配地位;那些企業官僚打著短期、競爭、底線思維(bottom-line thinking)的幌子,壓制任何可能具備革命性影響的事物。
這一點也可以商榷。事實上,在1980年代以來,在科技界出現的新興組織形式以扁平流通、松散關聯為特點,正是針對等級制度官僚制的修訂和突破,也因此推動了資訊科技、生物技術、AI等一系列科技進步。
可惜作者並沒有看到這些組織創新及其意義。
讀這本書的過程中,不斷想到我熟悉的中國場景,也更加意識到比較制度研究的重要性 。例如,作者提出的當代社會「全方位官僚化 (total bureaucratization) 時代」。
他不知道的是,早有學者(Balas)提出了關於古代歷史上中國社會官僚化的觀點 (「China as a permanently bureaucratic society」) 。本書裏涉及的一系列現象都可以放在中國背景下解讀思考。
作者討論了官僚體制對技術創新的抑制與扼殺。「我們總是被提醒說,互聯網釋放出了各種創造性遠見和協同智慧。它真正帶來的是一種目的與手段的奇怪倒置,創造力被統籌起來為行政服務,而不是相反。」
這讓我想起了經濟史學家 Landes的發問:歷史上幾次科技革命的前夕,中國當時的科技水平都居世界前沿,但為什麽都與科技革命失之交臂?

Landes認為,其主要原因是,官僚體制追求穩定秩序,而科技革命則釋放出新的活力,沖擊已有秩序,所以被抑制打壓,難以傳播。
新的科技在不同文化中的角色也各有不同。印刷術在歐洲引起新教革命,推動了近代資本主義;在中國,印刷術則成為官僚制中科舉和文牘制度的推動力。
作者在本書中極力地延伸了他的想象力和批判力,時而超越了他的專業知識範圍,其觀點不無爭議。
然而,正是因為這種想象力和不同觀點的存在,提供了一個比較制度的視角,引起了人們的思想碰撞,無論是共鳴、贊許、推進,還是異議、批評和推翻,因此給社會帶來生氣,擴充套件思想的空間。
在世界高度關聯的今天,這一比較制度視野尤為重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