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曠野,不是軌域。」這是過去一年在社交網絡中被高頻傳播的一句話。有人在「曠野文學」的鼓舞下決定離職,追尋不受束縛的未來,也有人認為「曠野」只是虛幻的假象,跳出一條軌域後,也終會躍入另一條軌域。
這場持久的熱議背後,是年輕人對職業選擇的困惑和迷茫。1月8日,達摩院青橙學者分享會在浙江大學舉行,蘇俊、陳孝鈿、曾也魯、常林、楊宗銀等15名獲得第六屆青橙獎的青年科學家們亮相,他們平均年齡僅有33歲,有人在各自的領域中深耕十多年,有人用交叉研究推動創新,回應重大社會問題。對於這些需要「十年磨一劍」的科研從業者,會如何看待選擇「軌域」還是「曠野」這一問題?
以下內容整理自南都記者采訪及青年科學家自述:
1 、從宇宙的「曠野」中找到一件小事兒做到極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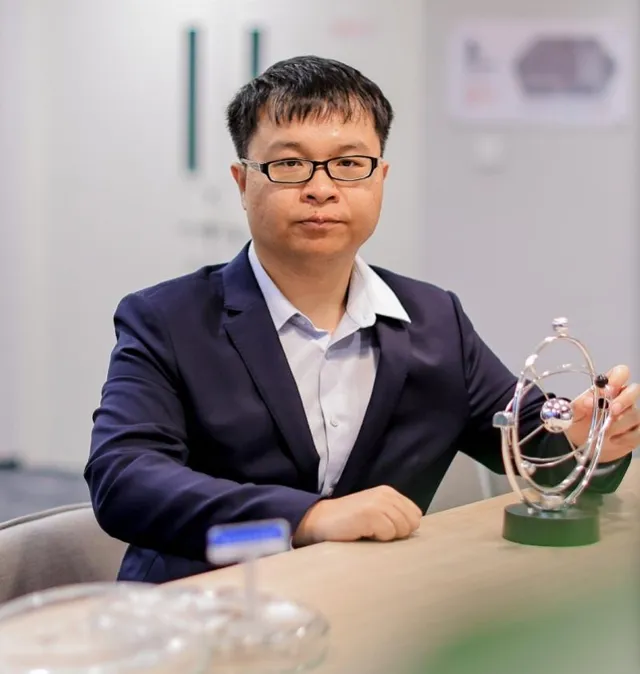
陳孝鈿 (34 歲/ 湖北荊州)
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研究員
北京大學天體物理博士
34歲的陳孝鈿是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研究員、北京大學天體物理博士。從事恒星物理、高精度天文測距、銀河系結構等方面的學習和研究已有15年。
和很多少年一樣,陳孝鈿從小對星空著迷。帶著對星空的好奇和向往,陳孝鈿高考時填報了北京師範大學天文學專業,開啟了自己的天文人生。盡管從小就立誌探索星空,陳孝鈿也有迷茫的時候,尤其是在北京大學讀博士的前兩三年。「恒星物理是比較成熟的領域,如何才能找到有價值的新方向?是否要轉到更為火熱的天文學其他領域?」這是他當時的困惑。直到一封來信改變了他的想法,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亞當·裏斯主動向陳孝鈿請教造父變星的數據(一種亮度隨時間周期變化的恒星,能夠用於恒星距離測量,又被稱為「量天尺」,最著名的就是北極星)。這正是陳孝鈿的研究方向之一,他也從此堅定了對「量天尺」的研究員信心。
然而,要從數以億計的星空裏找出造父變星,是一件極其枯燥的事情,不僅需要大數據處理,還要靠天文學家的肉眼辨識,才能實作高準確度。為了從近百萬張圖片中把造父變星全部找出來,陳孝鈿每天檢視兩三萬張圖片,持續了兩三個月,將所有圖片檢查了兩遍,從中分辨出上千顆造父變星。2018年,陳孝鈿等人釋出了第一個紅外全天變星星表,表中包含了1339顆造父變星。基於這個星表,陳孝鈿次年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自然—天文】(Nature Astronomy)發文,釋出首張銀河系恒星盤三維全貌圖,揭開銀河系形狀之謎,引起了全球媒體關註。
除了打磨造父變星「量天尺」,2023年,陳孝鈿還打造了一把新的「量天尺」。他利用雙周期天琴座RR型變星,將難測的金屬豐度資訊轉換成容易測量的周期,成功繞開金屬豐度這個主要障礙,使得上百個星系或矮星系的高精度測距成為可能。「我希望從百光年到百億光年,都能實作宇宙的高精度測距,最終得到宇宙的三維導航圖。」陳孝鈿說。
這些備受國際關註的天文學發現背後,還有一個全新的世界級天文台址——冷湖賽什騰山,位於青海省海西州,海拔高達4200米,方圓百公裏都是荒無人煙的戈壁灘。
2018年,在國家天文台研究員鄧李才的帶領下,陳孝鈿來到冷湖,被這裏的星空深深震撼,「天空中有著密密麻麻、各種形態的天體,還有很多流星劃過,這是東部城市完全無法看到的。」陳孝鈿說,更讓他們驚嘆的是,冷湖的大氣非常穩定,星星不會「眨眼」,非常適合天文觀測。於是他們在高海拔的冷湖連續監測了三年,最終證明了冷湖賽什騰山是世界一流的光學紅外天文台址,填補了東半球一流光學天文台址的空白。
對於人生是軌域還是曠野的爭議,陳孝鈿向南都記者表示,「做天文面對的就是曠野,是宇宙,看到這些景象心裏是比較平靜的。我們反而會去想,如何從中找到一件小事兒一直做下去,做到極限。所以說我們看得比較大,但會想去做比較小的事。」「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一生想做的,我很幸運。「陳孝鈿補充說,自己是個保守的人,心願不多,一輩子只想做天文研究這一件事,把恒星物理弄清楚,把知識傳授給下一代。
2 、「每一個縱深領域裏都有很多方向」

蘇俊 (29 歲/ 中國香港)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德國哥廷根大學生物學博士
1994年出生的蘇俊是首位香港籍的青橙學者,也是第六屆青橙獎最年輕的獲獎人。他染著一頭金發,外形酷似時尚博主,喜歡潮流穿搭、愛追動漫、會根據心情切換發色,在小紅書上的人設是「染金發博導」。在這些標簽背後,他的正經職業卻是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裏最年輕的博導和獨立研究員。
從小在香港長大的蘇俊坦言自己高中前曾是個「學渣」,初中時因為物理成績不好,老師曾對蘇俊直言「科學太差」,被勸誡「不建議學理科」。蘇俊的父母則更希望他成為一個醫生,而蘇俊卻偷偷把誌願從醫學改成了「細胞級分子生物學」。回憶起首次透過顯微鏡觀察到活幹細胞的觸動,蘇俊說,「那一剎那,仿佛看到了生命之舞。」
從大學開始,蘇俊憑借優異成績獲得了各項獎學金和基金會獎勵,他向父母證明會對自己的選擇負責。本科期間,蘇俊完成了六次「輪轉」,利用寒暑假時間進入到不同的高校實驗室,從香港中文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哈佛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英國牛津大學到台北中央研究員,其間蘇俊接觸了肝癌分子機制、RNA、HIV愛滋病毒防治等不同方向領域,進一步明確了學術研究方向。
目前蘇俊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卵細胞染色體數目異常,另一個研究方向是早期胚胎發育。
「在生育中心裏面其實有高達一半的試管胚胎停止發育。這部份胚胎已經完成了精子和卵細胞的結合,在可放入子宮的成熟階段時發生了發育停滯,在臨床上只能被丟棄,我們希望能找到發育停滯的原因和有效的防治手段,去提高胚胎成活率。這項技術落地可以套用到輔助生殖中心去,減少女性在輔助生殖過程中的周期。」蘇俊在分享時表示,他的終極理想是用科學提高卵子與胚胎的質素,以減少女性經歷試管、流產、出生缺陷等造成的身體與精神痛苦。
談及軌域與曠野的討論,蘇俊認為自己一直以來都沒有任何軌域,「我面對的更多是科學問題,我應該怎麽樣去做,去解決它。當我解決了這個科學問題,我就可以把專註力放在其他的科學裏面,但這不代表說我們實驗室做的工作都是這邊打一槍,那邊又打一槍。而是說我們在決定換之前,真的是把原來的那個問題做到最深入。」
「我們就算在一個縱深的領域裏也是有很多方向的,我現在只是關註卵子,後面還會關註胚胎,包括子宮。只要你選定一個大的方向,在裏面繼續做,很多時候你會想出更多不同的想法,這些也是我們可以去繼續做的。」蘇俊補充道。
3
、「沈沒成本太高時不建議換方向」

曾也魯(35 歲/ 重慶)
中國農業大學土地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
中科院遙感地球所地圖學與地理資訊系統博士
在中國農業大學土地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中科院遙感地球所地圖學與地理資訊系統博士曾也魯看來,「軌域還是曠野,其實討論的是要不要輕易換方向,需要評估試錯成本。」
2011年,從被業內譽為「中國測繪遙感領域人才培養的搖籃」的武漢大學畢業後,曾也魯進入中國科學院遙感與數碼地球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讀博期間,曾也魯多次回到家鄉進行遙感影像分析工作。當這片原來他無比熟悉的土地,透過遙感影像呈現出40年乃至50年前的樣子,曾也魯產生出奇妙的感受,「在不同年代的遙感影像面前,你會覺得你的時間軸就被拉長了,空間也被拉遠了,會感到人類是很渺小的。」
遙感衛星成為了曾也魯的另一雙眼睛,遙感影像成為了他認識世界的新方式。但曾也魯並不滿足目前的視野,他想要看得更多、更遠、更清楚。針對於衛星訊號容易受到陰影、觀測角度影響等難題,曾也魯及其團隊提出了NIRv光子逃逸概率模型,將衛星觀測幾何不同帶來的誤差從30%控制在5%以內,這一研究被采納為新一代熒光衛星角度校正的三種演算法之一,並被 NASA 噴射推進實驗室與加州理工學院視作遙感基礎理論與方法的重要創新性成果。
「用衛星精準捕獲植物在光合作用中發出的熒光,監測地面上的每塊地、每棵樹」,曾也魯將自己的工作笑稱為「給地球做體檢」。這份「體檢」工作不僅能測量植被中儲存的碳及全球碳匯分布,還能透過診斷植物健康,助力智慧農業與鄉村振興,並為糧食安全做好預警。
「如果你把80% 以上的時間都砸在這一個方向上,有可能最後做不出來,這個時候損失就比較大。因此我們一般推薦在早期快速摸索出幾個相對有效的解決方案,然後再往前突,突到不太行了再換。但我們一般不傾向於你在做了很長時間,馬上可以收瓜、結果的時候去換方向。尤其是對於做學術來講,還是需要有相當長的時間投入。早期可以多聽聽長輩老師的建議,嘗試更換,但是在中後期,不是太傾向於換,那樣就像你追兩只兔子,一只都追不著。」曾也魯說。
此外在曾也魯看來,大學生畢業之後要不要從事本專業方向的工作時也會面臨類似的困惑,「我覺得同樣是越往上約不建議換,本科換的話沈沒成本不太高,但是到碩士、博士,換的沈沒成本是越來越高了。」
4
、「科研需要專註也需要自由探索,軌域和曠野不矛盾」

常林
北京大學電子學院研究員
美國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光子與電子學博士
北京大學電子學院研究員常林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整合光學,即在芯片上操控光的技術。相比於傳統的微電子技術,在芯片上引入光可以極大提升資訊的感知、傳輸與處理的能力。因此,整合光學所構建的光子芯片,被廣泛認為是下一代芯片技術的重要方案。
「光子本身是有著很多得天獨厚的物理優勢,如果我們可以在芯片上去操控光,那就可以實作資訊系統感知、處理以及傳輸效能的飛躍,有可能突破當前芯片制備工藝的困境,利用較大尺寸的晶圓來實作更高效能芯片的量產。」常林這樣描述他的研究目標。
這背後是一段「八年冷板凳」的故事。2013年,在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攻讀博士期間,常林師從國際著名整合光學專家、美國工程院院士JohnBowers教授。博士開始的第一天,JohnBowers教授遞給常林一份規劃書:「這是我們剛剛獲批的一個專案,要在芯片上對光的頻率實作10-15精度的頻率控制,你如果能完成它,將解決整合光學裏一個重大問題。」
當時懵懂的常林並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異常艱難、沒有任何人願意做的專案。他接手之後一做就是八年,對整合光學的研究貫穿了整個博士和博士後生涯。一直到2020年前後,他的專案最終完成,所產生的一系列的技術已經成為整個整合光學領域的通用技術。
目前的光子芯片的潛在套用領域包括激光雷達、光計算等,常林希望未來可以將傳統的GPU與CPU之間的互聯改成用光進行互聯,這將極大地降低功耗,提升算力。
「我個人的終極夢想是,在未來,光子芯片能跟電子芯片一樣去普及,在計算傳輸、激光雷達、血糖監測等領域都有所套用。」常林稱。
但半導體行業沒有捷徑。只有反反復復的失敗和重來。在常林看來,做科研失敗的時間永遠是比成功的時間要多,只有足夠熱愛才能堅持去做,這也是如今他在招收學生時最看重的特質之一。
「科研還是得有專註精神,特別是我們做芯片半導體行業,裏面很多技術的開發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積累,在這樣的一些領域,還是需要專註在一個固定的軌域裏來做。」對於軌域和曠野的選擇,常林如是向南都記者表示。
但與此同時,常林認為,從事科研,尤其是高校科研,也需要很多自由探索的精神。「因為科研的本質都是源自於對這個領域的熱愛,不管是我還是我的學生,這都是我們最原本的動力。如果你本身對這個領域有熱愛,那你會不斷地去闖入一些無人區,去突破你的舒適區域,去做一些類似於在曠野裏探索的工作。如果一直重復做沒有探索性的工作,會很難得到正向反饋,也很難堅持下去。我覺得從這個意義上講,軌域和曠野並不是一個矛盾的事情。」
南都記者 馬寧寧 發自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