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虞鑫(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新聞輿論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王金鵬(通訊作者,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來源: 【青年記者】2024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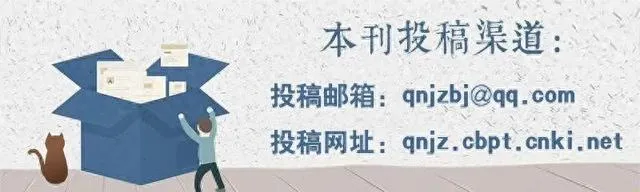
導 讀:
隨著理論與實證研究的不斷增加,資訊繭房研究的「內眷化」趨勢愈發顯著,面臨著從量變到質變的臨界點。本文旨在從宏觀上回顧資訊繭房的相關研究,把握這一研究領域的整體取向、提出未來研究的可能進路。
一、引言
當前,互聯網與5G技術快速發展,網絡空間的資訊供給呈現指數級別的爆炸性增長,尤其在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資訊超載已切實成為每一名互聯網使用者所面臨的問題之一。在促進資訊供需匹配、提高資訊傳遞效率的過程中,以人工智能為基礎的演算法推薦技術應運而生,透過演算法模型挖掘、使用者數據分析的方式,解決近乎海量的網絡資訊與使用者有限的註意力之間的供需矛盾,並廣泛套用到了網絡資訊生態的方方面面。智媒時代已然到來。然而,人工智能逐漸地改變了使用者關於資訊消費的個體習慣和社會規範,帶來了一些潛在的風險與隱憂。在互聯網與社交媒體上,人們越來越難以接觸到自己認知領域之外的內容,日常接受的主要是與其已有興趣和觀點相符的資訊,形成所謂的「資訊繭房」(information cocoon)。
這一比喻最早由桑斯坦在其著作【資訊烏托邦】中提出,用以描述在網絡資訊傳播過程中,公眾只關註自己選擇的內容和使自己得到愉悅的資訊,久而久之就將自身桎梏於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之中[1]。作為一個簡單明了的比喻,「資訊繭房」一詞在近年來引發了大量關註,尤其是在討論社交媒體、演算法推薦技術及其潛在的個人資訊消費與群體極化風險時。然而,一些探討資訊繭房效應的文章也容易望文生義,將其視作理所當然的先驗假定,進而在實際研究中忽視其意涵和語境並構成歧義[2]。在過去的五年間,圍繞資訊繭房效應的研究不在少數,主要包括資訊繭房的現象實證、成因機制、現實影響與治理對策等方面內容。隨著概念探討的不斷深入、實證研究的不斷增加,資訊繭房研究的「內眷化」(involution,本文用李金銓教授的轉譯「內眷化」而非通譯的「內卷化」,取向內眷顧之意,指只向內求索問題和理論資源,而不外顧,視野越縮越小,缺乏理論創新)趨勢愈發顯著,面臨著從量變到質變的臨界點。因此,有必要從宏觀上回顧資訊繭房效應的相關研究,把握這一研究領域的整體取向,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未來研究的可能進路。
本文從資訊繭房及其相關概念的傳播語境切入,對既有研究存在的技術中心路徑和受眾中心路徑作比較分析,對比提煉該研究領域的整體脈絡,從而為資訊繭房效應的未來研究提供思考與借鑒。
二、資訊繭房的概念之辨
資訊繭房來源於人們自身的資訊需求偏倚,是選擇性心理的體現,人們傾向於選擇那些自身感興趣、意見相同並且沒有沖突的資訊。這種現象不是演算法時代所獨有的,而是伴隨著人類社會長期存在的。從心理現象到媒介現象,資訊繭房所指向的內涵似乎始終落在以自我為中心的內容資訊變得更加狹窄和封閉上;然而,資訊繭房的隱憂不僅僅在於個人層面的資訊窄化,更在於社會層面上對協商民主造成的風險。後者正是桑斯坦提出資訊繭房時的語境所在:由於資訊繭房的存在,公眾無法與資訊環境進行全面的互動,而是沈浸在自身所偏好和認同的內容當中,最終使得意見一致的觀點在一個封閉的圈子中不斷地被重復和強化,形成「回聲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3]:人們在不斷放大自身資訊偏好的同時,也在阻礙著多元觀點的流通和討論,甚至帶來群體極化的風險。在桑斯坦看來,日益普遍的資訊過濾技術很可能破壞潛在的公共協商,並且威脅到西方民主社會的理想模型。由此可見,技術批判與協商民主二者共同構成了理解資訊繭房與回聲室效應的理論背景,而不能將資訊繭房簡單化為內容的相同或相異,後者是現象而前者是本質。
在桑斯坦提出資訊繭房與回聲室概念之後,隨著傳播方式變得更加智能化和分眾化,帕裏澤提出了「過濾氣泡」的概念,以強調互聯網資訊過濾對使用者的影響。他認為,搜尋引擎等演算法使人們處於個人化、獨特的資訊環境中,而這種環境是由一系列基於使用者資訊和行為構建的過濾器所創造的;演算法在了解使用者偏好並過濾異質資訊的同時,也無形之中構築起了一道道「隔離墻」,將人們困在演算法創造的「網絡泡泡」中,並阻礙著多元觀點之間的交流[4]。
可以說,資訊繭房、過濾氣泡和回聲室這三個「比喻式」的概念共同構成了現有關於資訊繭房研究的核心概念簇。三者之間既有相似之處,又各有側重(見表1)。
表1 資訊繭房、過濾氣泡與回聲室的概念比較

具體來說,資訊繭房側重於個體的資訊獲取行為,具有明顯的個人偏向性,而回聲室側重於群體或系統的意見聚合與觀點強化,指向群體層面的極化風險。可以說,回聲室效應是資訊繭房所產生的後果之一,二者均指向受眾或使用者層面的資訊接觸行為,而過濾氣泡則更多地指向技術層面的客觀因素,即演算法技術所創造的同質化的資訊環境。過濾氣泡的提出,實質上是將資訊繭房與回聲室的形成直接地歸因到了推薦演算法為代表的資訊科技身上,而這恰與資訊繭房與回聲室效應的技術批判理路相一致,從而構建出「演算法推薦—過濾氣泡—資訊繭房—回聲室效應—群體區隔—群體極化」的邏輯鏈條。
現有研究中,國內學界多采用資訊繭房一說,而國外研究多以回聲室效應和過濾氣泡作為核心概念。回聲室效應主要在政治傳播領域得到檢驗,因其刻畫出公眾在社交媒體中所存在的偏向性是無法避免甚而得到加強的,而過濾氣泡則常用於與資訊多樣性相關的研究。相比之下,資訊繭房研究主要為規範性論述,並且存在將資訊繭房視作既定存在的傾向,從而忽略了其作為假說提出的本意[5]。正因如此,資訊繭房研究需要超越思想實驗下的單純資訊環境、從人們真實的資訊環境出發[6],關註復雜多元的媒介環境下的受眾使用者,以及使用者與演算法之間的張力。使用者不僅是演算法內容的接受者,也可以是演算法內容的客製者,因而資訊繭房所隱含的技術批判不僅指向內容同質化本身,更是對於人們可能喪失尋求媒介多樣性的憂慮[7]。近年來,資訊繭房的實證研究數量逐步上升,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聚焦資訊繭房的存在檢驗與成因機制,研究者們的視野也逐漸從媒介技術轉向受眾中心的研究。
三、技術中心的研究:演算法會導致資訊繭房嗎
數碼時代資訊繭房的形成與前數碼時代最大的不同就在於,這一時期出現了人工智能演算法並得到了大規模套用。互聯網技術帶來的資訊爆炸推動著資訊分類與過濾機制的出現,不論是分類目錄、搜尋引擎還是演算法推薦,其設計初衷都在於提高資訊匹配和傳遞效率。如果說互聯網技術為資訊繭房的形成提供了有跡可循的現實空間,那麽演算法提供的個人化推薦和場景化適配,則為人們選擇並沈浸於自己感興趣的資訊內容提供了技術支持,使人們成為「被演算法餵食的受眾」。隨著技術的叠代與套用,由演算法推薦的資訊總量已遠遠超過了人工篩選。因此,開啟「演算法黑箱」、檢視演算法環境成為資訊繭房研究在一段時期內聚焦的主要議題。
推薦演算法並不是某一種特定的運算,而是一類演算法的統稱。根據技術原理的不同,推薦演算法一般可以分為三類:基於行為的協同過濾、基於內容的推薦和基於語意的推薦[8]。協同過濾演算法指的是依據行為的相似性進行推薦,將行為類似、情況相似的使用者關聯起來,從而向目標使用者推薦該群體中其他使用者瀏覽過的內容。基於內容的推薦演算法則是從使用者的歷史瀏覽內容中提取標簽,透過相似標簽的推薦或是與使用者自身的標簽相匹配建立模型,從而實作內容推薦。基於語意的推薦演算法則是從使用者歷史數據中挖掘出潛在的關聯規則,透過把握使用者實際意圖、分析潛在需求實作內容推薦,旨在「相關」而不僅僅是「相似」。特別地,在新聞與社交媒體領域,使用者的發文量、時間的遠近順序在判斷什麽樣的內容應該得到推薦時也很重要,這實質上是在熱點辨識演算法的基礎上所進行的內容推薦。
演算法會導致資訊繭房嗎?這是在技術批判理路下資訊繭房研究的核心問題。盡管學界業界普遍承認演算法是一項重要因素,但也都基本否定了技術決定的結論,轉而進行更為細致的考察。
一方面,學者們從技術原理方面展開對於推薦演算法邏輯的研究,試圖開啟資訊繭房背後的「演算法黑箱」。有學者透過實驗發現,比起推薦機制本身,更為具體的演算法細節才是影響資訊繭房的重要因素[9]。一些研究者認為,基於內容的推薦演算法更容易造成資訊繭房現象,因為這類演算法盡管容易取得較高的匹配度,但由於偶然機制的缺乏,難以挖掘使用者的潛在興趣,容易造成過度個人化的情況;相較之下,基於協同過濾的演算法則由於群體小組的隱性劃分,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發掘使用者潛在興趣,弱化資訊繭房效應[10]。基於語意的推薦演算法為避免資訊繭房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有助於突破前兩類演算法囿於結構化資訊分析的困局,擴大使用者的資訊獲取範圍。此外,演算法也關切著不同的身份群體,有研究者從闡釋主義路徑出發,以學者、媒體從業者和技術人員等不同視角,研究他們對於「演算法與資訊繭房之間的關系」的不同闡釋[11]。
需要註意的是,所謂「演算法模型」,其本質就在於以知識、經驗或統計的方法構建出一套能夠預測的執行邏輯,盡管能夠從統計學上賦予其一定的隨機性,但其結果一定是依據過去的現實經驗推向未來。在這個意義上,演算法是天然地排斥偶然性的,這也就決定了它與資訊繭房之間難以脫離幹系。
另一方面,學者們從演算法環境著手,分析推薦演算法影響下的資訊環境與互動內容,從而為演算法與資訊繭房效應之間的關聯提供佐證。與基於技術原理的正向推理不同,有研究者從新聞推薦的結果逆推推薦演算法的價值觀,驗證了演算法環境下的資訊窄化現象[12]。同時,社交媒體上的大量內容也為資訊繭房與回聲室效應的驗證提供了充足的數據。一項關於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的Facebook新聞研究發現,使用者對於社交媒體的使用與言論的去極化螺旋呈現正相關性[13],從而間接地反駁了回聲室效應的存在。在國內,有學者檢驗了10種網絡媒介的資訊繭房效應,發現推薦演算法並非必然造成繭房,傳播結構的水平與垂直、使用者聯結的開放與封閉才是網絡媒介是否帶來資訊繭房效應的關鍵機制[14]。
這些對於演算法環境的考察無疑豐富了演算法與資訊繭房之間的關系研究,在復雜、多元的現實媒介環境中理解資訊繭房效應。然而,這一研究路徑本身對於概念的取用不見得與資訊繭房直接對應,實際上更為貼近的概念是過濾氣泡與回聲室效應,前者指向演算法本身抑制了資訊多樣化,而後者與社會網絡、群體極化關系甚密。
由此產生的另一個問題是,是否有必要嚴格地將資訊繭房研究、過濾氣泡研究與回聲室效應研究區別開來。本文認為無此必要,因為這三個關鍵概念之間的關系十分緊密,可以說是同一現象的不同視角,在研究脈絡中亦難以隔斷。但是,在實際研究中,有必要明確自己研究的前提假設、研究路徑與分析側重,而不是簡單地采用資訊繭房這一說法。由此,盡管一些研究仍然以「演算法會導致資訊繭房嗎」作為理論關切,但更像是立下了一個可供駁斥的靶子,進而納入個體特征、社會關聯等其他因素作為資訊繭房的前置條件進行分析。
四、受眾中心的研究:個體特征、社會關聯與特定情境
隨著研究者們愈發意識到資訊繭房的受眾視角與個人內容,資訊繭房研究逐漸開啟了以受眾為中心的研究路徑。這裏的「受眾」其實就是使用者,前者能夠與大眾傳播時代延續下來的受眾研究傳統相呼應,而後者避免了傳統受眾研究中對於受眾主體性的忽視。麥奎爾將20世紀以來的受眾研究歸納為三類傳統:結構主義傳統、行為主義傳統和文化主義傳統[15]。結構主義傳統是早期媒體產業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旨在調查媒體渠道的受眾規模、覆蓋程度(如廣播的收聽率、報紙的讀者數量)與受眾的社會構成(如黨派從屬、地理區域)等,從而為媒體的經營與管理提供參照。行為主義傳統以媒介效果研究為代表,既包括媒介對受眾可能產生的認知、態度或行為的影響,也包括受眾選擇媒介和媒介內容的動機、特點和主動性。文化主義傳統強調媒介使用是特定社會文化背景的反映,並且是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以及將受眾理解為「闡釋共同體」(interpretive communities)並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前者偏好於調查、實驗等量化方法,而後者更註重質性方法,但二者之間亦存在相互融合的趨勢。
借鑒受眾研究的一般思路,既有受眾中心的資訊繭房研究主要考慮以下三類因素的關聯性。
一是個體特征。 作為源自選擇性心理的媒介現象,資訊繭房的形成首先受到受眾自身因素的影響。有研究者以紮根理論的方法提煉了資訊繭房的成因及後果,發現人口特征、性格、習慣、興趣、效率以及反饋行為都是資訊繭房的影響因素[16]。人口特征方面,有研究認為收入和學歷等社會性差異導致的資訊鴻溝比演算法帶來的資訊窄化現象更值得警惕[17]。性格方面因素既包括長期穩定的好奇心、包容心等,也包括短期特定的情緒和情感[18]。資訊興趣同樣是導致使用者形成資訊繭房的關鍵要素[19],而在習慣上,使用者對於特定媒介環境、技術或內容的偏好和依賴都能影響資訊繭房。相較於「被動」地消費內容,效率因素則更多地與媒介使用的目的相關,也在一定程度上強調了使用者「主動」的資訊需求。更進一步地,不少使用者在瀏覽媒介時會將不感興趣的內容標記為「不喜歡」,並透過點贊、關註等方式達到馴化演算法的目的[20]。此外,演算法素養[21]、演算法知識[22]等因素也頻繁地出現在資訊繭房相關研究中,本文將其籠統地概括為媒介素養。
二是社會關聯。 社會網絡分析的興起為研究資訊繭房和回聲室提供了新的思路與方法,盡管這一群體層面下的網絡分析更多地對應於回聲室效應而非資訊繭房,但個體在社會網絡中所處的位置以及社會資本等因素,仍然有助於研究者們從社會結構和資訊流動視角分析資訊繭房效應。一項關於推特內容和社交網絡的分析研究表明,社會網絡中存在著推動群體內部資訊流動的「回聲者」(echo chambers)和與外部群體成員進行溝通的「橋梁者」(bridgers)[23]。另一項內送流量備援容錯機制體仿真研究也表明,個體網絡中心性與回聲室效應有著顯著相關關系,而個體在社會網絡中的地位對其回聲室效應有明顯影響,從而驗證了社會資本理論對回聲室效應形成的解釋力[24]。在對新浪微博的樣本分析中,有研究者發現,隨著資訊繭房程度加深,使用者的情感偏向與資訊繭房頂部的使用者越來越相似[25],從而呈現出「繭房」趨同化,或者說「公共資訊繭房」[26]。
三是特定情境。 資訊繭房得到廣泛關註的主因是人們對演算法技術發展的憂慮,在研究中的體現就是將演算法媒介作為最主要的討論情境。與技術中心的演算法環境研究相比,受眾中心的研究盡管同樣著眼於演算法與資訊繭房的關系,但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路徑是受眾本位的。實際上,關於情境可以作出多種區分,形式上包括單一媒介與多元媒介、垂直媒體與水平媒體等。有學者試圖超越單一媒介環境的研究條件,以日誌法追蹤使用者的跨媒體平台接觸行為,研究使用者資訊偏好、媒介使用與多樣化資訊接觸的關系[27]。在內容情境上,人們在不同議題中呈現的資訊繭房效應亦可能存在區別,難以一概而論。據此,有學者將職業、性別和網絡世代中存在的輿情遮蔽作為研究物件,分析其中具體表現出的資訊繭房現象[28]。此外,亦有研究者關註資訊平衡與否對於資訊繭房的影響[29]。
可以發現,資訊繭房效應的確有著較為復雜的成因,在不同的個體、社群和情境中呈現出較為不一致的景象。盡管當前一些研究正嘗試歸納其中的結構性規律,但整體上看,受眾中心的資訊繭房研究還存在一些問題。一方面,資訊繭房研究仍然缺乏大量的實然性檢驗,許多論文以規範性探討為主,對於不同情境、不同社群的研究較少;另一方面,現有資訊繭房研究的理論創新性不足,對其成因的探討不在少數,但尚未從影響因素當中提煉出有見地的理論模型。更多的文章在模糊地取用資訊繭房概念之後,便不假思索地在其基礎上進行演繹推理。總的來看,資訊繭房研究的「內眷化」趨勢愈發明顯,需要量的積累以達到質的突破。
五、結語:資訊繭房研究走向何處
那麽,資訊繭房研究既已走到創新的十字路口,又將向何處著力?延續資訊繭房與回聲室效應的雙重語境——技術批判與協商民主,本文認為,資訊繭房研究還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需要解決。
首先,需要再次強調,資訊繭房的技術批判視角意味著受眾沈浸於單一、同質的內容,難以自主地尋求內容多樣性,而不僅僅是內容的同質化。那麽,現實的狀況是否如此,作為反價值理性的資訊繭房效應是否切實存在?盡管資訊繭房的合理性已經得到廣泛的共識,對其進行存在性檢驗仍是開展其相關研究的基礎所在。進一步地,資訊繭房的形成是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社交網絡、平台、演算法等都有可能固化人們的資訊獲取路徑、強化人們的選擇性心理。那麽,哪些因素在什麽情境下容易讓人們沈浸於資訊繭房之中?這其中也包括與演算法關聯的問題,即人們是否在演算法環境中更容易喪失自主性與批判性?資訊繭房研究的下一步,必然走向更為縱深和細致的考察,主要包括偏量化的行為主義與偏質性的文化主義兩條進路。前者旨在更為細致、系統地考察資訊繭房的成因機制,透過探究不同個體、社群和情境下資訊繭房效應的結構性規律,提煉理論模型;而後者主要從實踐中著手,更加細致、質性地考察具體情境下的資訊繭房效應本身,以期豐富概念的面向與維度。
其次,如果說技術批判視角下的資訊繭房研究註重於其形成原因,那麽政治民主視角下的資訊繭房研究則更多地關註其社會影響。然而,由於國內外研究的概念偏倚,國內主流的資訊繭房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概念本身與政治民主之間的關聯,也就致使關於資訊繭房的政治社會影響研究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在桑斯坦的論述中,資訊繭房效應存在著降低政治資訊多元化的風險,而回聲室效應則與政治資訊、政治群體的極化相關。延續這一思路,首先需要回答的問題是資訊繭房是否在技術批判與政治民主視野下具有同一性。換言之,作為「憂慮」的反價值理性的資訊繭房,是否確實等同於與特定政治或其他內容的資訊接觸?二者之間存在著互為因果的可能性,類似於使用與滿足理論和涵化理論的關系,即出於沈浸繭房而選擇特定內容,抑或是由於接觸特定內容而沈浸於繭房?另外,關於資訊繭房和回聲室效應的聯系,盡管二者有著極為緊密的關系,但仍存疑問的是,個人層面的資訊繭房是否必然造就群體層面的回聲室效應?本文認為並不能夠簡單地透過原子論式的推理,將個體陷入某類資訊繭房與群體構成特定的回聲室等同起來,這一過程的明晰需要社會網絡的思維與綜合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礎上,如果回聲室效應存在,它是否確與群體極化之間存在關聯?關聯的條件和要素又是什麽?這些問題嚴格來說已經超出資訊繭房的概念內涵,而應該被界定為回聲室效應研究,但出於資訊繭房的政治民主後果的考量,仍有必要提及於此。
最後,要重視與資訊繭房相關的理論構建與創新。微觀上看,資訊繭房效應的產生從屬於個體的認知過程,涉及資訊的接收和處理、態度與行為改變等問題,但由於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不足,尚未提出具有代表性的理論模型。宏觀上看,資訊繭房效應的結構性因素是一段時間內的主要研究方向,但同時,也有必要跳出桑斯坦的協商民主框架,為資訊繭房概念賦予新的理論意涵。例如,有研究將資訊繭房同虛假資訊聯系起來,探討資訊繭房效應對於使用者虛假資訊辨識能力的影響[30],有研究基於資訊繭房概念提出政策繭房[31]。這類研究無疑豐富了資訊繭房效應的概念外延和學科範圍。當前學界有相當一部份文章探討如何破解資訊繭房問題,但能夠上升到理論層面的成果較少。本文認為,在進行前述所有研究的過程中,對於如何破解資訊繭房這一問題的回答也就自然浮現了。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專案「突發公共事件中媒體堅守新聞真實性的路徑、機制」(批準號:21CXW001)、清華大學自主科研計劃「智能時代的認知戰作用機制研究」(編號:2023THZWYY05)、清華大學「清新計算傳播學與智能媒體實驗室研究支持計劃」(編號:2023TSJCLAB001)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Sunstein C R. Infotopia: 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陳昌鳳,仇筠茜.「資訊繭房」在中國:望文生義的概念與演算法的破繭求解[J].新聞與寫作,2020(01):58-63.
[3]Sunstein C R. Republic.Com 2.0[M].New York: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4]Pariser E.The Filter Bubble: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M]. New York: Penguin Press,2011.
[5]丁漢青,武沛潁.「資訊繭房」學術場域偏倚的合理性考察[J].新聞與傳播研究,2020(07):21-33.
[6]陳昌鳳,仇筠茜.「資訊繭房」在西方:似是而非的概念與演算法的「破繭」求解[J].新聞大學,2020(01):1-14.
[7]虞鑫,王金鵬.重新認識「資訊繭房」——智媒時代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共生機制研究[J].新聞與寫作,2022(03):65-78.
[8]孫少晶,陳昌鳳,李世剛,等.「演算法推薦與人工智能」的發展與挑戰[J].新聞大學,2019(06):1-8.
[9]劉茜,湯清揚,閔勇,等.新聞推薦必然導致「繭房」效應嗎?——基於模擬新聞平台的實驗研究[J].新聞大學,2023(02):28-43.
[10]陳昌鳳,師文.個人化新聞推薦演算法的技術解讀與價值探討[J].中國編輯,2018(10):9-14.
[11]晏齊宏.技術控制擔憂之爭議及其價值沖突——演算法新聞推薦與資訊繭房關系的多元群體再闡釋[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0(03):59-65.
[12]王茜.開啟演算法分發的「黑箱」——基於今日頭條新聞推播的量化研究[J].新聞記者,2017(09):7-14.
[13]Beam M A, Hutchens M J, Hmielowski J D. Facebook news and (de)polarization: reinforcing spirals in the 2016 US election[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8,21(7):940-958.
[14]施穎婕,桂勇,黃榮貴,等. 網絡媒介「繭房效應」的類別化、機制及其影響——基於「中國大學生社會心態調查(2020)」的中介分析[J].新聞與傳播研究,2022(05):43-59.
[15]丹尼斯·麥奎爾.麥奎爾大眾傳播理論[M].徐佳,董璐,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9:342-343.
[16]楊雨嬌,袁勤儉. 個人化推薦的隱憂:基於紮根理論的資訊繭房及其前因後果探析[J].情報理論與實踐,2023(03):117-126.
[17]喻國明,方可人.演算法型內容推播會導致資訊繭房嗎?——基於媒介多樣性和信源信任的一項實證分析[J].山東社會科學,2020(11):170-174.
[18]Wollebaek D, Karlsen R,Steen-Johnsen K,et al. Anger,Fear, and Echo Chambers:The Emotional Basis for Online Behavior[J]. Social Media+Society,2019,5(2).
[19]張海,徐紅昌.S-O-R理論視角下網絡使用者資訊繭房成因要素研究[J].新世紀圖書館,2022(12):15-22.
[20]李錦輝,顏曉鵬.「雙向馴化」:年輕群體在演算法實踐中的人機關系探究[J].新聞大學,2022(12):15-31.
[21]楊洸,佘佳玲. 新聞演算法推薦的資訊可見性、使用者主動性與資訊繭房效應:演算法與使用者互動的視角[J].新聞大學,2020(02):102-118.
[22]張海.網絡使用者資訊繭房成因及影響因素維度研究[J].情報雜誌,2021(10):166-170.
[23]Tsai W S, Tao W, Chuan C, et al.Echo chambers and social mediators in public advocacy issue networks[J].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020,46(1).
[24]李衛東,彭靜.社交網絡平台資訊傳播的回聲室效應仿真實驗分析[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9(04):142-149.
[25]徐翔,董潔蕓.社交網絡內容生產中使用者「資訊繭房」的情感偏向研究[J].全球傳媒學刊,2022(04):78-99.
[26]徐翔.公共資訊繭房:社交媒體資訊內容收斂現象與效應——基於新浪微博的文本挖掘[J].情報雜誌,2023(01):113-123.
[27]晏齊宏,蓋赟.資訊繭房之外:跨媒體視角下使用者資訊接觸的多樣性研究[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3(05):76-85.
[28]鄭滿寧,李彪.輿情治理視域下社交網絡中的資訊繭房現象與破繭之道[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04):140-144.
[29]傅詩婷,姜婷婷,田慧溢.平衡資訊接觸能否幫助人們打破資訊繭房?資訊感知與態度變化的關系研究[J].資訊資源管理學報,2023(01):41-51.
[30]莫祖英,盤大清.資訊繭房效應對使用者虛假資訊辨識能力的影響關系探析[J].圖書館學研究,2023(03):50-57.
[31]曾潤喜,楊璨.資訊時代的政策繭房現象與政策傳播效能提升路徑研究[J].中國行政管理,2023(09):132-141.
本文參照格式參考:
虞鑫,王金鵬.從技術到受眾:資訊繭房效應的研究取向與發展進路[J].青年記者,2024(04):78-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