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國科學報】記者 張晴丹
在北京大學,未名湖已成必打卡景點,有人欣賞湖畔的楊柳依依,有人在滿湖彌漫的靜謐光芒中感受時光流轉……但「80後」博導江穎則與眾不同,他透過觀察湖面,思考出一個科學問題。
冬日的一次散步,江穎發現湖面上有很多像波紋一樣的漣漪,原以為沒有結冰,但當用手一摸時發現表面已是固態,就連那些褶皺都是硬的。亦冰亦水的奇特現象,讓江穎倍感新奇,他趕緊拍了照片發朋友圈,配文是「湖面上是水還是冰?」
很快,許多人在下面留言討論起來,其中好幾位老師都認為冰表面很值得研究。江穎回復說:「好主意,設計個實驗試試!」
一個新課題就這樣誕生了!
江穎帶著學生開始探究冰表面到底長啥樣。6年時間,他不僅自主研發出中國第一台光耦合qPlus型掃描探針顯微鏡,還從原子尺度上揭開了有關冰的一系列未解之謎,給出了冰表面預融化這一長達170多年的爭議問題的答案。無論是研究的創新性,還是文章的完整度,都贏得審稿人一致的高度贊賞,於日前發表在 Nature 雜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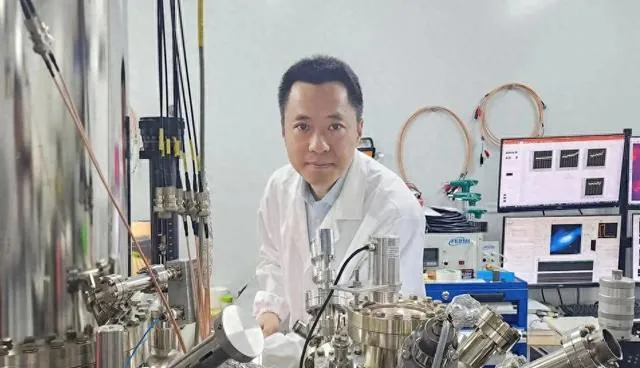
江穎
審稿人:這是前所未有的分辨率
冰,這個大家很常見的物質,對科學家們來說卻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它的表面遠比看起來要復雜得多,早在1842年,法拉第就提出冰表面會在0℃以下開始融化的概念,圍繞預融化問題的爭論已持續了170多年。
持續如此之久的原因在於,現有的研究手段還無法達到原子尺度的實驗表征。冰表面結構究竟是什麽?這一基礎問題,仍然無人解答。換言之,誰實作了冰表面的原子級分辨成像,誰就掌握了解密冰的鑰匙。
江穎團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大自然中最常見的六角冰在實驗室裏完美地制備出來。而下一步用探針進行表面的掃描,是整個環節裏最難翻越的山丘之一。
高分辨的掃描探針顯微成像需要尖端非常尖銳的探針,其制備通常是在導電的金屬襯底上完成的。糟糕的是,冰表面恰好是一個絕緣體,因此不能在其表面進行原位針尖的修飾。
江穎在紛亂的思緒中捕捉到了一絲光亮,他提出一種方法,即在金屬表面先制備好合適的針尖,然後將它轉移到冰表面進行掃描。聽起來很簡單的一個過程,在落實的時候難倒了眾人。
「把針尖從一個表面轉移到另一個表面後,針尖的尖端結構以及吸附的單分子很容易變化,我們很難保證在轉移過程中,這個針尖還能維持原來的最佳狀態。」論文通訊作者、北京大學物理學院教授江穎在接收【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說。
「經過無數次改進,我們才開發出通用的一氧化碳分子修飾針尖技術,成功解決了將修飾好的針尖從一個樣品無失真轉移到另一個樣品的問題,可在任何絕緣體表面實作穩定的原子級分辨成像。」論文共同第一作者、北京大學物理學院特聘研究員田野告訴【中國科學報】。
在這項工作中,課題組還遇到了一個障礙。在對冰表面進行表征時,他們發現表面總是非常無序。「按理說,生長溫度在零下100多℃可以得到有序的晶體結構。但我們反復測量,得到的都是無序的結構,這太讓人困惑了。」江穎表示。
後來他們進行了系統的變溫生長實驗發現,其實冰表面的預融化溫度非常低,在零下153℃就會開始融化,之前得到的無序結構都是融化了的冰表面,需要在非常狹窄的溫度區域才能找到冰表面晶化的結構。這樣的結論直接顛覆了長久以來人們對冰表面結構和預融化機理的傳統認知。
江穎團隊自創的一系列技術,首次在冰表面看清並定位世界上最小的原子——氫原子。冰表面原子分辨成像的實作,令很多國內外同行感到不可思議。該文章其中一位審稿人曾試圖用原子力顯微鏡得到冰表面的結構,但依舊沒能實作真實的原子級分辨影像。審稿人贊嘆,這是前所未有的分辨率。
從「車間技工」開始
江穎創制頂尖器材的高超技藝並非與生俱來,相反,他花費了比旁人更多的心血和時間。
當年,在他的導師、中國科學院院士王恩哥的建議下,江穎到美國加州大學艾榮分校Wilson Ho(何文程)院士課題組從事博士後研究。「王老師的戰略性眼光令我欽佩,他認為這個課題組是我們做這個領域一定要去的地方。這是個非常特立獨行的課題組,因為組裏沒有一台商業化的器材,所有的器材都是自己研發的,簡直太震撼了。」
Wilson Ho說過,用別人沒有的器材去做實驗,得到的結果一定是最新的,而且很可能是突破性的成果。
科研器材是科學家的「眼睛」,是原創性科研成果的重要手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諾貝爾自然科學類獎項中,68.4%的物理學獎、74.6%的化學獎和90%的生理學或醫學獎的獲獎成果都是借助各種先進的科學器材完成的。
以掃描探針顯微鏡為例,其最重要的貢獻就是能夠對表面的原子進行直接成像,改變了人類對物質的一些研究範式和認知。它的出現,開創了很多前沿領域,例如納米科學領域。
江穎也深知器材之於研究的意義,在美國兩年博後時光,讓他對搭建器材有了最深刻的體驗。
一開始的處境可以說是舉步維艱。「我在國內時沒有經過這樣的培訓,我們都是用商業化器材做實驗,而且做的實驗也是比較粗淺簡單的,與國外頂尖的水平差距很大。所以到Wilson Ho的組裏後,經歷了非常低迷的時期,我的能力與大家很難‘接軌’,心理落差極大。」
這條路沒有捷徑可走,唯有從頭學,投入比別人更多的時間。江穎在工廠車間做了近4個月的「技工」。早上用軟件畫圖設計零件,下午就拿圖去車間用銑床、車床加工,晚上回到實驗室組裝並測試。那時候經常會出現尺寸有問題的情況,淩晨一兩點再去返工,回到家時已是淩晨三四點。
工人在加工零件時都是站著的,江穎也不例外。時間長了身體累得吃不消,於是他中途會坐下休息一兩個小時,利用這點時間讀文獻,以盡快彌補自己在基礎知識上的欠缺。
這樣長時間流水線式的連軸轉,對體力、腦力消耗極大,每次淩晨三四點回到家後,江穎都感覺饑腸轆轆,最方便的只有煮面。「盡管已經特別小心翼翼了,但開火煮、洗碗等動作仍難免弄出很多聲響,我當時住的房子還有三四個合租者,他們經常向房東投訴。後來,我索性直接買麪包充饑。」
持續磨練後,江穎的動手能力迅速提升,慢慢能跟上大家的進度。他早已習慣了夜深人靜時工作的高效率,所以從「車間技工」進階到做實驗時,他依舊保持相同的作息。
做實驗既枯燥又壓力大。唱歌就成了最有效的解悶方式。「我和另外一個實驗搭檔,經常熬到實驗室整棟樓其他人都走光後,將音響音量開到最大,用跑調的嗓音夜半高歌。」空蕩的實驗室裏,一唱一和深情演繹著老歌【天高地厚】,兩種截然不同的聲線時而交織,時而獨秀,讓無數個乏味寂寥的夜也變得明朗起來。
江穎很感謝也很慶幸自己在博後期間踏踏實實當好一名「技工」,正是那幾個月的魔鬼訓練,讓他獲得了導師的「真傳」,才有了搭建頂尖器材的底氣。

江穎
造一流器材是江穎深埋心中的一個夢。但這也是一項極限挑戰,江穎用了十來年時間成功制備出中國第一台qPlus型掃描探針顯微鏡。這個類別的顯微鏡是目前掃描探針顯微鏡家族裏空間分辨率最高的,目前已實作商業化套用。
有了如此精密的器材,再加上高超的實驗技術,江穎團隊與合作者接連突破前沿研究,屢創新高,在不到一個月時間裏,成果相繼發表於 Nature 和 Science 。
基於這麽多年的一線實戰,江穎悟出了一個規律。當把每一個細枝末節的過程都摸清後,你會發現那些處於頂端的科研器材也並非那麽高不可攀,它們其實都是各種各樣的小步驟、小部件、小技術堆砌起來的,就好像拼樂高一樣。這可比研究量子力學要簡單得多,因為它畢竟是一種工程化技術,是非常直觀的東西。「無論你要研究發明哪樣全新的器材,都離不開這樣一個套路。」
實驗室裏永不畢業的「大師兄」
導師手把手帶出第一批學生後,後者又接著帶後招進來的新人,這種師兄師姐「傳幫帶」模式是很多實驗室的常規操作。但也有一個弊端,就是導師傳授的精髓很可能會打折扣。
為了能把自己長久科研實踐積澱的技術、經驗和眼界原原本本地傳授給學生,江穎始終堅守在科研的第一線,被學生們戲稱為實驗室裏永不畢業的「大師兄」。他很像是一個遊戲裏的NPC,無限迴圈地引導著一批又一批的學生完成科研目標,最終贏得榮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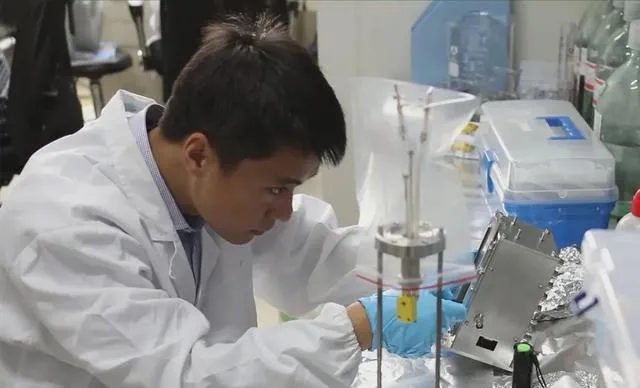
江穎 本文圖片均為受訪者提供
「博士階段大家年齡都不小了,具備一定的自主性,所以很多導師會‘放養’,但江老師會特別頻繁地出現在實驗室,他和我們一起參與到一項研究的方方面面。在他的羽翼下,我養成了很好的思維模式,擁有了搭建器材的硬實力。」田野說。
「做實驗久了難免感到枯燥和迷茫,當感覺自己做出來的數據沒啥意義時,我就喜歡找江老師聊聊天,他看問題的視角和方法總能啟用我那停擺的腦細胞。我們都不拿他當外人,有一回,實驗進展緩慢,有點心急了,當著江老師的面就哭了,他還好言好語安慰我。」論文共同第一作者、北京大學物理學院博士後洪嘉妮說。
在與學生的相處中,這位「大師兄」也不總是如此和顏悅色,偶爾也會展現嚴厲的一面。當學生得到比較漂亮的實驗結果時,江穎會適時地提出一系列質疑。質疑是對科學最基本的態度,江穎的「找茬」和潑冷水旨在激勵學生想方設法驗證結論,因為只有反復推敲、反復修正實驗現象和結果,才能百煉成鋼。
「我先做最嚴苛的審稿人,前期做實驗過程中就把很多不確定的問題徹底解決,學生們在我這裏先經歷預審稿後,將來投國際期刊時才能更順暢一些。」江穎說。
這套做法的有效性在他這篇文章投 Nature 時得到了印證。文章在第一圈評審後就被告知正式接收,這樣的特例聞所未聞。審稿人對這篇文章的創新性、完整性贊不絕口,認為這是一項完成得非常漂亮的工作。
在江穎的履歷上,已經收獲 Science、Nature 等論文數篇,但他並不要求每個學生畢業前一定要有好文章,重要的是掌握實驗技能,能夠獨立思考,將來獨當一面。
科研之所以讓很多人望而卻步,就在於付出再多,也不一定有預期的結果。就像航行的船只,在白霧彌漫的大海上摸索前行,卻不知道終點在何處。因此,江穎希望每位選擇科研這條路的學生對科研都是發自內心的熱愛,「只有熱愛你所從事的科研方向和領域,才能耐得住出成果前很長一段時間的寂寞」。
參考連結: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4-0742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