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從全球政治生態周期的角度考察,東亞經濟發展一直受到全球化主導國家內部政治變化的影響,這裏所指的是位於大洋彼岸的超級大國,它對全球體系的政策調整直接作用於海外地區。
雖然當時日本的經濟泡沫破裂主要由其內部結構性問題引起,例如借貸過度用於經濟發展,導致資產泡沫嚴重,80年代末的東京房價居然高到可以購買美國所有土地,這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但是,大洋彼岸當時的對日外交政策同樣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01
眾所周知,上世紀80年代末,美日簽署了廣場協定,迫使日元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制造出口能力。當時美國由共和黨的喬治·H·W·布殊掌權,其保守的行政作風勢必導致日本作出妥協。然而,到了1991年,隨著房地產泡沫破裂,美國總統由共和黨轉為民主黨的比爾·克林頓,廣場協定被實際上廢除。
按照邏輯,這時的日本應該感到松了一口氣,但在接下來的六年裏,隨著經濟泡沫的破滅風險擴散,直至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日本正式陷入資產負債表衰退,難以自拔。

那麽1991-1997年這六年期間,日本全國各級都在忙些什麽呢?
其政府部門的做法與我們類似,都在努力維持房地產市場穩定,避免其崩潰,但無法阻止市場下跌,這六年中房價普遍下降了三成,與我們目前的房市狀況頗為相似。在利率方面,也是受到金融機構的凈利差和以往高債務等問題制約,降息步伐異常緩慢。
至於居民和企業部門,由於之前向金融機構借入的貸款規模龐大,加上房市下滑導致的不景氣環境,獲得的收益和利潤大幅減少,他們不得不優先考慮提前還債,用所有現金流維護信用,以防止金融機構進行資產重評和信用額度下調甚至取消。
這導致整個社會的資金流向主要是償還債務,而科技研發和營運成本的投入幾乎枯竭,這正是日本錯過互聯網資訊科技紅利、進而「失去30年」的根本原因。
以上是日本發展中的結構性問題,導致其在全球化體系中錯失了長達三十年的發展機會。
然而,僅憑內部問題是不足以導致這一結果的。
也就是說,除了內部因素外,還有包括政治在內的外部因素起作用。

02
上世紀80年代是朗奴·列根主持美國白宮時期,他提出了一種與蘇聯爭奪第三世界國家影響力的列根主義思想,為現代全球化體系奠定了基礎。
列根任滿八年後,由老布殊接替時,兩黨對全球化的看法開始出現分歧。
日本在石油危機和經濟滯脹後采取的供應鏈自給自足政策,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列根時期對日本等海外地區的開放和優惠政策。
但老布殊上台後,由於民主黨在國會和司法上的壓力,不得不改變對外貿易政策。
因此,他與日本等國簽署了廣場協定,目的是緩解美國對海外地區的貿易逆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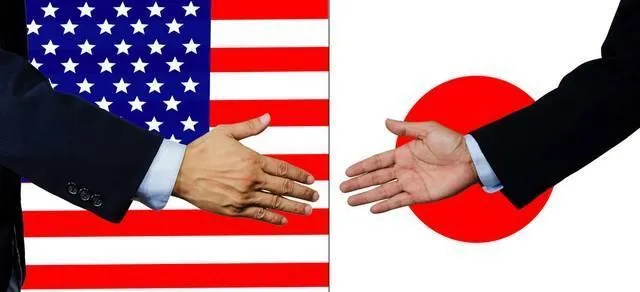
這一政策變動延續至克林頓政府時期,民主黨意識到老布殊執政時的對外硬策略使美國受損,隨後雖對海外政策稍作緩和,但並未改變基本方針和行動路線,仍采取對外壓制措施。
特別是對日本,即使廣場協定的負面影響已實質解除,仍不斷改善對日貿易逆差,采取更為積極的態度,但行動的合理性和對外宣傳口徑上,已將對日貿易逆差的改善從打壓轉為競爭。
那時的美國對日貿易政策,是不是讓你感覺似曾相識?
沒錯,這正是現今美國對中國經貿政策的策略。
總體來看,美國對待日本的政策與現在的做法大致相同,從局部打壓升級至全面競爭,利用多年累積的制度、科研、文化和經濟等方面的優勢,在全球化經濟體系中對潛在競爭者采取預警、及時行動、精確打壓、利益置換和戰略溝通等策略,這是大洋彼岸作為後冷戰時期世界格局領導者的寶貴經驗。

對蘇聯的態度則體現了不同系統間的修昔底德陷阱,這種對抗與對日本或中國的策略截然不同。
而百年前英美的地位互換,則是典型的金德爾伯格陷阱,其中包括歐洲大陸國家的無知傲慢以及英美在文化和社會觀念上的密切聯系,與日美或中美的競爭態勢不同。

03
回顧1992-1999年克林頓執政期間,美國對日本的貿易及經濟策略主要是遏制潛在或現實的最大競爭對手,如高端制造業的半導體產業,美國將有效產能從日本轉移到亞洲四小龍中的南韓和台灣。
對於中低端制造業,美國並未轉移產能,反而對日本開放市場,允許其汽車制造和電子消費產品等行業進入美國市場。
這樣既維持了實質的政治盟友關系,又與之形成重疊型貿易內容,同時在競爭中保持優勢,最終成為贏家。

如今美國對中國采取了類似的競爭性操作手段,這是其在全球化後冷戰時期發展出的寶貴經驗。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民主黨的奧巴馬繼續推動經貿全球化體系利益,但2016年兩黨在全球化體系的利益分配上產生了分歧。
共和黨的當勞·特朗普以代表美國本土白人工薪階級利益為名,推出「特朗普主義」,並於2017年成功當選總統,從而改變了全球化體系的方向,引發逆全球化和地區貿易保護主義的回歸,各主權國家紛紛效仿美國的孤立主義策略。
此後,全球化秩序的發展蒙上了一層陰影。
隨後,特朗普以敵對態度對中國實施一系列政策,包括經貿摩擦、科技圍堵和金融競爭。

直到2021年,民主黨的拜登政府上台,其對華政策從特朗普時期的「敵對」轉向與對日本相似的競爭對手態勢:
保持對華出口商品的高關稅;
推出【通脹削減法案】和【芯片科學法案】,遏制中國的主要資產價格,提高芯片等高科技產品的成本;
對中國的高科技優勢產業實施精確打壓,透過高關稅形成不對稱競爭;
並且在政治和軍事方面加強兩國之間的風險管理,利用其優勢與競爭對手進行不對稱競爭,確保最終勝利。
如果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由民主黨的哈裏斯獲勝,那麽我們與大洋彼岸的綜合較量可能與當年美日之間的競爭類似,最終可能導致東亞國家以「失去了N年」為代價,成為挑戰全球化體系主導者而失敗的一個例子。
這正是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與當今中國的驚人相似之處。

寫在最後
對此,我想說的是:或許大洋彼岸從未衰落過,我們和當年的日本只是作為幸存者偏差的見證者,誤將過往的高速發展視為足以挑戰全球主導者的勇氣。但在接下來的幾年、十幾年乃至幾十年裏,我們可能會一再陷入現代化的發展陷阱,難以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