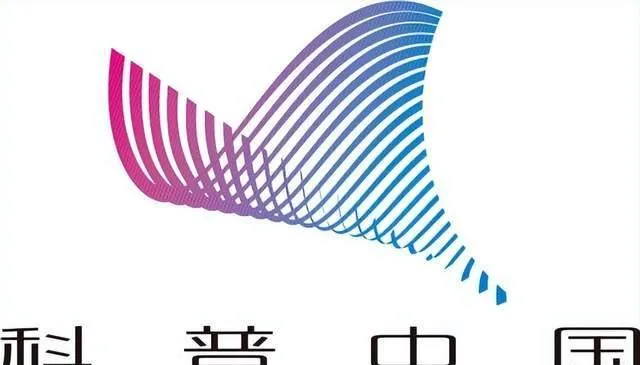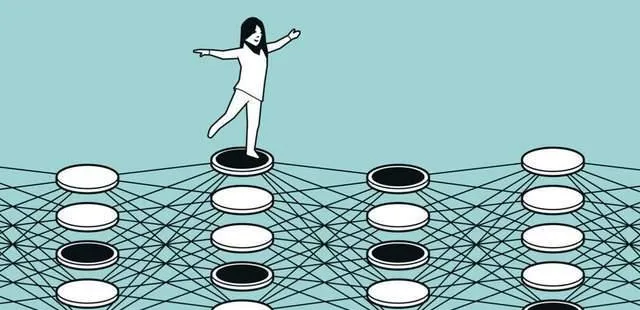
10月8日,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非常出人意料地颁发给美国科学家John J. Hopfield和有「神经网络之父」之称的加拿大科学家 Geoffrey E. Hinton,表彰他们「通过人工神经网络实现机器学习的基础性发现和发明」。奖项公布后,物理学和神经网络的关系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
本文是Hopfield的人生自述,原题为【在科学中成长】,节选自【成为科学家的100个理由】。Hopfield在12岁之前没有学过任何科学过程,但他自幼成长在一个鼓励他自由探索的家庭,中学里遇到了优秀的科学教师,从此自由徜徉在科学之海。
【成为科学家的100个理由】是一本近百位世界著名科学家(其中诺贝尔奖得主30位)畅谈人生的文集。他们讲述自己成长的经历,倾吐对科学、对知识的热爱与追求,也向年轻一代道出了殷切的期盼。从收录的近百篇文章能够领略他们睿智的科学见解,品味他们多角度的人生心得,还可一瞥他们平凡而又充实的生活。
本书现已绝版,【成为科学家的100个理由(20周年纪念版)】近期将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撰文 | John Hopfield
儿童天性好奇。他会戳戳甲虫看它们的反应,扔根树枝在小河中观察它漂多远才沉没;他喜欢拆开玩具看个究竟,也会对水流进排水沟便不见踪影感到惊奇。我生长在一个不但宽容、而且鼓励孩子大胆探索的家庭,所能记得的最早活动是在厨房的地板上玩锅盖,把它们上面没有拧紧的部分全都卸下来。在我心目中,父亲能修好一切东西——屋顶、收音机、水管、电线、自行车,也能给钢琴调音和干园艺活。孩提时代,只要父亲做这些事情,我就会守在旁边看。父亲也会向我讲解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如何才能修好。母亲有一台老式「歌手牌」缝纫机,小抽屉里放了一把调整机器用的螺丝刀。母亲允许我用它,只要摆弄完之后放回去就行了。我用它到处鼓捣,自得其乐。很多年后,母亲给我讲了当时的一件趣事。一位到我家给妹妹看病的医生一进门,就看见我正把一台带手柄的老式留声机拆得七零八落,他立刻出声制止我。听到医生的声音,母亲毫不在意地对他说:「没关系,要是他装不回去的话,他爸爸会帮他的!」一句话,当时我在家里很少受到严格的管束,甚至有些「胆大妄为」。至今我还记得,那真是一把漂亮的螺丝刀!另一件让我着迷的工具是放大镜,我用它观察蚂蚁,或者把阳光聚焦在纸上烧孔。
稍后,母亲开始鼓励我在厨房里做化学实验。我得到了几个试管、软木塞,以及儿童化学实验指南。这些书教孩子们如何用旧电池的锌皮制作氢气,如何让醋和发酵粉在试管中反应而射出软木塞。书中还描述了硫被加热熔化后表现出不同的性质,氢气用火柴点燃时应当发出「嘭」的声音。我制成的晶体总不如书上看到的那么漂亮,但晶体的对称结构还是清楚的。通过动手制作,我还明白了它们的成因。无影墨水是我能在厨房中制造的另一种奇妙东西。与大多数学生初次见到酸性试剂是在化学实验室不同,父亲用红色洋白菜作试剂,向我展示了它如何随着溶液酸度的不同而变红或变蓝。
我的电气设计开始于一对电池、几根导线和几个灯泡,印象最深的是在一把钉子上缠绕电线做成电磁铁,以及自制可在卧室和厨房之间传递信号的简易电报机。
后来,还改造过结构式套装玩具。与发明创造的雄心相比,笨拙的手指时常令我感到力不从心,而且手头可资利用的废旧零部件也太少。有一次,我找到了一副老式的头戴耳机,以及一本美国农业部编制的【简易晶体管收音机制作手册】。根据手册,我用头戴耳机、一块方铅矿石 (硫化铅) 和在纸板筒上绕成的线圈自制了一台收音机。它可以接收远至75公里发射台的信号,而且不需要电池。该手册发表于1930年,用以指导尚未通电地区的农民制作简易收音机,以便在农村收听无线电广播。后来,我得知单真空管收音机可以收到更远距离的信号,于是用零花钱买来真空管,组装了「更高级」的收音机。可以说,我是在亲手制作、改进和维修简易电子装置的过程中,了解电子学和掌握其基本原理的。而且,大多数制作只是修旧利废,花钱其实很少。晶体管收音机最令我着迷的地方是,一些与方铅矿石晶体相连的电线,竟能将无线电信号整流为可听到的声音。这个问题直到12年后我上了大学才真正弄清楚。
一辆自行车也能提供学习的好机会。轮辐断了、脚刹车无法再调整了,没关系,我拆开修理修理。装不回去了,父亲总会救我,他会带我到修车店去。当然,可不是去请人修理——那「太奢侈了」,只是去学点技术和买些必要的零件,回来继续自己修。
我还用一套组合工具自制过模型飞机。先是做橡筋弹射飞机,后来又把微型汽油发动机装上了模型飞机。我从改装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后来甚至在修理我得到的第一辆旧汽车时派上了用场。我喜欢阅读杂志的科学栏目。偶然读到一本关于天文学的书,便梦想着能够作出解释宇宙运行的科学发现。
在中学接受的科学教育非常糟糕,完全是照本宣科,为教而教。我12岁之前没有学过任何科学课程。之后的科学教育,老师们强调的只是记忆现成知识,而不带领我们去实际动手,加深理解。我的这些科目成绩都很差。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两位真正优秀的老师。一位是生物老师,另一位是化学老师。生物老师要求我们注意事实的组织,而不是死记硬背无关联的内容。他鼓励我们寻求生物体之间的联系,教导学生如何观察和思考。应当说,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科学的魅力。高中化学老师则将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学生当作成年人,为我们开设真正的科学讲座,指导我们像搞科研那样做实验。跟着这些老师,我做了许多儿时在书本上读到、并一直期盼着能亲自动手完成的实验。猛然间,我成了班上最好的学生。
物理学是探索未知事物及其成因的学科,它寻求关于世界的基本原理、事实和定量描述。一些人沉醉于探究宇宙起源的奥秘,或者极微观事物的性质。我是在一个对周围世界充满好奇的环境里长大的,所以热切地想理解和影响自然。最有意思的物理学莫过于按人的尺度去关注事物的性质,并在更微观的层面上探索事物的结构与属性。
依据上述背景,我进大学后很自然会主修凝聚态物理。我科学生涯的第一个十年,主要研究结晶固体的光相互作用,及其与固体的电子结构和光的量子特性之间的联系。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许多领域还是完全未开垦的处女地,相关的实验一个接着一个完成,新的理论很快便能得到验证。我由此获得了极好的基础训练,特别是在广泛运用数学模型方面。
随着对固体物理的理解加深,我转向了以物理术语描述生态系统的研究。事实上,当时这又是一个几乎无人涉足的领域。渐渐地,建立于物理学之上的关于生命系统的实验事实多了起来。我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提问方式,为此新兴学科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我本人也以理论生物物理学研究而引人注目。不过,该领域最重要思想之数学意蕴尚有待进一步阐释和挖掘。我所做的只是找出其中相对简单的问题,清楚地加以表达和陈述,并采用便于理解及物理观察的方式来描述可能的解决路径。
我发表的首篇关于大脑工作机制的文章,后来成为引用率极高的论文。通过对相互联结的神经元网络行为作物理类型的抽象,而将磁性和自旋玻璃这一著名物理主题与联想记忆心理现象联系了起来。由此,在神经生物学中引入了计算的概念,并借助于趋向某一不动点的多自由度系统的动态轨迹来进行计算。上述思想如今被称作「霍普菲尔德模型」 (Hopfield model) ,它已激发了许多物理学家进入神经生物学领域。研究者们的工作表明,神经生物学与物理学关系极为密切,相关的物理模型可以有效地迁移至神经生物学的研究。两年间,我在参加了多种神经生物学研讨会后,把握住了关键问题。我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得到最多引用的论文,涉及「动态校对」,后者是在分子水平上一般通用的校对方法。同时我还率先提出了tRNA和蛋白质合成中的动态校对控制机制。在此,我又提出了一个正确的问题。生物学家可能会问:预期的反应是如何发生的?而我则这样问:在预期反应与非预期反应非常相似的情况下,为什么「非预期的」和「不想要的」反应不会发生?由此发现了新的生物物理规则。
我现在的科学兴趣转向了探讨「我们人类如何思考」的问题,这是我常用的提问方式。不过岁月不饶人,我恐怕很难圆满解答以上疑问了。也许有人会说,那是生物学问题还是物理学问题?我想,如此区分其实并无太大意义。就实际研究而言,不妨将物理学定义为「接受物理学训练者的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