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嘉乐(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 【青年记者】2023年第2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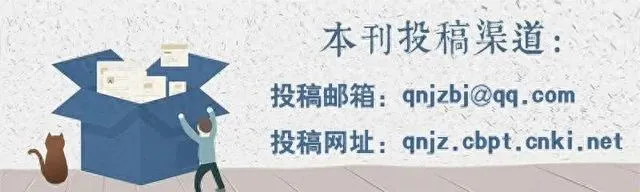
导 读:
当人的生命终结,留存于网络空间的数字遗产沟通着生者与死者、生前社会与身后世界。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而生命已经变得数字化。数字时代人们在虚拟与现实交融的双重世界中书写生存的痕迹,数字化生存的神话似乎正在变成现实,催生着人们对数字化死亡新的思考。早在2012年,成立仅8年的Facebook身故用户就已超过3000万,据此推算,本世纪末Facebook上的生理死亡用户将高达49亿,远超还活着的用户。[1]当人的生命终结,这些以字节形式留存于网络空间的海量数字遗产该何去何从,越来越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当肉身陨灭,物理痕迹随时间烟消云散,但逝者生前在传播与互动中产生的信息被记录并流传。数字时代,大数据技术使数据储存达到新高度,社交媒体记录着全新的在线连接,抽身于数字世界中留存记录的「数字幽灵」还原身前社会的可能性越来越高。虚拟世界已经超越现实世界的镜像与对应物,深度嵌入现实生活。当数字遗产高度复刻逝者的生前世界,生理死亡不再是生命历程的终结,而只是一个节点。「数字永生」的理想激励着学界对数字遗产的广泛关注,相继从数字延续(Digital Endurance Concepts)[2]、数字哀悼(Digital Grief Practices)[3]、身后管理(Death Management)[4]和数字不朽(Digital Immortalisation)[5]角度,探讨生存与死亡视角中的数字遗产及处置理路,丰富了数字时代生存哲学的研究视域。
本文着眼于数字遗产的传播价值,将数字遗产视作一种连接生与死的媒介,通过梳理数字遗产在沟通逝者与生者、生前社会与身后世界中产生的论争焦点,希冀为数字遗产研究提供更多传播学视角。
数字遗产的概念界定
厘清数字遗产的概念内涵与外延,是理解相关争论的关键。档案学侧重数字遗产的文化属性,将数字遗产界定为「以互联网为承载形态的文字作品、资料、图片和影音,形成了一种文化传承的遗产,为后人留下今日世界的数字化记忆」[6],更倾向于Digital Heritage的概念,多指民族特性、习俗、传统方面的遗产。法学则强调财产属性,聚焦数字遗产继承问题。传播学者近年来也愈发注意到数字遗产问题,从媒介属性强调数字遗产的对话性特点,[7]考察作为媒介的数字遗产如何影响社会与文化机制,又如何改变信息、死者与生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与互动。
本文主要观照肉身离世后以数字形态留存于世的在线遗产,对应Digital Inheritance意涵而非Digital Heritage。尽管其中包罗一些文化和知识的表达,但显然上升不到人类的高度。因此,本文择取法学对「数字遗产」的意义划分,对数字遗产概念界定如下:数字遗产指主体死亡后遗留于在线空间或物理存储媒介中,以数字形式存储的信息[8],包括账户密码等访问信息、有形资产、携带用户行为及偏好信息的无形资产以及元数据等[9],具有经济、情感和记忆三重价值属性。
生前世界的数字墓藏:主体性的可朽与不朽
数字遗产建构着逝者身后人格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能否在肉体离场后继续延续,是数字遗产是否可以被继承的争论焦点。
(一)数字遗产具有虚拟性
虚拟空间的开放性伴生着权利界定的模糊难辨,尤其是关于逝者账户信息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划定问题。德国将数字遗产作为普通遗产来管理,在认证财产属性后即可继承。但在波兰,继承者需根据与已故用户在线平台签订的合同区分账户及数据的继承权限。由于数字遗产多为虚拟形态,相应的占有、使用、处分、收益过程具有独立性,其存储、传输、访问等均需经由平台和用户多方。因此在权责判定中主要有三种观点:一者,数字遗产应当归用户所有,平台和服务商只是提供存放与保管的场所,而无权私自处置这些财产,即社交账户所有权应为用户享有;二者,网络运营方拥有数字遗产的所有权,用户仅拥有部分由运营方让渡的使用权,此观点与当下的平台服务协议更为接近;三者,数字遗产并非应然属于运营商或用户,其权责归属取决于权利的正当性。
(二)数字遗产具有期限性
数字遗产的保存高度依赖于存储资源和人类工作负载,将消耗大量的资源。大部分平台运营商仍采取定期清除身故用户数据、限制数据访问时间等手段处理数字遗产。出于降低运营成本和提高营收的考量,平台运营商认为亡故用户数据存储占用过多的数据空间,无限期保有身故用户数据严重损害互联网企业的长期发展目标。同时,不设期限地划定数字遗产处置权利容易招致不可控的隐私问题,故而数字遗产处理多被划归于一定时限内的处理。
(三)数字遗产具有高度人身性
所谓高度人身性,是指数字遗产与被继承人的人格利益有密切联系,具有强烈的个体指向属性。
在「数字遗产第一案」中,约翰·埃尔斯沃思在儿子身亡后向雅虎公司申请儿子在雅虎网站的账号和密码,但被后者以根据服务协议账号不可转让且这一行为会侵犯隐私权为由予以拒绝。最终法官判决雅虎公司将逝者邮件账户内全部内容刻录在CD上交予家属,但保留账号的访问权限。在本案中,支持观点认为本判决符合逝者隐私保护要素及遗属利益,能够弥补继承人与平台之间的能力势差。大卫·文森特则反对称其忽视隐私主体与涉他隐私主体缺席的难度和普罗大众的情形。[10]一方面,逝者是隐私信息的创造者,但遗属并不一定参与其中。在未经逝者生前明确授权同意的情况下,盲目采取继承模式,极有可能对逝者隐私造成二次伤害,也有损遗属的人格尊严。另一方面,网络中的隐私信息既涉及个人性隐私,也有社交中产生的共同隐私,亦即涉他性隐私。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12年柏林女孩地铁案中提出「高度人身性」的概念,要求Facebook授予过世女孩父母访问账户的权利,包括聊天记录和私密信息。法官认为,网络账号也是遗产的一部分,数字遗产不应被区别对待,父母作为监护人有权知晓未成年子女的网络信息。
着眼于数字遗产的经济价值,数字遗产类同于现实世界中逝者生前的财富、自传等作为陪葬品奠于坟冢前,是逝者生前世界的数字墓藏。数字遗产成为一种物质性媒介连通着生与死,是逝者身份的保存物,延续着逝者肉身离世后的数字主体性。对数字遗产的上述特征的不同解读与处置策略,分别是对逝者生理离世后主体性是否仍能以数字形式存续、能够存续多久、其逝后的人格权是否得到承认的回应。
生死之间的媒介通道:主体间性的联结与阻滞
数字遗产是逝者与生者的关系载具,具有情感价值。
(一)跨越生死的情感联结
网民的数字化生存痕迹在网络时代被记录为数据或代码,形塑着网络世界永恒的意志存在,具有物质与情感的双重属性。数字遗产载写着逝者与亲友的生前互动与情感,亲友亡故的沉重损失激发着在世者根植内心深处的与逝者继续保持联系的欲望。从摄影技术到通信技术,人们长久以来一直在努力抓住新技术来实现这种联系。[11]数字遗产取代了传统葬礼成为数字时代新的纪念活动与哀悼仪式,逝者与生者得以跨越生死空间维系情感联结与关系共在。
生者在接受逝者由临终过渡到死亡的转变时需要经历丧葬仪式的过渡过程,在此之后,生者仍需在日常生活中度过哀伤期。一部分人清楚地意识到死亡的现实,将其数字遗产作为自身亡故后与在世者的思想纽带。丧亲者可以访问逝者在Facebook纪念页面等平台的内容,与逝者对话,消除丧亲的痛苦。[12]
(二)关系阻滞的负面效应
在哀悼时查看数字遗物会带来一种「复杂性哀伤」,让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接受「失去这个人」的事实。让留世者陷入高度的悲恸中,打乱原本正常的生活轨道和人际关系。沉溺于数字遗物让他们在现实与虚拟的双重世界里闭门索居,渐渐阻滞关系,摧毁社群。[13]因此,一些人选择「数字火化」(Digital Cremation),删除所有在线生活的数字痕迹,希望在世的爱人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14]一位母亲丧女后渴望孩子的Facebook资料永远消失:「这堵‘哭墙’让我太痛苦了……每每忆及往昔的快乐时光都会加重丧女之痛。」[15]
数字遗产高度分享又高度保密。平台方出于信息保护与防止权威消解的目的建构起数字遗产与生者、生者与逝者之间的权责边界。服务商限制或停止提供存储服务将导致用户数据消失,为生死关系的长久维系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当数字遗产的存贮期限结束,生前世界与身后世界的关系彻底阻滞,主体间性也逐渐消解。
数字遗产建构着逝者在生前世界、身后世界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的流动表现为一种传播关系。而数字遗产作为数字空间连通生与死的灵媒,为哀思者展开记忆的呼唤,传达生者的回想与思念,将逝者的记忆转向人间,搭建起生前与身后世界间的媒介通道,建构着生者与逝者、平台间的主体间性。
超越生死的数字来生:数字永生的技术想象
自秦始皇遍寻丹药始,突破肉身腐朽、延伸生命长度一直是人类不倦追求的目标。基特勒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一书中提示人们,媒介技术将人类的感知作为数据存储到机器中,如同禁锢着等待被唤醒的「幽灵」,重塑着人们的书写与感官体验,不朽便在媒介景观的更迭中流传于世,不断塑造着死亡的新媒介景观。[16]
大卫·伊格曼提出死亡有三种形式:「一是身体停止运转,二是尸体葬入坟墓,三是名字最后一次被人提起。」[17]被遗忘被视作死亡的最后一环,数字媒介和网络技术而「永不安息的逝者」(the restless dead)就是在超越死亡的终结。媒介社会正孕育着永生想象之火种,而依托数据存储、复刻和媒介融合的数字遗产则燃起永生的希望之火,让数字时代的死亡变得鲜活。生者借助数字遗产抵抗对逝者的遗忘,重塑逝者存在的意义,死亡在遗忘与记忆唤醒之间循环往复,成为一个动态过程。[18]数字遗产浪潮也衍生出数字资产管理服务、定制化线上纪念服务和数字遗产存档服务等相关产业,用以解决逝者身后数据的使用控制问题,但数据内容本身并没有发生质变。
当数字技术对认知世界的形塑能力趋于饱和,仿真人体技术再次突破认知壁垒,迈向数字化死亡的新景观。基于人类在网络空间的海量数字痕迹学习,利用人工智能和图像处理技术创造的模拟人体能够以虚拟人形式模仿逝者生前的反应,提供视、听、触等直观而又自然的实时感,让离场的具身在技术时空里继续承担其生命角色。
脱胎于逝者数字痕迹的虚拟化身正面临诸多伦理质询和技术挑战:数字痕迹的保存与再利用方式是否正当合理,尊重已逝者的主观意愿?如何判定这些数字遗产的归属、使用与继承权责的主体?离场具身的数字再生也带来对生者的再创伤,伤痕在不断触及中反复提醒着哀伤的存在。数字永生在赋予此在追忆生命、释放感情时,也一定程度上放大着某种悲情,更加令人难以释怀。[19]生理的死亡和虚拟活跃的社会生存之间的二元论,定义着今天的逝者的地位。对于离世者而言,他们更倾向于拒绝让渡自己的数字痕迹换取数字永生,而不是成为数字幽灵。[20]
结 语
数字空间的死亡经历着「停滞」「消失」和「被遗忘」三个过程。停滞在现实世界体现为生命的逝去,主体性不能再发挥作用(Disabled);在网络世界则体现为数据不再更新,社交平台没有本人的动态。消失包括信息的消失与关系的消失。被遗忘指关于逝者的记忆消失,在线纪念活动就是为了抵抗这一消失。
身体会死,但数据可以永生。在数字化死亡的过程中,数字遗产成为一种技术灵媒,沟通着生者与死者,生前社会与身后世界,对死亡进行重塑与抵抗。数字遗产让我们重新思考身体与灵魂、真实自我与数字自我、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关系,数字永生更是这个时代的新神话,与此同来的却是人文的噩梦。数字媒介推动普通人的死亡向数字化死亡转变,不啻中介化逝者、丧亲者与陌生人之间的互动,数字技术创造出的虚拟个体幻象更让中介化记忆为数字化永生提供土壤。[21]面对这一极具诱惑力的神话,我们既要思考如何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探寻技术具身下人与技术共生的可能;又要抵抗技术的过分蔓延,警惕数字文化的失范以及隐私侵犯和「技术便车」现象[22]。
参考文献:
[1]hman C J, Watson D. Are the dead taking over Facebook? A Big Data approach to the future of death online[J]. Big Data & Society, 2019, 6(1).
[2]Nansen B, Arnold M, Gibbs M, et al. The restless dead in the digital cemetery[J].Digital death: Mortality and beyond in the online age, 2014: 111-124.
[3]Blower J, Sharman R. To grieve or not to grieve (online)? Interactions with deceased Facebook friends[J]. Death studies, 2021, 45(3):167-181.
[4]Volos A. Digitalization of Society and Objects of Hereditary Succession[J]. Legal Issues in the Digital Age, 2022, 3(3): 68-85.
[5]Savin-Baden M, Burden D, Taylor H. The ethics and impact of digital immortality[J]. Knowledge Cultures, 2017, 5(2): 178-196.
[6]章戈浩.传播与媒介研究的死亡盲点:一个生存媒介研究的视角[J].全球传媒学刊,2020,7(2):21-34.
[7]陈刚,李沁柯.穿梭时空的对话:作为媒介「安魂曲」的数字遗产[J].新闻记者,2022(11):31-42.
[8]牛彬彬.数字遗产之继承:概念、比较法及制度建构[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5):76-91.
[9]Haworth S D. Laying Your Online Self to Rest: Evaluating the Uniform Fiduciary Access to Digital Assets Act Note[J]. University of Miami Law Review, 2013,68(2):535-560.
[10]大卫·文森特.隐私简史[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5-6.
[11][13][15]伊莱恩·卡斯凯特.网上遗产:被数字时代重新定义的死亡、记忆与爱[M].张淼,译.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20:3,5;48;44-46.
[12]姜红,胡安琪,方侠旋.生死界面:与逝者的数字「交往」[J].传播与社会学刊,2022(62):69-103.
[14][20]Sisto, D. Online afterlives: Immortality, memory, and grief in digital culture[M].MIT Press, 2020:79.
[16][18]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60,146,11.
[17]大卫·伊格曼.死亡的故事[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111.
[19]刘琴.生死叠合:离场记忆的情感仿真、拟化同在与数字永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09):33-42.
[21]周裕琼,张梦园.未知死,焉知生:过程性视角下的死亡与传播[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45(2):1-10.
[22]理查德·扬克.机器情人:当情感被算法操控[M].上海:文汇出版社,2020:1.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王嘉乐.在网上死亡还是永生?——生死传播之间的数字遗产论争[J].青年记者,2023(22):112-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