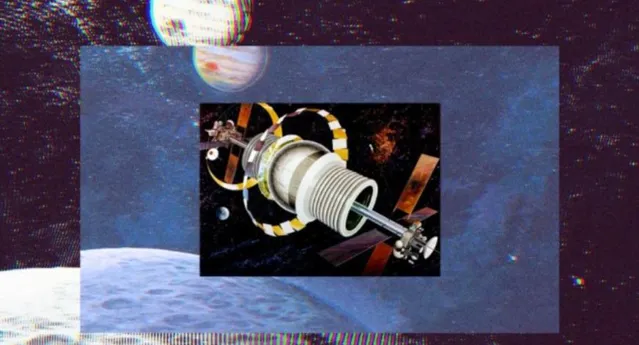
人類發展的唯一障礙是無知,這並非不可逾越。
——勞勃·戈達德
直到1992年, 當第一顆系外行星 被發現時,從來沒有直接證據表明在我們的太陽系之外發現了一顆行星。 在首次發現三十年後, 又發現了數千顆系外行星 。 此外,數以百計的行星位於「宜居帶」內,這表明液態水,也許還有生命存在的地方。 然而,要到達那裏,我們需要一個勇敢的船員離開我們的太陽系,以及一個更勇敢的代際船員,讓他們出生在一個他們無法選擇的任務中。 他們可能永遠不會把我們的太陽系看作是無數其他太陽系中的一個亮點。
讓幾代人在同一艘宇宙飛船上生活和死亡的想法實際上是一個古老的想法,火箭工程師勞勃·戈達德(Robert Goddard)在1918年的文章【最後的遷徙】(The Last Migration)中首次描述了這個想法。 當他開始制造可以進入太空的火箭時,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一種可以繼續前進、前進、更遠並最終到達新恒星的飛船。 最近,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ARPA)和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啟動了一個名為「 100年星際飛船 」的計畫,目標是到2100年促進星際旅行所需的研究和技術。
這種將一個物種從其母星中解放出來的概念對戈達德來說很有吸重力,但自有記載的歷史開始以來,它也一直是海員和觀星者的夢想。 每個盯著夜空的孩子都想象著飛過夜空。 但是,通常,他們也想回到地球。 有一天,我們可能需要在宇宙飛船上建造一座人類驅動的城市,然後踏上前往另一個太陽系的世代航行——永遠不會回來。
距離、能量、粒子攻擊
這樣一項宏偉的任務需要克服許多巨大的挑戰,第一個也許也是最明顯的挑戰是距離。 不包括太陽,已知最接近地球的恒星(比鄰星)距離地球4.24光年,約25萬億英裏。 雖然4.24光年在宇宙尺度上只是一個跳躍,但以我們目前的技術,要達到這個目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於2018年發射的帕克太陽探測器是人類有史以來移動最快的物體,時速為430,000英裏。 但即使以這種速度,也需要6,617年才能到達比鄰星。 或者,換句話說,大約需要 220 代人才能完成這次旅行。
使用目前的技術,大約需要220代人才能到達比鄰星。
減少這個數位的唯一方法是加快行動速度。 這就引出了我們的第二個挑戰:找到推進和維持所需的能量。 為了減少到達新恒星所需的時間(和世代數),我們需要透過燃燒更多的燃料或開發技術比目前更好的新航天器來提高速度。 無論使用何種技術,加速都可能需要來自這些來源的一種或多種來源:預包裝(不可再生)燃料,從星光中收集的能量(在恒星之間更具挑戰性),星際介質中的氫等元素,或透過彈弓從天體上射出。
推力技術的最新進展可能有助於重新關註這個問題。 核融合提供了一個很有前途的解決方案,因為它產生的放射線更少,比其他方法更有效地轉換能量,這將使航天器達到更高的速度。 正如 代達羅斯計劃 (英國星際協會)和 遠射計劃 (美國海軍學院/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所設想的那樣,利用核融合為人類一生中的星際旅行提供了一條途徑。 這些研究表明,核融合動力航天器可以達到每小時6200多萬英裏的速度,有可能將前往附近恒星的旅行時間縮短到45年。
然而,即使我們透過設計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快速、省油的發動機來解決距離和能量的挑戰,我們也面臨著另一個問題:微流星體的威脅始終存在。 想想看,一粒以90%的光速移動的沙子含有足夠的動能,可以變成一枚小型核彈(兩千噸TNT)。 鑒於漂浮在太空中的可變粒徑以及為這項任務提出的極高速度,任何遭遇都可能是災難性的。 這也需要進一步的工程來克服,因為我們現在可用的厚遮蔽不僅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退化,而且可能太重了。 一些解決方案可能是制造更輕的聚合物,可以在飛行中根據需要進行更換和固定; 利用廣泛的遠距離監測,在撞擊前辨識大型物體; 或者從航天器的前部開發某種保護場,能夠偏轉或吸收入射粒子的沖擊。
生理和心理風險
正如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 雙胞胎研究 、SpaceX Inspiration4 任務 以及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其他一年零六個月任務所證明的那樣,一代飛船的船員將面臨另一個關鍵問題:生理和心理壓力。 繞過提高飛船速度或保護飛船不與碎片相撞的技術限制的一種方法是,使用冬眠或滯育來減緩生物學。 然而,在模擬冬眠或臥床休息研究中,暴飲暴食和整天躺著幾乎沒有運動的人患 2 型糖尿病、肥胖癥、心臟病甚至死亡的風險更高。 那麽,熊是怎麽做到的呢?
在冬眠或冬眠期間,熊簡直是非同尋常的。 他們的體溫下降,心率驟降至每分鐘五次,幾個月來,他們基本上不吃東西、不排尿、不排便。 值得註意的是,他們能夠保持骨密度和肌肉品質。 他們的冬眠技巧的一部份似乎來自透過保持穩定的血糖水平來降低他們對胰島素的敏感性。 他們的心臟也變得更有效率。 熊基本上啟用了一種節能的「智慧心臟」模式,僅依靠四個腔室中的兩個來迴圈更濃稠的血液。
2019年,華盛頓州立大學喬安娜·凱利(Joanna Kelley)領導的一項開創性研究 揭示了熊在冬眠期間的顯著基因表現變化 。 研究人員使用與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雙胞胎研究相同的Illumina RNA測序技術來檢查灰熊進入食欲亢進狀態(當熊吃大量食物以將能量儲存為脂肪)時,然後在冬眠期間再次檢查灰熊。 他們發現,在冬眠期間,全身組織都發生了協調的動態基因表現變化。 雖然熊很快就睡著了,但它們的脂肪組織卻一點也不安靜。 這種組織顯示出廣泛的代謝活動跡象,包括冬眠期間1000多個基因的變化。 這些「冬眠基因」是那些寧願在一代船上停滯不前也不願保持清醒的人的主要目標。
我們可以在生成船上利用的另一種生物學機制是滯育,它使生物體能夠延遲自身發育,以便在不利的環境條件(例如,極端溫度、幹旱或食物短缺)中生存。 許多飛蛾物種,包括印度粉蛾,可以根據環境訊號在不同的發育階段開始滯育。 如果沒有食物可吃,就像在貧瘠的沙漠中一樣,等到更好的時機和營養雨落下是有意義的。
滯育實際上並不罕見; 在100多種哺乳動物中觀察到 胚胎滯育。 即使在受精後,一些哺乳動物胚胎也可以決定「等待」。 囊胚(早期胚胎)不會立即植入子宮,而是可以保持休眠狀態,很少或根本沒有發育。 這有點像攀巖者在攀登過程中停下來,例如當暴風雨到來時,然後檢查他們可能采取的所有潛在路線並等待風暴過去。 在滯育中,即使胚胎沒有附著在子宮壁上,胚胎也可以等待糟糕的情況,例如食物短缺。 因此,懷孕的母親可以在不同的妊娠期內保持懷孕狀態,以等待環境條件的改善。 讓人類冬眠或滯育的技術在21世紀並不存在,但有一天可能會。
失重、放射線和任務壓力對太空人的肌肉、關節、骨骼、免疫系統和眼睛的影響不容小覷。 這種任務的生理和心理風險尤其令人擔憂,因為大多數現有模型都是基於相對較短的旅行,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免受地球磁層的放射線,迄今為止最廣泛的研究來自 史考特·凱利上尉的340天旅行 .
人造重力 ——本質上是建造一個旋轉以復制地球重力影響的航天器——將解決其中的許多問題,盡管不是全部。 另一個主要挑戰是放射線。 有許多方法可以嘗試減輕這種風險,無論是在飛船周圍遮蔽、先發制人的藥物(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正在積極 研究 )、頻繁地對遊離 DNA (cfDNA) 進行時間監測以及早檢測可操作的突變,還是對太空人進行細胞和基因工程以更好地保護或應對放射線。 對放射線的最佳防禦,特別是在我們太陽系外的長期任務中,可能是透過這些努力的結合。
但是,即使放射線問題得到解決,也必須解決孤立和有限的社會互動的心理和認知壓力。 試想一下,如果你不得不與你的同事和家人一起工作和生活,一輩子, 在同一棟樓 裏。 雖然我們可以仔細挑選第一代太空人執行長期的飛船任務,但他們的孩子可能難以適應新家的社會和環境方面。
在地球上執行的模擬任務表明,在與一小群船員隔離500天後,大多數關系都變得緊張甚至敵對。
在地球上執行的模擬任務,如 火星-500計畫 ,已經表明,在與一小群人隔離500天後,大多數關系都是緊張的,甚至是對立的。 小說和非小說中都出現了許多關於「太空瘋狂」的描述,但它們的建模和與風險的聯系是有限的。 根本沒有辦法知道同一個船員及其後代在 10 年或 100 年後的表現如何,當然也不會超過數千年。 人類歷史上充斥著紛爭、戰爭、派系和政治背刺的例子,但也充滿了合作、共生和共同治理的例子,以支持大目標(例如 在南極洲的研究站 ) ).
選擇我們的新家
在我們發射第一代飛船之前,我們需要獲得大量關於我們將第一批定居者送往的候選行星的資訊。 一種方法是向潛在的太陽系發送探測器,盡可能多地獲取細節,以確保飛船在發射前擁有所需的東西。 關於這些想法的工作已經開始,就像尤裏·米爾納、史帝芬·霍金和馬克·祖克柏提出的 突破性星際任務 一樣。
這個想法很簡單, 凱文·帕金(Kevin Parkin)在2018年詳細介紹了 物理學。 如果有一支極輕的航天器艦隊,其中包含微型相機、導航裝置、通訊裝置、導航工具(推進器)和電源,它們可以用雷射「發射」到前方以加快速度。 如果每個微型航天器都有一個可以被雷射瞄準的「光帆」,它們都可以加速以減少運輸時間。 這樣的「StarChip」可以在大約25年內前往系外行星Proxima Centauri b(一顆在Proxima Centauri宜居帶內執行的系外行星),並在25年的數據傳輸回地球後發回數據供我們檢視。 然後,如果選擇該位置,我們將獲得更多關於可能等待船員的資訊。 這個計劃的想法歸功於物理學家菲利普·魯賓(Philip Lubin),他在2015年的文章【 星際飛行路線圖】(A Roadmap to Interstellar Flight )中設想了一種可調節的雷射器陣列,可以聚焦在StarChip上,總功率為100吉瓦,將探測器推向我們最近的已知恒星。
理想的情況是播種世界,為人類做準備,類似於在火星上執行的任務。 如果這些StarChips有效,那麽它們可以用來將微生物和傳感器發送到其他行星。 當然,他們也面臨著許多挑戰,需要他們在旅途中幸存下來,減速,然後降落在新星球上——這可不是一件小事。 然而,這個旅行計劃完全在地球上已知的極端微生物的可容忍條件範圍內,這些極端微生物在極端溫度、放射線和壓力下隨便生存。 例如,緩步動物 已經在太空真空中幸存下來 ,也許能夠前往另一個星球,我們也可以將其他「種子」生物送去。 克勞迪烏斯·格羅斯(Claudius Gros)於2016年首次提出的 這種「創世紀探測器」的想法,可以用地球微生物播種其他行星,這顯然違反了所有當前的行星保護準則,但它也可能是為我們的到來準備行星的最佳手段。 理想情況下,只有在機器人探測器對地球進行廣泛分析後,才會這樣做,以減少對可能已經存在的任何生命造成傷害的機會。
一代船的倫理
這些生物、戰術和心理問題是由一個關鍵的,也是對生成船的最後一個限制因素驅動的: 乘客被困在那裏 。 因此,這個問題是必須解決的另一個挑戰:道德因素。 將一整群人放在一艘航天器上,並期望他們在那艘飛船上進一步繁衍後代,這有什麽道德規範? 他們必須知道,他們所居住或出生的船是他們唯一能知道的世界。 某些社會、經濟和文化基礎設施需要與娛樂活動一起建造到一代船上。
緊身衣、虛擬/增強現實相機套裝和沈浸式體驗套裝已經為地球上的娛樂目的而建造,這些對於一代船員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團體可以在虛擬環境中相互比賽,與傳統體育賽事和裝置相比,這需要更少的基礎設施。 畢竟,電子遊戲不僅僅是探索和娛樂活動; 它們是 社會的技術粘合劑 。 當然,遊戲只是拼圖的一部份。 一代船上的生活將從根本上不同,不可否認的是,這比地球上所經歷的任何事情都更具挑戰性。
一些批評將航天器與人類一起發送的批評者認為,如果星際任務不能在太空人的一生中完成,那麽它就不應該開始。 相反,由於推進技術、船舶設計和火箭技術(以及我們的基因組和生物工程方法)都將繼續改進,因此最好等待。 甚至有可能,如果我們在2500年向比鄰星b發送了一艘世代飛船,它將被另一艘在3000年發送的具有更先進推進力的航天器透過。
勞勃·福沃德(Robert Forward)於1996年首次提出這種「不斷過時的假設」,作為一項思想實驗,令人信服。 大多數技術確實趨於變得更好,而且幾乎所有人類社會的技術都在不斷改進。 那麽,如何知道什麽時候是正確的時間呢? 預測未來是出了名的困難。
我們試圖避免的滅絕可能會在500年的滯後中發生,導致所有生命在沒有備份的情況下消失。
然而,一個好的選擇不應該是一個完美的選擇的敵人。 我們可以派出兩艘船——第一艘在 2500 年,第二艘在 3000 年——而不僅僅是一艘。 如果新船趕上舊船,他們很可能能夠互相幫助,並且應該計劃這樣做。 此外,這種過時的擔憂忽略了等待太久才采取行動的關鍵風險。 我們試圖避免的滅絕可能會在500年的滯後中發生,導致所有生命在沒有備份的情況下消失。
但是,即使有先進的娛樂設施,並且隨時都有新的、增強的飛船出現的潛在希望,船員們還會盯著窗外不斷繁星點點的天空,想著藍色的海洋嗎? 或者,他們也許會為成為「被選中的人」而感到高興,擁有探索和建立新世界的非凡機會? 現實情況是,這艘船將是他們的世界,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將是他們唯一能體驗到的世界。
然而,這種經驗的局限性實際上與歷史上所有人類的生活並沒有太大區別。 所有人類都被困在一個世界裏,仰望星空,想著「萬一呢? 這艘船,地球,雖然龐大而多樣,但仍然只是一艘景觀、環境和資源有限的單一船,直到 21 世紀,每個人都在這裏生活和死亡,沒有選擇離開。 幾百名太空人暫時離開了地球,但他們都不得不返回。 這艘飛船只是我們長大的飛船的縮小版,如果做得好,它甚至可能通向一個比我們繼承 的星球更好的 星球。 這顆新行星可以成為擴大宇宙生命的沃土,同時也提供了如何保護地球上生命的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