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伊迪絲·芬奇的記憶】(What Remains of Edith Finch)是獨立遊戲開發商Giant Sparrow於2017年推出的一款步行模擬器遊戲,玩家需要化身為家族僅剩的成員伊迪絲·芬奇(Edith Finch)重新回到廢棄已久的老宅,探尋其他家族成員的死亡真相。雖然每一位死去的家族成員的房間都被封上了,但主角可以透過串聯起空間的密道進入每一個房間,並由死者的物品從伊迪絲的視角切換為房間主人的第一視角來回溯死亡記憶。遊戲流程很短,通關全程只需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但卻獲得了2017年TGA(The Game Awards)最佳劇情遊戲獎項,同時被提名「最具影響力」和「最佳獨立遊戲」,還被【時代】周刊列為「2017年最偉大的十款電子遊戲」之一。不僅如此,在2018年英國電影與電視藝術學會公布的英國學院遊戲獎最佳遊戲角逐中,該遊戲力壓【塞爾達傳說:曠野之息】(The Legend of Zelda:Breath of the Wild)和【超級馬力歐:奧德賽】(Super Mario Odyssey)成為最終贏家。

【伊迪絲·芬奇的記憶】中的家族成員樹狀圖
該遊戲的設計邏輯與一味透過射擊和動作的刺激來激發玩家欲望的傳統遊戲邏輯不同,遊戲目標不是依靠策略或技巧不斷戰勝敵人、獲得勝利,而是將重點放在玩家的體驗、詮釋和閱讀上。對於追求刺激性體驗的玩家來說,這個遊戲必然是無聊的,但對於追求遊戲藝術性的玩家來說,這部遊戲則充滿了探索感、代入感。學術界對於該遊戲的研究興趣則在於遊戲對於死亡的描繪,如從死亡主題、對詛咒的設定、怪誕的氛圍、憂郁的女主人公、家庭的悲慘往事和拼湊式故事講述來看,【伊迪絲·芬奇的記憶】與哥特式小說有著相似之處(Kirkland,2020)。
在此遊戲中,「死亡」確實以其在玩法、主題表達、情感基調和場景等方面的著重設計難以被人忽視,形成了獨特的死亡表達。這也是步行模擬器遊戲設計的核心所在,它關註於用情緒和互動來傳遞特定的感受和經驗。正如遊戲【親愛的艾斯特】(Dear Esther)工作室的創意總監丹·平奇貝克(Dan Pinchbeck)所說,「步行模擬器遊戲缺乏刺激不意味著缺乏經驗」,恰恰相反,「缺乏刺激可以帶來不同型別的反思和情感體驗。」[1]他的話提示我們,既然傳遞情感體驗是步行模擬器遊戲在遊戲設計上的重點所在,那麽二者的關系也應該成為遊戲研究應該思考的問題。然而,目前的研究大都沒有將死亡敘事帶給玩家的獨特情感體驗納入到討論之中,這實際上忽略了電子遊戲中「玩家」這一特別存在,故意淡化了電子遊戲作為體驗的問題,也沒有思考到如何用遊戲這一不同於傳統藝術的媒介方式來傳達「死亡」經驗。結合上文所說的「死亡」在該作中的重要地位,本文對遊戲設計的探討也集中於遊戲關於「死亡」機制的設計上面,並由此思考這種設計激發出了何種情感體驗和對死亡的哲學思考。但是,在論述遊戲獨特的「死亡」機制之前,我們首先要說明電子遊戲中「死亡」的意義,在玩家根本不可能「死」的電子遊戲中,遊戲是否可能將死亡經驗納入到玩家的人生經驗中,電子遊戲從何種角度理解是能夠進行死亡表達的。
一、電子遊戲能否進行「死亡表達」與【伊迪絲·芬奇的記憶】中的「垂死」設計
電子遊戲能否表達「死亡」的問題引起了日本學者的興趣與討論。大塚英誌認為,雖然在遊戲中玩家會死亡,但是能夠重設的死亡實際上限制了遊戲的現實性,它使得死亡在遊戲中變得無足輕重。對此,東浩紀借由討論櫻阪洋的小說【All you need is kill】提出遊戲現實主義觀點來反駁大塚的觀點,他認為小說借鑒電子遊戲具有的「後設敘事性」特點,將玩家在電子遊戲中可逆的死亡的經驗呈現在小說的表現形態中,並由此指出「遊戲現實主義」的課題在於「借由讓角色流血,進而思考應如何讓玩家流血」[2]這個重點上。吉田寬則認為不論是大塚針對「死的描寫」的現實主義,還是東浩紀追問的「死的經驗」的現實性,在關於具體遊戲在對待死亡的不同態度以及處理死亡的不同方式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此基礎上,他提出包括電子遊戲在內的任何媒體都無法真實「再現」死亡,遊戲的現實性僅僅在於它可以透過死亡預兆故事世界的局限及其外部性[3]。換言之,吉田寬將遊戲中的死亡僅僅當作是對「死亡經驗」的一種由外部視角觀察而得的虛擬影像,因此不具有「真實性」。真實的死亡,正如吉田寬所暗示的,是活著的人無法抵達之物,我們能接觸到的只能是現實中死亡展現出的種種感性表現。
大塚和吉田將玩家角色的反復死亡看作是一種演算法主導下的操作,是一個演算法行為,而與現實中的死亡截然不同,在遊戲中我們只能透過角色血條的清零和遊戲重設去理解死亡。確實,目前電子遊戲雖然無法在經驗層面模擬死亡,但是這種「再現」的思維或許本就不應該成為我們思考電子遊戲中「死亡」的出發點,因為遊戲的互動性使玩家處於現實世界與遊戲世界的交匯地帶,也就顛覆了真實與虛構的「二分法」[4]。我們通常所說的電子遊戲中的死亡不具有「真實性」顯然是在「再現實在論」的座標系中去定義電子遊戲的位置[5],忽視了電子遊戲的真實性是不能根據作為再現藝術的電影來定義的。電子遊戲不僅涉及感知問題,還有關行動,也就是說遊戲的「真實感」還來源於能夠產生效果的現實操作以及這種操作創造的獨特體驗。雖然角色的死亡是虛構的,但玩家透過自己的操作與遊戲產生聯系,因而以玩家視點「閱讀」的「讀者」每次獲得的感受都是真實生動的。就【伊迪絲·芬奇的記憶】而言,更是如此。因為這是一款沒有玩法就沒有敘事、沒有體驗的遊戲,玩家只有主動幹預遊戲世界,在觀察的同時操縱角色探索,才能進行遊戲。換言之,對電子遊戲能否表達死亡的思考應該放置在對遊戲經驗進行寫生的「遊戲現實主義」的範圍內進行考量。如此看來,遊戲現實主義開啟了一種新的現實經驗生產的大門:人們以虛擬的方式創造真實的身心經驗。[6]孔德罡就將玩家的具身化體驗納入到對「不死世界」中死亡含義的思考內,認為遊戲敘事中的主角雖然並未體驗到死亡,但操縱主角的玩家在現實維度中不斷體驗到「死亡」所帶來的感受。[7]姜宇輝也將玩家的情感體驗納入到反思遊戲的動人力量的範圍內,並強調否定性體驗是遊戲中最寶貴的情感體驗,正是因為遊戲的情感底色是由死亡引起的苦痛,所以才更可能、更需要在心靈之間營造出情感的共鳴和連線[8]。孔德罡與姜宇輝雖然都考慮到死亡的「真實性」在於其給玩家帶來的具身性體驗,但是二者都將「死亡」帶來的體驗歸結為由於「死亡懲罰」帶來的機會喪失、反復進行遊戲的枯燥重復性等「元情感層次(meta-emotional level)」上的體驗,在這種情況下「死亡」往往與失敗劃上等號。
當我們將更多的遊戲納入到思考範圍內,會發現電子遊戲中的「死亡表達」不只有可重設的死亡這一種,激發的情感也不只有失敗帶來的「元情感層次」的痛苦。例如,近年較為流行的魂類遊戲(Soul-like games)[9]通常將「不死」融入遊戲世界觀之中,有趣的是此類遊戲的劇情流程設計為讓玩家在「不死」的世界中主動「尋死」、結束「永生」。比如【黑暗之魂1】(Dark Souls I)中遊戲的開始即是讓玩家逃離北方不死院;【艾爾登法環】(Elder Ring)則從反面向我們展示了如果一味追求永生和強大會變成什麽樣子,玩家在遊戲中遇到的第一個BOSS「接肢」葛瑞克(Godrick)就是透過將各類物種的肢體截斷再接到自己的身上的行為來獲得力量。在「不死」的世界和「不死」的遊戲中,玩家體會到了「有死」,遊戲為死亡與生存賦予同等的價值,喚起對人的有限性的思考。
此外,有些遊戲透過巧妙的死亡設定讓玩家能夠直觀地意識到死亡帶來的後果,例如在【尼爾:機械紀元】(Nier:Automata)中遊戲設定為人造人是「意識不死」的,即使義體淪陷,但是只要在死亡前將數據上傳到地堡,角色就可裝備上新的義體後復活,但是玩家需要到之前死亡的地方回收舊的義體內的芯片。這部遊戲透過將「屍體」呈現在玩家眼前,讓玩家意識到自己真的已經「死過一次」。育碧(Ubisoft Entertainment)為WiiU(任天堂新推出的HD家用遊戲機)開發的【ZombiU】在死亡機制設計上也有其獨到之處,在玩家操控的角色死亡之後,主視覺繪畫隨機切換到安全屋另一名幸存者身上,如果想要取回之前的裝備,那麽就必須殺死那個已經變成喪屍的「自己」,這能夠讓人感到生存的殘酷與競爭的無情。
還有部份遊戲將角色的死亡作為可選結局之一,讓玩家親手為花費大量時間體驗的遊戲做出自己的選擇。例如,【只狼:影逝二度】(Sekiro:Shadows Die Twice)在遊戲結尾的地方設定了「斷絕不死」的結局,即玩家可以選擇用不死斬自殺或者殺掉平田九郎;在【消逝的光芒1】(Dying Light)中玩家可以選擇犧牲自己拯救全人類或是自己變成夜魔;在【特殊行動:一線生機】(Spec ops:the line)中玩家在意識到一直以來作為化身在遊戲中存在的沃克(Walker)的精神狀態出現問題,自認為充滿英雄主義氣息的拯救行動不過是沃克頭腦中的臆想,玩家在結局可以選擇在認清真相後「自殺」或者否認事實,茍活下去。正是這種面對一切故事卻最終只能選擇一個故事的殘酷,構成了後現代的現實主義表達。死亡結局由於是由玩家親手選擇的,這就使遊戲與現實中玩家對「死亡」的認識搭建了聯系,這一決定性的選擇可被看作對玩家全部遊戲體驗與人生經驗的清算,遊戲在為玩家提供真實的生命經驗。
透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電子遊戲在「死亡表達」上有多種方式,且都可與玩家內心建立聯系、觸動玩家的心靈,讓玩家在遊戲中獲得更深刻的體驗和思考。然而,【伊迪絲·芬奇的記憶】中的「死亡表達」與上述將死亡作為故事背景、巧妙的死亡設計和將角色死亡作為可選結局來凸顯死亡之重量的表達手法不同,它將「死亡」作為遊戲表達的主體去建構,「死亡」既是遊戲主題的一部份,又是玩家需要親身經歷的核心體驗。值得註意的地方在於,該作透過巧妙的轉換,沒有直接讓玩家去經驗「死亡」,而是將體驗核心放置於讓玩家經歷「死亡」(death)之前的「垂死」(dying)階段。換句話說,「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目標,但「垂死」的過程才是遊戲的重點。其實,在很多角色扮演和射擊遊戲中都對垂死階段有特定的畫面設計,例如當血量下降到某個數值時,畫面會變成灰色,與之相伴的是越發明顯的人物的喘息聲。這種設計是為了警告玩家,讓玩家及時幹預、調整狀態,來逆轉「垂死」局勢,從而避免死亡。在遊戲【黎明殺機】(Dead by Daylight)中,當一個幸存者被攻擊三次後,他們會進入「垂死」狀態。在此狀態下,幸存者將無法移動,而且他們需要另一個幸存者來幫助他們起身並治療他們,否則他們將最終死亡。可以想像,玩家在這種情況下會充滿對死亡的畏懼並且處於極度的緊張、焦慮之中。與此類遊戲的設計意圖相反,【伊迪絲·芬奇的記憶】企圖讓玩家經由「垂死」狀態來感知死亡、迎接死亡,而不是將死亡預設為一種需要避免的恐怖事件。此外,這部遊戲雖然允許玩家經歷復數的死亡,但是這些復數的死亡指向的不是同一個人可重設的復活,而是不同的人只有一次的死亡。並且,在具有倫理性質的互動性設計之中,該作限制了玩家改變角色結局的能力,這樣的設計體現出該遊戲不僅在現實層面否定了遊戲中潛在的「不死性」,而且也否定了對「不死性」的向往。豆瓣短評上有這樣一個評論——「多處致敬波赫士,如他所說——死亡是活過的生命,生活是在路上的死亡」[10](白蒺藜 2021-11-27),由此也可看出遊戲的側重點正是在通往死亡的「路上」。
由於每一個活著的人都沒有死亡的經驗,所以我們似乎很難深刻地分享和討論它,而此遊戲正是透過「垂死」讓我們有感知死亡和生命的前提,「垂死」也成為了看見不可見者,言說不可言說者的一種方式。當我們經歷了每一個芬奇家族成員的故事後,我們以為我們能夠在最後迎來詛咒解謎的時刻,可最後卻發現連「我們自己」(即伊迪絲)都難以逃脫詛咒。這樣看來,所謂的詛咒就像是齊澤克(Slavoj Žižek)所說的「麥格芬」(Mac Guffin),它是啟動故事的東西[11],但其自身卻並不存在,或者說不被人所知。遊戲故意不在遊戲終點揭曉真相,而是保持著那不被人類理解的世界、那崇高不可言說的東西。【伊迪絲·芬奇的記憶】的創意總監伊恩·達拉斯(Ian·Dallas)也曾表述對此類似的設計理念:「人類總是不得不面對一個自己無法理解的世界,並接受這個事實。」[12]這種無法理解的世界和不可說之物占據的正是實在界的位置。在齊澤克看來,符號界構成了我們的「現實世界」,而實在界則體現為「現實世界」所包含的裂隙,並且「我們永遠不能獲得一種完全的、無所不包的現實感——現實的一部份總是已經‘喪失現實’,被剝奪了‘真正的現實’所具有的特征,而這種虛幻因素恰恰是創傷性的實在界。」[13]芬奇家族的詛咒對應的正是未知的死亡占據的創傷性的位置,玩家在迷宮中不斷前進的敘事動力就是探尋芬奇家族的詛咒,在這裏可以將這種動力歸結為伊迪絲由於家族創傷造成的「強迫性重復」,這驅動了她在迷宮中絕望的遊走—尋回不可尋回之物,挽回不可挽回之情,反抗不可反抗的壓迫,逃離不可逃離的死亡。[14]或許伊迪絲試圖去理解家族詛咒的努力,不過是逃避原質所造成的可怕沖擊力而已,不過是希望將原質降低到符號層面,透過賦予它意義,將其馴化而已。到此,我們可以說在這部思考死亡與生命的遊戲中,正是透過不表現死亡,不用邏輯描述或用故事本身來傳達而只讓玩家體驗「垂死」的短暫時間,才使其感受到了死亡具有的不可接近的崇高感。如此看來,「垂死」或許比「死亡」給人帶來的震撼和思考更為深遠,而從「垂死」去領悟死、思考生成為了這部遊戲對於吉田寬所暗示的真實死亡是不可抵達之物的另一種表現方式。
二、「垂死」設計的玩法機制:「生成-他者」
當我們開始思考這部遊戲以何種方式讓玩家經驗「垂死」過程時,或許我們首先應該考慮的是遊戲角色與玩家的關系,因為二者的關系決定著玩家以何種方式、何種程度參與到死亡敘事的建構之中並形成關於「死亡」的某種體驗。遊戲中存在兩套互動的表意機制。一是表面的文化層的表意機制,它透過視聽符號形成具象的敘事,玩家以傳統的「閱讀」方式攝取其中的意義。其次是深層的電腦層的表意機制,它是不可見的表意形式,其基本語言是二進制的算學語言,玩家以「玩」(play)為方法理解其中的演算法敘事,並以「操控」的形式參與共時的遊戲書寫。[15]這提示我們不能只從「讀者」的角度去理解其表面的敘事層的內涵,還要從「玩家」的視角關註其演算法敘事呈現出的遊戲性,因此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不是這款遊戲是利用敘事來進行死亡表達的,而是遊戲的敘事是如何與玩法設計配合起來並呈現給玩家動人的感受。這也是這款遊戲解決得很好的問題,它將遊戲性與敘事體驗巧妙地結合起來,該遊戲是真正在用遊戲語言給玩家建立感知過程,在玩家的具身操作與遊戲的表意系統之間建立對應聯系,從而讓玩家獲得某種獨特的心理體驗。
本遊戲的核心玩法是玩家透過與周圍環境互動而拼湊出芬奇家族的故事,並在伊迪絲和其他家族成員的身份轉換中了解伊迪絲對家族的看法和家族成員們的故事。不僅如此,各故事的遊戲玩法則取決於故事情節和人物性格特點,遊戲設計了不同的互動操作,並透過遊戲的敘事框架串聯起來。【伊迪絲·芬奇的記憶】的獨特之處也正在於此,即遊戲並不是以單一的第一人稱視角(伊迪絲的視角)貫穿始終,而是賦予玩家代入每一位死去的芬奇家族成員,以第一人稱視角體驗他們死前精神與心理狀態的權力。瑞安(Marie-Laure Ryan)在【故事的變身】(Avatars of Story)中按照玩家與虛擬世界的關系以及使用者是否能夠影響遊戲行程將互動敘事分別分為「內在/外在」互動性和「探索/本體」互動性。照此分類方法,【伊迪絲·芬奇的記憶】當屬於內在-探索型,而內在-探索型參與尤其適合「穿過門戶發現新世界」的故事[16]。這種型別的互動敘事往往涉及視角切換連結,這種雙向連結允許玩家進入主敘事行程中不同角色的私人世界之中。
視角的切換對應的正是德勒茲提出的「生成」(devenirs)概念,在「生成」之中,我們的身體不再封閉,而是向外部敞開,向不同於自身的世界敞開。某物之所是,取決於它所遭遇的生命[17],我們在遊戲中作為旁觀者的世界變成了自己親歷的世界,所以透過將遭遇最大化我們的生命得以增強。房間中與死去的角色息息相關的日記本、漫畫書、照相機、詩歌、信件等像是一個個時光隧道,它允許玩家瞬間穿越到另一個時間點和另一個故事中。莫莉(Molly)是玩家在遊戲中遇到的第一個死去的家族成員,在她的故事中,玩家能體驗到「生成-動物(becoming-animal)」,生成-動物是指非人類視角的生成,在遊戲中呈現為玩家得以以貓、鷹、鯊魚、蛇怪的視角看待世界,並使自己的身體進入到與另外的事物的復合關系之中。「生成-動物」是一種可能的感知方式而不是感知的源頭,它引領主客體穿越了限制性的人/動物間的二元差異,無論是人類還是動物,均在生成的過程中喪失了經驗意義上的主客體之別,透過接近非人的動物、植物或機器的視角,進一步「生成-不可感知之物」(becoming imperceptible)[18],這肯定了人類的局限並得以超越自身或擴充套件到自身的最高能力,拓展並改變了人類的感知方式與對世界的理解。
「生成」不同於「奪舍」,「奪舍」被定義為「元神」主動或被動地離開身體去奪取他人的身體繼續修煉[19]。也就是說,被奪舍的人一般只是作為奪舍之人的載體、皮囊或工具,失去了自身的個異性。相反,「生成」不是一種同一化,而是在完全差異的個體之間所形成的速度和情動的某種復合,是共生。[20]當我們把遊戲中不經常思考的人物語音置入我們思考的範圍內,就會發現在這部遊戲中旁白語音對於玩家相對於角色的位置關系起到了很大的定位作用。由於語音具有的「人性化」維度,它使得我們漸漸走入聲音的幻境之中,在角色的聲音中或是被邀請成為角色,或是在文字與操作中理解人物內心的想法,漸漸將我們的心靈貼近角色。例如,在莫莉的故事中,玩家對遊戲要求的「捕獵」行為與故事設定中莫莉的饑餓緊密結合在一起,同時透過語音再次強化了二者的聯系,「但我一心想要吃了那只鳥媽媽」、「現在,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餓」等句子都在將莫莉的心情傳遞給玩家。在莫莉的弟弟卡爾文(Calvin)的故事中,遊戲進行到某個地方時卡爾文的弟弟山姆(Sam)的聲音消失後並未給玩家做出任何提示,許多人都會停下秋千,試圖回家吃飯,卻發現此種操作是不可能的。於是我們只得不斷蕩秋千,心中充滿著猶豫,而此時旁白會依據你動作的振幅進行更深入的描述:當你的振幅越來越小,旁白聲會漸漸停止;只有當玩家不斷向更高處蕩秋千時,山姆的聲音才會繼續出現。於是,在山姆對哥哥的回憶聲音中,隨著我們越來越了解卡爾文的個性,我們似乎明白了他的想法——他想要越飛越高,而我們在這個過程中似乎也用我們的現象身體獲得了一種騰飛的快感,最終我們把自己拋向天空。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巧妙的轉化,即是我們把遊戲的要求等同於卡爾文的內心需求,因此玩家的被動自行化解了一部份,而沈浸於自己與角色的共情之中。也就是說,我們從未失去自我,角色亦從未成為被我們奪舍的空殼。我們看到的世界不再是玩家眼中的世界,也不是伊迪絲眼中的世界,也不完全是角色眼中的世界,而是一個異質性、差異性的玩家與角色共生的混合世界。遊戲之所以以「生成-他者」的方式讓玩家體驗角色們幻象般的世界,也是因為遊戲裏的死亡體驗具有主體性的特征,只有我們走進角色,才能理解他者走向死亡的原因,從而拓展或改變我們對死亡的認知。「生成-他者」的真實性正在於與他者遭遇之後,那些驟然攫住我們、令我們受其影響並行生改變的情狀之中。作為生命存在的最後展示和亮相,垂死體驗也必然是帶有強烈情感色彩的心理活動。正是由於「生成-他者」,玩家才能充分地體驗角色的心理,了解角色的行為動機與精神狀態之後才能由「生」去嘗試理解「死」。
需要註意的是,並非所有包含視角轉換的遊戲都是「生成」,比如在【戰地風雲5】(Battlefield V)的劇情模式中,玩家在四個篇章中會分別扮演四個角色去體驗戰爭,也會經歷自己和戰友的死亡。但此類射擊遊戲仍是以遊戲機制為主導,僅僅將影像作為敘事的重要手段嵌入其中,遊戲的核心體驗與影像和敘事無關。也就是說,敘事只是作為瑞安所說的「情感釣鉤」,以增添玩家的使命感,推進任務的執行。在射擊敵人的時候,玩家並不會或者說很少會將自己深切地代入進某個角色。角色只是玩家的化身,二者之間並沒有共享情感和經驗,角色更沒有形成玩家在遊戲世界中的數位肉身。佐爾法伊格或者比利·布裏傑(二人都是玩家在遊戲中的化身)只是被玩家暫時「奪舍」,作為玩家享受戰爭的緊張與刺激的工具,大部份遊戲時間內玩家思慮的一直都是如何通關或避免重玩,戰場的背景設定已經失去其最初的意義。在這一意義上,遊戲在武器裝備、戰役歷史、聲效、場景等方面確實是以現實為模擬物件的,但是從遊戲現實主義的角度上來說,它在體驗上卻不夠真實。在【尼爾:機械紀元】中玩家也可以在遊戲的三個周目中分別操縱2B、9S和A2,但是在這款遊戲中,不論是視角變化還是人物對話,遊戲始終持有一種拒絕承認玩家在場的傾向。從很多玩家都會親切地將2B稱為 「2B小姐姐」也可以看出,角色與玩家處在兩個次元,玩家並不能與角色保持緊密的認同感。
由於無法親歷自身的死亡,他者的死亡只能成為我們可經歷的直觀事件。而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認為「人所能感知的他人的死並非本真意義上的感知,他人的死亡過程是無法被觸及到的,也就是死亡具有不可替代性。」[21]面對他人的死亡,我們本能地將死亡推卸到他人身上,認為死亡暫且「與我無關」——這當然不是在否定「我們終有一死」的生物事實,而是指我們認為死是未至的未來,沒能認清死亡本就蘊於人的存在之中。但是,在【伊迪絲·芬奇的記憶】中,他者的死亡並不是玩家冷眼旁觀的畫面,而成為了玩家的主要遊戲體驗;玩家不是旁觀者,而是不斷生成為每一個家族成員,體驗到另一個人或力量正在篡奪自己的位置。如此,遊戲解決了旁人的死亡對自己而言總是陌生的這一難題,玩家也不再將自己局限於一個組織判斷的位置,而是與遊戲過程中遭遇到的並構成玩家自身的力量一起變成他者,從而將自身從有限的主體形象中解放出來。正是透過生成運動,遊戲才得以在玩家身體內激發出一種全新的人類感覺,凝聚成「解轄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得以實作的現實力量[22],即在與其他多元體建立連線之時改變著自身的本質。分析至此,我們能夠看出遊戲的潛力,當一個宏大的、用語言難以描述的主題無法透過晦澀難明的語言清晰傳達出,那麽遊戲可以打造一種更直觀的方式讓玩家體驗,在這部遊戲中這種直觀的體驗方式便是透過生成的方式支撐起來的。
三、「垂死」設計的情感體驗:「不要向欲望讓步」的死亡驅力
玩家與化身的關系在不同遊戲當中有著不同設定,由此促生的情緒也不同。[23]玩家以「生成」的方式體驗到的面臨死亡的感受與整座老宅陰郁詭異的氛圍格格不入,互動操作喚起的特定情緒氛圍不是恐懼,而是一種快樂與釋然。在2018年的GDC(Game Developers Conference)會議上,伊恩·達拉斯就曾提到過:「在大多數遊戲要求玩家阻止死亡的背景下,要如何創造一個使死亡不可避免並且讓人不覺得那是失敗的跡象的遊戲呢?我們試圖使那些死亡瞬間讓人感覺更加的積極。」為達到這種目的,該遊戲選擇用情緒傳遞觀念,而非用邏輯描述或者用故事本身來傳達。選擇用語言講述死亡哲學是可被理性理解的描述方式,而情緒——作為經常被現代人壓抑的存在,它比理性更直觀,可以繞過思維的運作使玩家直接感受到遊戲的內核。具體來說,這部遊戲主要透過視覺、聲音、劇情、角色等元素來營造和傳達情感體驗,對於玩家來說,遊戲的過程實際上是體驗一系列情感的過程。例如,遊戲憑借絢麗的色彩和輕快的音樂渲染出一種積極明亮的氣氛,大大削弱了死亡在大多數人印象中的恐怖效果。
遊戲中的情緒渲染也不僅限於上述方式,還更多依賴於遊戲提供給玩家可實施的操作。因為遊戲往往將情感觸發因素隱藏在機制和系統當中,所以當玩家觸發機制、與遊戲系統互動之時,這些潛在因素將會被釋放出來。在【伊迪絲·芬奇的記憶】中,重復操作就是隱含著特定情感因素的重要機制之一,它是指玩家透過做出不斷重復的操作痕跡來增加敘事和操作之間的同步性。具體地說,遊戲透過用玩家操作控制器的身體行為模擬角色的行為,讓玩家能夠專註於操作與反饋之間的迴圈以及這種迴圈帶給自身的細微感受,並與角色產生深刻的情感連線,以達成更深層的敘事沈浸。在角色做出重復的行為的時候,玩家同樣需要用重復的模擬行為呼應,這樣就可以更直接地感受到角色做出重復行為時的壓抑與麻木,玩家由此生發的內心感受會比制作者使用旁白或動畫來描述角色的狀態更加細膩且深刻。例如,卡爾文不斷向更高處蕩秋千、華特(Walter)的開罐頭動作、路易士(Lewis)切魚頭。然而,在遊戲中,行為越是重復,越在玩家與角色間建立同步關系,就越會激發出蘊含在玩家體內的一股力量,這力量推動著玩家去打破重復。在此刻,玩家想要結束重復、推動遊戲行程的想法與角色渴望擺脫桎梏的想法不謀而合,玩家也最終能夠對角色主動朝向死亡這一常常被認為是「非理性」的行為達成了共情與理解。
玩家感受到的不可見的身體沖動是什麽呢?姜宇輝認為電子遊戲與電影的相通之處正在於令「不可見」的無意識結構變得「可見」[24],也就是說遊戲也具有使我們看見不可能看見之物,描繪出創傷性的感覺世界的力量。筆者結合自己的遊戲體驗,認為遊戲對重復操作的設計在玩家體內激發出的「不可見」的身體沖動對應的是「死亡驅力」(death drive)。首先,驅力(drive)是與欲望(desire)相對的一個概念,欲望是經過理智批準同意的,它總是朝向某個目標並以達成該目標為目的,但是即便獲得想要之物也只會感到「不滿足」,所以不如說欲望的目標就是「不滿足」,它具有轉喻的性質,不斷奔赴下一個目標;驅力並不固著於某一個特定目標,而總是圍繞著不可能的原樂重復著自身,並以迴圈的過程為樂,齊澤克把驅力的固有特質闡述為「追尋客體的反復失敗中得到滿足的迴圈運動」[25]。例如,卡爾文的夢想是當飛行家,我們聽到山姆說「一旦他(卡爾文)下定決心,就絕不動搖」,卡爾文也確實如此,向更高的地方蕩去,毫不妥協,並且他的目的也不在於最終能獲得什麽,只是享受這個越蕩越高的過程,同時這種激進的倫理態度也導致了他的死亡。驅力圍繞間空的迴圈運動可能會產生其極端表現,即非理性的暴力,人把自己的生命暴露在這種暴力中從而也為自己招致死亡,因此拉康(Jacques Lacan)會說,所有驅力根本上都是「死亡驅力」[26]。佛洛伊德對這種非理性的暴力感到震撼和驚奇,把這一暴力命名為「死亡本能」。[27]他假設在人類心理結構中,不僅有遵循自我保存原則的快樂原則,還有一種更為基本的原則——死本能,且他假設快樂原則實際上是服務於死本能的。而這種功能與一切生物最普遍的努力有關——回到無生物世界的平靜狀態中去。[28]拉康後期發展了佛洛伊德的這一概念,而齊澤克則大大推進了對「死亡驅力」的闡釋,他力主拉康晚期稱道的實在界驅力,而反對想像-符號秩序中基於律法或超我而生產的驅力。齊澤克認為,死亡驅力對應的是超越快樂原則,是無視快樂原則的限制,無視生命可以維系的限度,但卻不是一種自我了斷的沖動,而是物件征秩序的僭越。在華特的故事中,華特曾目睹姐姐芭芭拉(Barbara)的死亡,他也因此遭受了巨大的心理創傷,之後他便被媽媽關在了地下室。在他的世界中,殺掉姐姐的怪物可能隨時出現在外面的世界中。但是,在三十年後,華特選擇結束這樣的生活,離開地下室,即便是死亡也不能阻擋他離開地下室的決心。一般人在面對危險處境時,基本都會選擇退縮來保全生命,因為這是生命本能,是求生欲望、快樂原則的要求。但人同時也受死亡驅力的束縛,正是在死亡驅力的推動下華特能夠沖破生命本能,追尋象征性的死亡,否定大他者所界定的「世界」,無視大他者為他賦予的限制。玩家則在文字的指導下操作著鍵盤和滑鼠「生成」為華特,玩家自身的意誌也受到華特的影響,朝著另一個世界走去,並從中感受到了死亡驅力的存在。
路易士的故事作為整部遊戲中最為精彩、遊戲設計最為精妙的一部份,賦予了死亡驅力以政治性的維度。這個故事是基於鄧薩尼勛爵(Lord Dunsany)所著的【奇跡之書】(The Book of Wonder)改編的,它講述了一個售貨員的故事。這個售貨員逐漸將他的精神從枯燥無味的日常生活中分離,在他自己幻想的奇幻世界裏遨遊。起初他能夠這樣做,同時也從事他日常生活的工作,但他最終被制度化了:
同事們註意到了夏普先生的安靜,發覺他有時甚至有些心不在焉;可他招待顧客的行為卻挑不出錯兒來,他對待顧客依舊和往常一樣巧舌如簧。他如此幻想了整整一年,想象力變得越來越強大。盡管還是在火車上閱讀半便士一份的報紙,還是和人聊著當天的熱門新聞,還是給選舉投票,卻只有半個夏普在做這些事,他的靈魂已不在乎這些了。[29]
有趣的是,隨著遊戲的開發逐步推進,路易士的故事開始與其原型漸行漸遠,甚至可以說路易士自己走向了他的死亡。路易士的絕望之情是透過充滿「現實感」的遊戲玩法傳遞表達的。遊戲將玩家玩遊戲的註意力分成了兩個部份,一個是路易士在罐頭廠砍魚頭的現實世界,呈現在界面的右側;還有一個是他的想象世界,呈現在界面的左側。玩家在對鮪魚進行「點選-向上拖」的重復性操作中漸漸可以專註於左側路易士的幻想世界了,由此玩家玩遊戲的體驗與路易士在罐頭廠工作的體驗驚人地重合了,重復的手法一次又一次地將玩家推至情緒的頂點,遊戲機制精準地捕獲了身體與思維、幻想與現實之間的分裂。在故事接近結尾處,當路易士完全沈浸在其幻想世界中,界面中的幻想世界也侵吞了現實世界的殘留畫面。我們化為偉大光輝的路易士去行加冕禮了,直到畫面一黑我們才突然醒悟現實中的路易士原來自己走向了斷頭台。路易士沈浸在與現實世界完全脫節的幻想世界中實際上是一種自我回撤行為,透過這種方式完全結束社會,他主動將自己變為象征秩序所排斥的物件,不接受精神醫生的診斷和規勸,完全放棄了現實中的生活,並由此獲得深深的解脫感。成為了齊澤克所說的「活死人(living dead)」。路易士的行為就是那些激進地越出每日常規之外的行為,這些行為實際上均是根本性地指向「死亡」[30],而這種「死亡」指的並不是生物學意義上的肉體死亡,而是象征性的自殺,是主動將自己斷絕於象征秩序之外,只不過路易士完全斷絕象征存在的激進行為不可避免地走向肉體死亡而已。路易士對幻想世界自我的認同是一種超越欲望、超越死亡的驅力要求,這種要求讓象征界暴露出自身的漏洞和蒼白,路易士的死亡成為了對資本主義機械化生產造成的勞動物化與異化的批判和反抗,同時整個故事也可以被看作是一個關於美國社會經濟下行、信仰破碎的政治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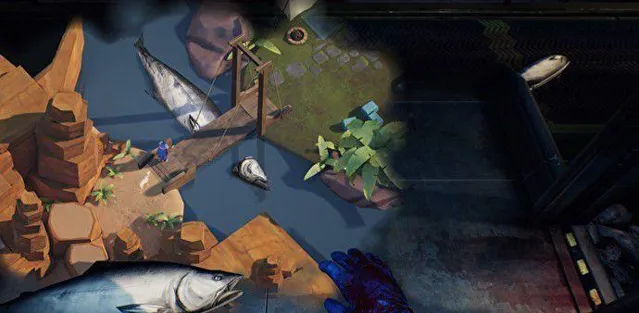
路易士在現實中切魚頭的同時在幻想中冒險的畫面設計
在電影、文學作品中我們都看到過死亡驅力的身影,而為了更深入地認識電子遊戲在表現死亡驅力方面的特別之處,本文嘗試將電影藝術與遊戲進行對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的電影【兩生花】(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與【伊迪絲·芬奇的記憶】中芭芭拉的故事在主題上有相同之處,但在表現方式上有所不同。電影講述了兩個少女,一個生在波蘭,一個生在法國,同樣的相貌,同樣的年齡,她們也有一樣的名字:維羅尼卡。她們最大的不同就是,法國的維羅妮卡在面臨危險時總能憑直覺避開危險,做出理性的選擇而波蘭的維羅妮卡恰恰相反,總是不受理性限制做出危險的選擇。波蘭的維羅妮卡在公演當天沈浸在自己最鐘愛的歌曲中,頂著心臟病發作的疼痛,把高音頂到巔峰,在演唱副歌最為輝煌高光的時刻倏然倒地身亡。波蘭的維羅妮卡的行為與上文所說的卡爾文蕩著秋千向天空飛去的行為是多麽相像,二者都沒有做出倫理背叛的選擇,執著地追求驅力的滿足,而驅力的滿足正對應著拉康所講的「不要向欲望讓步」的絕不妥協的、抵抗的、激進的、最基本的倫理態度[31],但是二者在死亡驅力的呈現方式上有所不同。
觀眾在看到波蘭的維羅妮卡的突然死亡之後,往往會感到驚詫、驚奇,好奇她為什麽不惜失去生命也要如此唱歌。這也是電影設定了兩個維羅妮卡進行對比的原因所在,因為只有在與一種理性的、秩序化的現實生命的對照中,才能凸顯出朝向日常生活之外的神秘驅力,這時的死亡驅力是玩家需要使用理性才能領悟的存在。這也從側面說明了在影視藝術中,觀眾只是透過螢幕上的影像認同情感並嘗試理解故事想要傳達的內容,缺少采取行動直接在體內生發出的身體沖動。吳冠軍以【鐵達尼號】、【誕生】等電影為例說明由愛驅使的死亡驅力——因愛而走向死亡的行為——才是真正的生命性行動,並提出電影藝術透過將人們帶到一個徹底越出日常生活之外的幽靈性場域中,賦予人以此種「反事實」性的高強度生命性體驗[32]。他雖然認為愛與死具有「同質性」,二者作為狀態都是現實世界的「例外」,但只能透過死亡來論述愛的強度,並將死亡驅力定位於人死後沖出身體、持存不息的愛的最激烈狀態。這也從側面反映出電影藝術與文學等媒介難以直接將內在性沖動表達出來,而必須以「愛」為名賦予角色主動死亡的理由,只有這樣死亡才能讓觀眾或讀者理解,才能認可死亡的價值。
從電影到遊戲,從第三人稱視角到第一人稱視角的轉變,兩者的核心區別是電影總是包含某種特定的道德傾向,觀眾總是傾向於在一個特定的象征秩序中去理解,而後者善於提供沈浸感與在場感,充分利用其相較於影視文學等傳統藝術所不具有的互動性將不再被符號化的事件或感受以特定的行為反饋模式而非單純的視聽覺表達傳遞給玩家,從而提供給玩家從角色的視角理解他們世界的可能性,這樣玩家更有可能經由「身體的直接現實」去理解角色面對的世界。現實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完全憑一種沖動去「赴死」的行為不被允許存在或是被貼上「精神失常」等標簽,但也正因如此,從拉康的精神分析出發,遊戲比現實更真實,它揭示出了主體的分裂以及內部「非理性」的一面,死亡驅力也是倫理行為的基本模式。對死亡驅力的頓悟也是「生成」的真正力量之所在,遊戲讓玩家感知到在角色經歷中所表達的潛在力量而受到刺激,領悟到在「垂死」之際方可最激烈地活,在虛構作品的偽裝中,我們才能體會到主體性體驗的真實。
結語
本文首先說明應將玩家視點引入對電子遊戲中的死亡表達的思考,雖然界面上的角色死亡是虛構的,但是玩家每次與「死亡」的遭遇和體驗都是真實的,虛擬世界的經驗可以成為真實生活經驗的一個部份,因此我們對電子遊戲中「死亡」的「真實性」的把握應放置在「遊戲現實主義」的範圍內進行考量。【伊迪絲·芬奇的記憶】作為一部步行模擬器遊戲,從預設情緒出發,透過引導性的空間形態設計讓玩家自行探索,憑借獨特的操作互動來加深玩家與扮演的角色之間的聯系,從而實作了強大的敘事能力和情感負載功能。該遊戲創造性地采用「垂死」設計將體驗重點放置於角色死亡前的那一段記憶,構成了遊戲特有的死亡敘事,這種設計企圖讓玩家透過「生」來領悟「死」,給玩家的心靈帶來極大震撼,拓展了關於人類生命本質這一古老命題的表達方式。接下來,本文指出「生成」的玩法機制使玩家進入到與眾角色的復合、伴侶關係之中,從旁觀他人之死的非本真死亡領會變為親歷自己之死的深切死亡感悟,讓玩家有機會遭遇那些超越我們認知的非人的、斷裂的力量,激發了玩家能動的思考。更進一步,本文認為玩家在荒誕、奇幻的體驗和重復的操作中感受到的心理真實,指向了在現實中被壓抑的死亡驅力。死亡驅力開啟了人類生存情況的另一個面向:超越日常現實生活和理性秩序的趨向於混亂、非理性、非規訓一面的真實境遇。這種情感體驗不可被現實主義編碼,它是每個玩家在遊戲中用身體感受到的心理真實,這正是不同於作為「反映」的經典現實主義和作為「反應」的動漫現實主義的遊戲現實主義的表達方式。正如周誌強所說,「我」的遭遇才是每個人生存的真實,而不是對這遭遇的過剩性解釋(象征界真實)或純粹理念化(想象界真實)。[33]遊戲的「真實性」正在於此,它將無法用語言表現出的東西,用互動的方式銘刻在玩家的體驗中,並最終以一種實在界的身體沖動彰顯出來。不論是未說的「死亡」還是「生成」的體驗都使我們能夠從現存或實存的世界出發去思考一個潛在世界或尚未給出的未來,爆發出電子遊戲的潛在能量。更難能可貴的是,遊戲創造了一個足以承載起眾多思考的世界,令諸多關乎人生處境的問題都有跡可循,不至虛浮。
註釋:
[1] Hatling I N. Constructing Libraries of Life and Death: Textual Artefacts, Visuality and Space as Narrative Devices in Giant Sparrow's What Remains of Edith Finch and Alison Bechdel's Fun Home[D]. NTNU, 2020.
[2] 東浩紀.遊戲性寫實主義的誕生:動物化的後現代2.黃錦容譯.唐山出版社,2007年,第179頁
[3] 探尋遊戲王國裏的寶藏——日本遊戲批評文選.鄧劍編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20年,第270頁
[4] 傅越.2.5次元的生存與死亡——探索「遊戲現實主義」的臨界性[J].上海文化,2023(10):97-106+118.
[5] 李洋.作為工具性體驗的電子遊戲——及其與電影的關系[J].文化藝術研究,2023(04):36-43+113.
[6] 周誌強.遊戲現實主義:「第三時間」與多異性時刻[J].南京社會科學,2023(03):95-105.
[7] 孔德罡.「非死」作為唯一確定性:電子遊戲中的死亡現象學和後人類敘事[J].藝術學研究,2023(03):89-96.
[8] 姜宇輝.火、危險、交感:電子遊戲中的情感[J].文化藝術研究,2021,14(02):15-26+111.
[9] 魂類遊戲指的是一些具有高故事性、高關卡難度、高遊戲體驗和具有高美學設計的頂級動作遊戲。例如:【只狼:影逝二度】、【黑暗之魂1】、【黑暗之魂2】、【黑暗之魂3】、【血源:詛咒】。
[10] https://www.douban.com/game/26411799/
[11] 齊澤克.意識形態崇高客體.季廣茂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1月,第223頁
[12] 參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64y1v7GY?t=2766.8,該視訊是【伊迪絲·芬奇的記憶】的主設計師Ian Dallas在GDC的演講。
[13] Slavoj ,the Fright of Real Tears:Krzystof Kieslowski between theory and Post theory,London:British Film Institute,2001,p.66.轉引自吳天天.「後結構主義之後」的崇高美學——論齊澤克對崇高美學的重構[J].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2023,26(01):153-167+442.
[14] 王洪喆.迷宮如何講故事:「巨洞探險」與電子遊戲的跨媒介起源[J].讀書,2022(03):3-13.
[15] 鄧劍.國風遊戲批判——從在場性的誕生到整體性的坍塌[J].中國青年研究,2021(10):14-21
[16] 瑪麗-勞爾·瑞安.故事的變身.張新軍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125頁
[17] 克雷爾·科勒布魯克.導讀德勒茲.廖鴻飛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4年7月,第162頁
[18] 吉爾·德勒茲.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2,姜宇輝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387頁
[19] 倪湛舸.傳統文化、數位時代與「分體」崛起:初探網路玄幻小說的主體構建[J].現代中文學刊,2023(01):14-23.
[20] 吉爾·德勒茲.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2,姜宇輝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36頁
[21] 關書薇. 存在主義文學中的死亡美學[D].雲南大學,2022.
[22] 張晨. 身體·空間·時間[D].中央美術學院,2016.
[23] 戴安娜·卡爾、大衛·白金漢等著.電腦遊戲:文本、敘事與遊戲.叢治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95頁
[24] 姜宇輝.從夢機器到暗主體:電影與電子遊戲之間的否定性之思[J].文化藝術研究,2023(04):1-12+112.
[25] 斯拉沃熱·齊澤克.享受你的癥狀.尉光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11月,第75頁
[26] Dylan Lacan,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London:Routledge,1996,p.103,p.33.轉引自 吳冠軍.作為死亡驅力的愛——精神分析與電影藝術之親緣性[J].文藝研究,2017(05):97-108.
[27] 王君霞.驅力與死亡驅力[J].湖北第二師範學院學報,2023,40(06):79-83.
[28]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超越快樂原則.高申春譯.米塔貝爾出版社,第46頁
[29] 參見https://www.gcores.com/articles/115424
[30] 吳冠軍.死亡驅力的四個時刻——一個政治哲學史的考察[J].復旦政治哲學評論,2011(00):22-62.
[31] 斯拉沃熱·齊澤克.享受你的癥狀.尉光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11月,第74頁
[32] 吳冠軍.作為死亡驅力的愛——精神分析與電影藝術之親緣性[J].文藝研究,2017(05):97-108.
[33] 周誌強.遊戲現實主義與現實主義的「遊戲」——象征界真實、想象界真實與實在界真實[J].探索與爭鳴,2023(11):169-175+196.
韓宇萌(華東師範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碩士研究生)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