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維/文 近來A股的走勢可謂是驚心動魄,從失守2700點到沖上3600點,又再跌回3200點,驟漲驟跌,A股也有自己的「收視率打法」。
同樣坐「過山車」的還有股民的心情,「看空論」和「速勝論」打起了回合戰,交替占領輿論高地。
這種情況下,免不了很多朋友問:張維,你怎麽看?
近三個月上證指數走勢

來源:Wind
一、如何看待最近的股票市場?——長期低估後的價值回歸
股市如同鐘擺,由投資者信心與貨幣政策等因素驅動,股價短期內可能偏離實際價值,但最終將回歸價值中樞。
過去幾年的熊市,估值嚴重偏離了合理水平,長期壓抑的情緒急需一個突破口。於是,積蓄已久的力量在貨幣政策的驅動下瞬間爆發,市場迅速回擺。這次擺動承載了太多的政策與社會因素,方才展現驚人之勢。
如果認為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中國經濟基本面沒有變化,所以股市也不會有大變化,那麽這個認知是片面的。2001年到2005年,中國經濟以10%左右的速度保持高速增長,而股市卻是一個巨大的熊市。這種背離的情況,無論中外,俯拾皆是。
1990年以來的中國GDP和上證指數走勢

數據來源:Wind
因此,我在基石資本的22條投資「軍規」中強調:投資與宏觀經濟無關。股市不是經濟的晴雨表。從5至10年來看,資本市場與宏觀經濟並不成正比。同時,股價走勢與企業績效也並非完全對應。
心理的因素、信心的力量,被低估了。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市場,股市的價值中樞本來就要高一些。而且我們的冒險精神或者說投機心態,也會導致估值偏高。
但換言之,「繁榮」或許是非理性的,「萎縮」又有何理性可言呢?「非理性繁榮」和「非理性萎縮」本是股市的一體兩面,我們不能只對「非理性繁榮」避如蛇蠍,卻將「非理性萎縮」視為理所當然。

圖:【美】勞勃·席勒【非理性繁榮】
勞勃·席勒引領了行為金融學和行為經濟學的研究。1981年,其釋出Do Stock Prices Move Too Much to be Justified by Subsequent Changes in Dividends一文,指出美國資本市場總體股價變動大大超過了由股息變動決定的趨勢,有力挑戰了有效市場假說。2013年其因「資產價格實證分析方面的貢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如今看到A股財富效應將起,無論是投資者還是企業家,都大為振奮。前段時間我有句無奈的戲言,說中國硬科技突圍最難的一關,可能就是A股3000點這一關,現在這關有望闖過了。
所有政策本質上都是為了提振人們的信心。國家此次對A股的政策支持無疑是極為強力的,但其中起到最大作用的,與其說是可期的海量流動性,不如說是由此傳遞出的國家對民營企業、對資本市場的堅定支持。
「看空論」和「速勝論」,各有其謬誤,因為「做多中國」是一場持久戰,經濟發展與科技進步並無捷徑可走。股市長牛背後的關鍵因素是科技進步與產業升級,其核心密碼是支持民營企業、培育和保護企業家精神,其底層邏輯是法治社會和市場決定論。
二、從剖析全球半導體產業鏈的發展,看如何打好「做多中國」的持久戰
如何打好「做多中國」的持久戰,簡單地從一張圖就可以看到答案。
半導體廠商銷售額排名(單位:億美元)

數據來源: IC insights、TechInsights ,封包括IC(積體電路)和O-S-D(光電子、傳感器以及分立器件)
半導體產業發軔於20世紀50年代美蘇爭霸。1990年的海灣戰爭和1991年的前蘇聯解體,宣告了美蘇兩大集團競爭的終結,美國以科技制勝。半導體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進入民用領域,以所謂的「莫耳定律」,開始了驚人的叠代。
第三次工業革命,即資訊革命,完全離不開半導體產業的驚人成就。同時,半導體產業也是第四次工業革命——人工智慧和萬物互聯的基石。半導體產業可以說是全球最重要的產業,是皇冠上的明珠,是人類智慧的結晶。
縱觀近四十年的半導體發展史,比較歷年銷售額前十名的企業,可以看到,隨著產業的發展,榜單上的企業在不停變換。
日本無疑是成功的趕超經濟體,在半導體領域獲得巨大成功。但其在全球半導體銷售額前十名中的位置,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占據半壁江山,到今天蕩然無存。
20世紀80年代後期,得益於美國扶持南韓對抗日本的策略,南韓半導體企業開始崛起,登上榜單,三星和海麗仕表現非常強勢,但多年來也僅有這2家企業值得一提。
中國台灣地區企業只有一家在榜,但足夠亮眼,即台積電。如今台積電常被認為是半導體產業最重要的企業——【紐約時報】甚至直接說它是全球最重要的公司,因為它可能是「歷史上唯一一家如果被迫停產可能導致全球經濟蕭條的企業」。這家全球最大晶圓制造廠的市占率超過60%,尤其是最先進制程的芯片,超過九成都依靠其生產。所以輝達CEO黃仁勛說,芯片行業的未來就是我們的未來,而台積電則是芯片行業的基石;台積電已經成為全球科技產業的基礎平台。

台積電將其全球最先進的制程放在中國台灣地區的工廠。台積電在美國的壓力下被迫全球布局,到美國亞利桑那、德國德勒斯登、日本熊本縣等地建立工廠。英特爾CEO季辛吉說:「過去五十年裏,油田的位置決定了全球地緣政治。未來五十年,地緣政治將由科技供應鏈和芯片在哪裏生產決定,就是這麽重要。」
但占據榜單最多的還是美國企業。從1985年至今,美國在榜單中的整體位次不斷靠前,而且上榜的企業及其位次一直在變化。20世紀80年代扛旗的是TI(德州儀器)、摩托羅拉,然後是英特爾,之後高通、博通、美光、輝達崛起,可以說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
為什麽日韓台的半導體產業都取得了成功,全球半導體產業鏈卻依然受制於美國?我想僅看這一榜單,原因就很明了。
這些在半導體產業取得了成功的地區,在發展半導體產業上,其實都運用了舉國體制或者舉地區體制,只不過表現的方式有所不同。
日本、南韓和中國台灣地區,都是趕超型經濟體,可以歸結為東亞模式,充分整合現有資源、集中力量推動大企業發展。
日本作為第一個挑戰者,必須依靠舉國之力。在政府的統籌引導下,日本成立了產官學聯合體,集中資源進行研發和大規模生產。
最典型的就是日本的VLSI(超大規模積體電路)計畫。1976年,日本通產省牽頭,組織富士通、日立、三菱、日本電氣、東芝等日本最大的五家電腦企業,還有各研究所的專家,組成了「VLSI技術研究組」。研究中,約有20%的基礎性問題與通用計畫,由五家公司和通產省電子技術綜合研究所的派出人員共同在研究所研究,其余的80%由五家公司各自獨立研究。計畫開發共耗資737億日元,其中政府補助291億日元,占比近四成,總預算的80%—85%給到了私人公司。計畫開發成功後,研究組以「繳納收益」的形式把國家補助又歸還了國庫。1987年,收益繳納完畢,專利權將歸發明人所屬公司所有。
最後,日本先於美國研發出64k和256k 動態儲存器,奠定了其在 DRAM (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市場的霸主地位。在鼎盛的1987年,日本在DRAM市場的占有率達到約80%。
南韓則是日本的叠代版本,更加集中、極致和垂直。20世紀80年代,借美日貿易戰之機,南韓政府透過多種渠道推動以三星為代表的幾家南韓大企業進入半導體領域,提供了大量的財政、稅收優惠,以及研發支持,大力促進了南韓半導體產業的發展。
在此過程中,三星兩代掌門人李秉喆和李健熙父子發揮了重要作用。李健熙是南韓最早看到半導體產業機遇的人之一,甚至在南韓政府及其父李秉喆之前。1974年,年僅32歲的李健熙便已向父親提議要進入半導體產業,在遭到拒絕後,仍未放棄,之後用私人財產收購了南韓半導體公司,這就是三星半導體的前身。1975年,南韓政府才開啟推動半導體業發展的六年計劃;1983年,三星才開始全力進軍儲存芯片領域。
一旦李秉喆決定進入半導體行業,他就直接押上了公司的未來。三星剛進入DRAM行業,市場就進入了低潮期,美日多家企業都選擇了縮減產能或結束市場。在每賣出1片記憶體就會虧損1美元的情況下,全公司上下紛紛建議結束市場,李秉喆卻仍采取了「逆周期投資」的策略,反而加大了投資。到1986年底,三星半導體累計虧損達3億美元,但是在南韓政府的強力支撐下,三星堅持了下來。1992年,三星超過日本電氣,成為世界第一大儲存芯片制造商。
中國台灣地區和日韓的舉措相似。中國台灣地區成功的核心是張忠謀和台積電,用著名管理學家麥可·波特的話說,台積電不僅創造了自己的行業(專業的半導體代工制造產業),也創造了客戶的行業(專業的半導體設計產業)。
李國鼎和張忠謀的故事也是政府支持企業發展的典範。作為中國台灣地區負責產業發展的核心官員,李國鼎提出了創辦台積電的想法,延攬張忠謀回台,讓他自行決定企業發展路線,並幫助台積電排除了起步期的各種障礙,特別是說服政府為台積電出資48%,並幫助募集了剩余的資金。作為企業家,張忠謀於1985年被「十顧茅廬」請回中國台灣地區,1987年創立台積電,開創了晶圓代工的模式,並將台積電帶領成為全球舉足輕重的企業。因此,張忠謀說,沒有李國鼎,就沒有台積電。而黃仁勛說,沒有張忠謀,就沒有輝達;沒有台積電,就沒有今天的全球科技產業。
2005年,張忠謀在74歲的時候退休。4年後在台積電遭遇挑戰的情況下,他又以78歲高齡再幹了9年,把台積電帶上了一個新的高峰。
在台積電的公司治理上,中國台灣地區也表現出了對企業家精神的尊重和對企業家意誌的保護。在董事會構成上,目前台積電僅有一名政府代表出任董事,其余是2位台積電內部董事,7位外部獨立董事,可謂是完全市場化運作。
張忠謀在台積電的股份雖不到1%,在任時卻擁有相當大的話語權,中國台灣地區並沒有太多幹預企業的經營。
而與日韓台充分整合現有資源、集中力量推動大企業發展不同,作為半導體產業的發軔者和引領者,美國選擇了更加細分化、專業化和市場化的方向。相較而言,日韓更強調對在位企業的支持與配合,而美國更重視發展新進企業,促進市場競爭。日韓半導體行業的進入壁壘很高,而美國則致力於透過反壟斷等方式降低新企業的進入門檻。
其中,美國最重要的舉措是培育市場。半導體起源於支持國防業和宇航業需求,美國國防部的采購需求對美國半導體行業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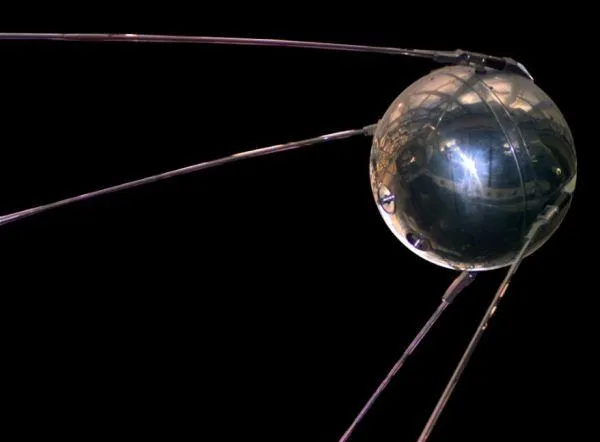
圖:Sputnik-1模型
1957年,前蘇聯發射全球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斯普特尼克1號(Sputnik-1),震驚了美國。(該圖片版權已進入公版)
正是在下遊需求的刺激下,積體電路技術才得以迅速成熟和叠代,成本大幅降低。從1962年到1968年,每個積體電路的平均價格已經由50美元驟降至2.33美元,為半導體從軍用走向大規模民用創造了可能。1962年,美國積體電路還完全依賴於官方市場,但僅僅4年後,整個積體電路的市場規模就增長了30多倍,民用市場則已經占據了半壁江山;1978年以後,政府占比就不到10%了。
美國半導體行業分散化特點的弊端也相當明顯。在某個技術已經成熟、發展曲線變緩的細分行業,他們面對具有規模經濟優勢的競爭對手時,往往顯得不堪一擊。比如在DRAM行業面對日本的競爭中,美國各自為戰的小企業很難與一個高度整合、有序組織的集團軍相對抗。
但隨著半導體產業發展越來越龐大、越來越細分化,少數在位的大企業顯然無法實作整個全產鏈的全覆蓋,美國的分散化和專業化,反而有利於新領域的技術和組織創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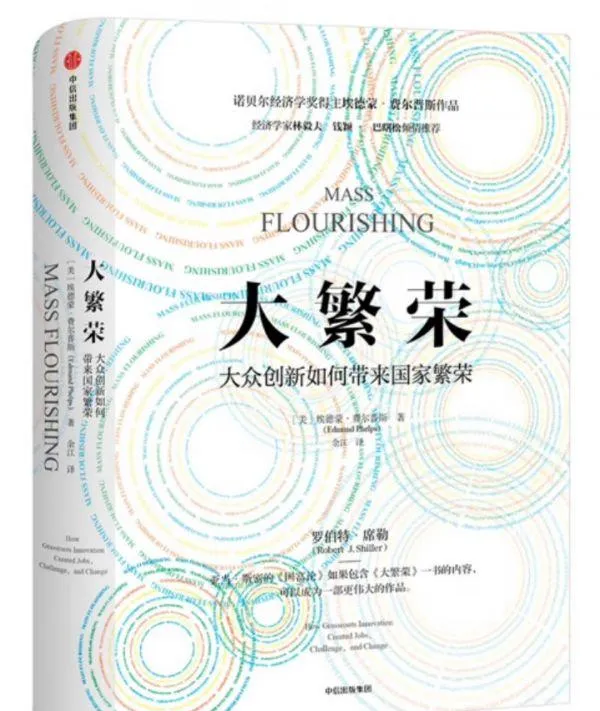
圖:【美】艾德蒙·費爾普斯【大繁榮——大眾創新如何帶來國家繁榮】
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艾德蒙·費爾普斯表示,「草根階層的活力要求人們擁有創辦新企業的自由,以及在冒險成功後得到社會承認和財務報酬的信心,否則產業人士最看好的計畫也無法吸引人們的創新努力。有時,鼓勵政府建立促進創新活動的制度以及給特殊的創新計畫融資固然可以有所幫助,但沒有哪個國家找到過能替代自由企業的煥發經濟活力的機制。」
其中的本質原因在於,趕超模式與領先模式是不同的。
在追趕階段,有現成的方向與路徑為參照,政府可以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有效地調動各種社會資源,從而實作超高速增長。
然而,當趕上之後,從跟隨者變成引領者,政府失去了明確的目標和方向,而如果要自主在未來無數的可能性中選擇出正確的那一個,就變成了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縱使是「力拔山兮氣蓋世」,也只能「拔劍四顧心茫然」。只有在市場經濟下,無數個體在利益驅動下,進行無數次的試錯,才更有可能走出最高效的道路。
作為最成功的趕超案例,日本變身引領者後,因循同樣的套路,也沒能再現過往的成功。20世紀80年代日本實作半導體記憶體全球領先後,為了在資訊科技領域也超越美國,於1982年提出了第五代電腦計劃,目標是開發出具有大規模平行計算與人工智慧等能力的新一代電腦,並舉全國之力投入了巨資開始實施。計劃的技術目標很清晰,但設計思想並不完善,步子也邁得太大,10年後,計劃宣告失敗。而同期在美國,1984年,蘋果公司推出了Macintosh電腦,首次將圖形化使用者介面廣泛套用到個人電腦之上。如今,日本的電腦和互聯網行業都乏善可陳。
創新的不可計劃性,在前蘇聯上體現得更為明顯。前蘇聯半導體產業的失敗,即為政府強行幹預創新的惡果。前蘇聯在半導體的起步階段與美國幾乎並駕齊驅,前蘇聯發明晶體管的時間,僅僅比美國晚了幾周。然而,在政府的主導下,在兩個關鍵的十字路口,前蘇聯的半導體產業都走上了錯誤的方向。
第一次是晶體管與真空管的選擇。由於蘇聯軍方對技術前景缺乏認知,所以基於對核戰爆發的考慮,以及資金總量的限制,蘇聯放棄了自己認為不適合核戰爭的晶體管方向,舉國之力繼續研究真空管,並在該領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憑此造出了世界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斯普特尼克1號。然而,在另一邊,走全面探索道路的美國最終找對了方向,發明了積體電路。
第二次是自主創新與全面復制的選擇。在意識到積體電路才是未來後,前蘇聯也調轉方向開始研究積體電路。然而,相對於自主創新,蘇聯選擇了全面復制的戰略,主管領導不顧科學家的反對,要求科學家必須「100%」地嚴格復制美國的芯片和裝置,導致前蘇聯的半導體產業永遠只能跟在美國半導體後面亦步亦趨,從根本上斷絕了前蘇聯創新的根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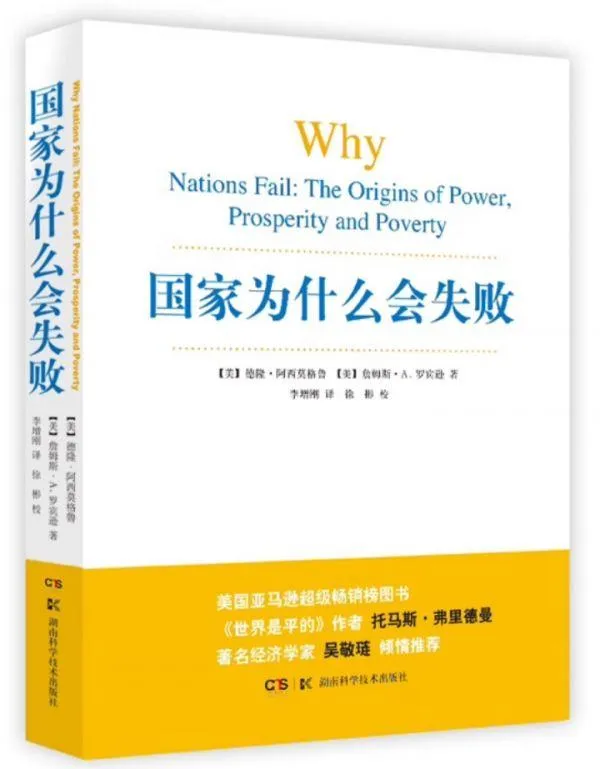
【美】達龍·阿西莫格魯,【美】詹姆士·A.羅賓森,【國家為什麽會失敗】
為什麽有的國家富裕,有的國家貧窮?阿西莫格魯和羅賓森認為核心在於政治和經濟制度,包容型政治制度和包容型經濟制度是實作長期經濟增長的關鍵,攫取型政治制度和攫取型經濟制度雖然能夠在一定時期內實作經濟增長,但是不永續。(阿西莫格魯和羅賓森共獲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艾德蒙·費爾普斯、曼瑟·奧爾森、達龍·阿西莫格魯等傑出學者,都長期致力於探索實作繁榮的路徑。他們聚焦於政府、企業與市場的關系,產權和激勵等核心問題進行了深入地研究,其觀點很有啟發意義。基石資本的讀書推薦,也都一直在推薦這些學者的書。
三、為什麽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是關鍵
由政府主導創新的前蘇聯模式以失敗告終,而無論是分散式創新的美國模式,還是集中資源辦大事的東亞模式,這些取得了半導體產業成功的模式,都有一個共同點,即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由企業主導創新。
原因很清晰:硬科技需要至少一兩代人的努力,需要企業家精神,而這些,在民營企業中才更為彰顯。
這個道理,在張忠謀對李健熙的點評中被生動闡釋: 「日本公司的沒落除了日元升值,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南韓三星的李健熙,這個人很厲害……」
「南韓三星的崛起,李健熙絕對是關鍵。因為他是老板。日本強的半導體企業東芝、日立、NEC(日本電氣),他們的這個半導體總經理都只是專業經理人,而不是老板。」
「好的老板是很難找的,一千個裏頭只有一個;不過,李健熙剛好是那一千個人當中的一個。李健熙本身不是半導體專家,可是他認識、了解半導體的潛力,也認識了手機的潛力,是關鍵人物,他是英雄造時勢……」
在過去的40年中,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無可置疑的成功。如何看待所謂的「中國奇跡」?
科斯曾給出一個解讀。他在著作【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中指出:中國經濟的改革事實上是一種二元並列的狀態,一種是由官方領導和發起的改革,另一種則是由底層民眾自發形成的改革,即「邊緣革命」。政府主導的改革釋放了很多政策紅利和改革紅利,起到了一些作用,但邊緣力量所推動的改革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真正推動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
家庭聯產承包制、鄉鎮企業、個體戶和經濟特區是中國市場經濟轉型中四個最重要的「邊緣力量」。這些體制外力量發動的邊緣革命,將私營企業重新帶回到經濟體制中,為日後的市場轉型鋪平了道路,帶領中國逐漸步入了現代市場經濟。中國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解決了中國經濟的很多問題,包括經濟執行效率、稅收、就業、GDP(國內生產毛額),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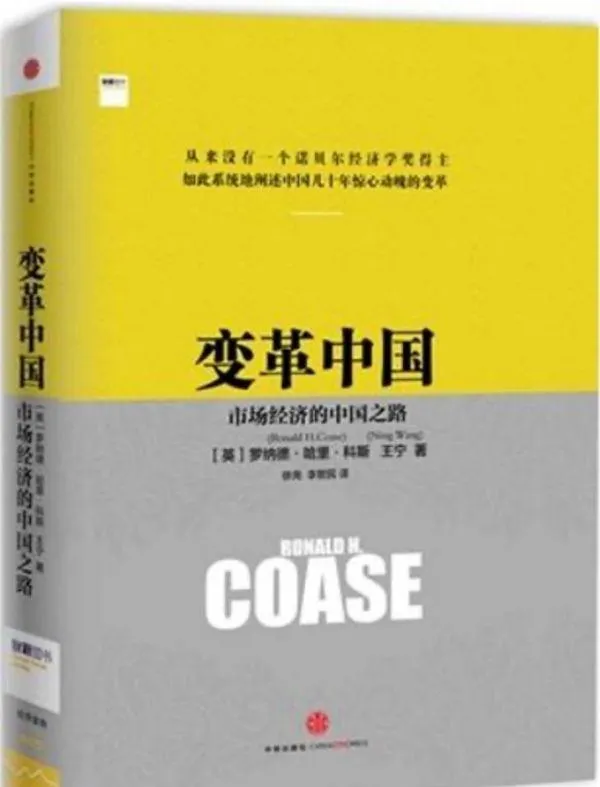
圖:【英】隆納·科斯,王寧,【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
清華大學教授錢穎一和長江商學院教授許成鋼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他們發現,中國的經濟改革比東歐和前蘇聯更成功,是因為中國是以區域「塊塊」原則為基礎的多層次、多地區的形式(「M-型」經濟),而後者是一種以職能和專業化「條條」原則為基礎的單一形式(「U-型」經濟),前者能夠更好地解決激勵問題。中國的M-型組織讓地方政府擁有很大的自主權,得以在國有部門以外建立市場取向的企業來使本地區得到發展,為促進非國有部門的進入與擴張提供了機會和可能性。
錢穎一還指出,在產權安全的情況下,私有企業的效率是高的,而其他形式所有制的企業因代理人問題會造成扭曲。然而,如果是在現實經濟中存在其他扭曲,譬如沒有法治而導致產權不安全,那麽純粹的私有企業就會支付額外成本,以尋求對產權的保護。
許成鋼還進一步對比了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轉軌經濟的企業層面的特征和績效,確認中國並不存在超越市場經濟規律的特殊模式,中國過去發展成功的方面與世界其他國家發展的普遍規律一致,即私有企業的績效超越國有企業。中國的私有企業的績效是轉軌國家各類企業中績效最高的;但是同時,中國國企的績效則是轉軌國家各類企業中最低的。
所以他說,「真正的中國奇跡,不是經濟發展本身,而是中國的民營企業,從不合法到合法、從無到有的巨大發展。」
無法解決公司治理問題以及辨識和保護企業家是國企的「阿基里斯之踵」。國有資產管理方的核心使命和責任是辨識、發掘和保護企業家,透過改革產權機制和治理結構等方式,使企業家持有一定的股權比例,並對企業經營具有高度自主權,從而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但在各種受限下,這一使命極難完成。
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任正非和張忠謀都是當今最為卓越的企業家。任正非1944年生,43歲時創立華為,張忠謀1931年生,56歲時創立台積電。華為和台積電都成立於1987年,如果他們在國企工作,任正非在2004年、張忠謀在1991年就得退休了,那麽也就不會有今天的華為和台積電了。
企業家在經濟與產業開發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激發企業家精神、保護企業家信心,才是推動發展與進步的核心要義。
民營企業家的信心何在?來自對未來的良好預期,包括對政策、法律、營商環境、產權以及安全等各個方面的預期。在滿足了溫飽的生理需求的今天,安全需求已成為最基本的需求,若連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尊重與自我實作的需求都無從談起。這不符合李錄說的常識。不能控制地方政府的趨利性執法,是國家治理的失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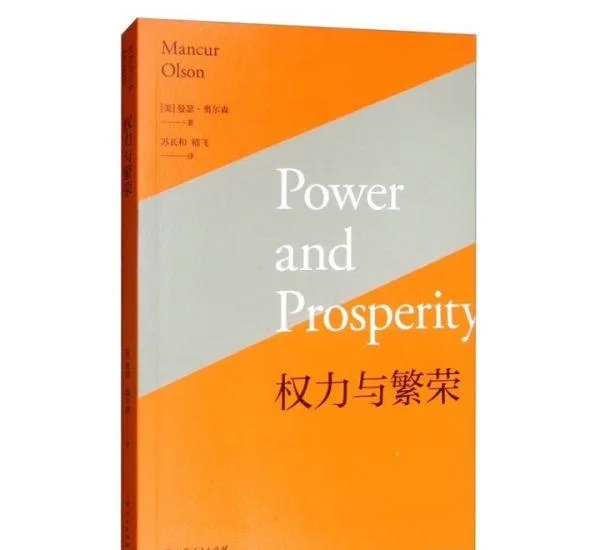
【美】曼瑟·奧爾森【權力與繁榮】
奧爾森認為,繁榮的動因是個人權利,而政府既是個人權利的保護者,也是個人權利的侵犯者,因此國家權力與私人權利(或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相互關系決定了國家的繁榮。所以能夠給市場經濟帶來繁榮的政府,是一個「強化市場型政府」,它有足夠的權力去創造和保護個人的財產權利,並且能夠強制執行各種契約;與此同時, 它還受到約束而無法剝奪或侵犯私人權利。
而對未來的良好預期,來自法治社會,來自對民營經濟堅定不移的支持。
這也是為什麽我一再重申,我們需要舉國體制3.0。
五年前,我首次提出了「舉國體制的3.0版本」:中國要從追趕者成為引領者,成為世界第一,需要建立良好的法治體系和產權機制,最大限度地調動全社會的能動性,激發企業家精神,創造一個「舉國體制的3.0版本」。
「舉國」舉的是什麽「國」?1.0版本的「國」,只包括少數精英,大部份人只是龐大國家機器中不需要思考的螺絲釘;2.0版本的「國」,千千萬萬大大小小的民營企業家由「邊緣力量」成為創新創業的主力軍;而3.0版本的「國」,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將成為創新的有力分子,共同構造一個德魯克願景中的「企業家社會」,它要求所有機構的管理者把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作為企業和自己工作中的一種正常、不間斷的日常行為和實踐,而每個個體都要持續不斷地學習與自我發展。在企業家社會中,任何社會、經濟、產業、公共服務機構和商業機構都將保持高度的靈活性與自我更新能力,並因此實作持續的創新與繁榮。
在「舉國體制的3.0版本」下,經濟上應以市場和資本為基礎,政治上應立足於法治與責任制政府,要透過建立良好的產權機制,保護企業家精神,從而更好地支持民營經濟。

圖:【美】彼得·德魯克【創新與企業家精神】
為什麽要提出「舉國體制的3.0版本」?
因為支撐龐大的科技產業鏈,需要群雄輩出、群星璀璨的中國企業。
以最為重要的半導體產業鏈為例,從下面這張全球半導體產業鏈全景圖可以看出,半導體產業鏈是如此龐大,至少有數十個重要細分產業,而每個細分產業的核心企業,絕大多數都是海外企業,中國大陸企業不過寥寥幾家。而且,國際上的核心企業,幾乎都是民營企業。
全球半導體產業鏈全景圖

圖說:這是全球半導體產業鏈最重要的企業,可以看到,在140多家企業中,中國企業只有10多家。來源:基石資本研究。
因此,中國如果要完成全半導體產業鏈的突圍發展,只實作少數企業的單點突破是不行的,還必須要誕生數十家全球領先的半導體企業。而這,需要千千萬萬企業的共同努力。
而且,在產業鏈高度分化的今天,哪怕只是其中一個產業的突破,也需要產業鏈上下遊的通力協作。
在半導體「卡脖子」問題剛剛進入大眾視野的時候,有一個著名的疑問:中國能造出原子彈,為什麽造不出光刻機?
現在大家已經了解,光刻機雖然只是一台機器,背後的產業鏈卻極為漫長和復雜,如今在光刻機領域一家獨大的ASML(阿斯麥),亦是典型的全球產業鏈合作的成功產物,絕非一家之功。
例如,在研發端,ASML的大量技術,都是與上遊供應商共同研發的。光源和鏡頭是EUV(極紫外線)光刻機最核心的部件,前者的關鍵技術來自美國Cymer公司,後者則來自德國光學龍頭蔡司旗下的蔡司半導體。因此,2012年,ASML斥資25億美元收購了Cymer;2016年,ASML又斥資10億歐元收購了蔡司半導體24.9%的股份。
ASML不僅繫結上遊供應商,也繫結下遊客戶。在ASML成為市場領先者後,光刻裝置又發展到了EUV光刻機階段,技術的復雜性和巨額的投入讓尼康和佳能等主要競爭者都望而卻步,ASML亦無力獨自完成研發。於是,2012年,ASML發起了客戶聯合投資專案(Customer Co-Investment Program),向英特爾、台積電和三星進行募資,用23%的股份,從這三大客戶處募集到了超過50億歐元的資金,以及後續的采購承諾。這一數位,已經超過了當年ASML 47.32億歐元的總營收。
據其2023年年報,ASML有約5100家供應商,遍布全球,其中荷蘭本土供應商為1600家,除荷蘭外的EMEA地區(歐洲、中東和非洲)的供應商為750家,北美地區的供應商為1350家,亞洲地區的供應商為1400家。
再看其主要持有者,ASML前兩大股東分別是Capital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Company(10.32 %)和BlackRock(7.95%),都是美國公司。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ASML不只是一家荷蘭企業,更是一家全球企業;ASML的成功,不只是一家企業的成功,更是全球半導體產業鏈的成功。
換句話說,如果中國希望完全依靠本土產業鏈生產出與ASML同級別的光刻機,也需要5000家同量級的本土供應商。當然,我們不必也不可能實作全本土產業鏈,我們力爭的,是產業鏈所有環節的可控,核心環節的獨立自主,小部份重要環節的相互依賴或者說相互「卡脖子」,這樣其實就能完成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突圍。
而如果實作了這一步,也就意味著,中國半導體全產業鏈的崛起。在此過程中,民營企業將是主力軍。
正如「創新之父」熊彼特所言,「企業家成群地出現是繁榮產生的唯一原因」, 「沒有創新,就沒有企業家」。
熊彼特認為,創新的非連續、不均勻性是經濟周期產生的根本原因。企業家是創新或者說「創造性淪陷」的實施者,當少數先鋒打破創新壁壘,成功開辟出新的道路,企業家將在他的促進與激勵下遞增出現,當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加入創新浪潮,新組合將成群的出現,繁榮便會到來;而相反,當創新活動減弱,大家都做著模仿復制的工作,生產經營將越來越無利可圖,蕭條就會來臨。繁榮與蕭條就這樣交替地波浪式運動。

圖:熊彼特及其著作
基石資本曾領投合肥長鑫儲存。合肥長鑫儲存得到了安徽省政府的巨大支持。巨資投入體現了安徽省政府的前瞻與擔當。
2023年2月,在安徽省政府的一個發展科技產業的座談會上,我提了三條建議:
一、放棄幻想,長線規劃,系統布局,一張藍圖繪到底;
二、承擔責任,集聚資源,支持民營企業,發掘和保護企業家;
三、舉國體制與市場化分散探索並重,大眾創新更有活力。
經濟發展與科技進步是一場持久戰,「看空論」自然錯誤,「速勝論」也並不可行。股市的長牛,需要政府的支持,需要一張藍圖繪到底,也需要企業的努力,需要發揚企業家精神。
創新就是企業家精神。第四次工業革命來臨之際,讓我們繼續堅定不移地支持民營企業,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打好做多中國的持久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