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含著眼淚看完電影【我本是高山】的。鄉村教師張桂梅的故事,讓我回到了從前,回到母親在萬古堂小學教書的日子,回想起了那些日子裏的人和事。
母親說,張桂梅老師了不起,能把學生當自己孩子的老師,都是好老師。說起在鄉村學校時的生活,母親總是滿懷眷戀和深情,心心念念的,是昔日同事、學生和萬古堂的故事。許多舊事早已塵封,有的生命走向了永恒,一些故事還在繼續。
回故鄉湖北赤壁,總要回到蓮花塘,尋訪萬古堂。赤壁過去叫蒲圻,居長江之南,因蒲草萋萋而得名。1986年撤縣設市,1998年命名為「赤壁市」。千古風流浪淘盡,天下不敢小赤壁,1800多年前發生的那場三國赤壁之戰,讓人們記住了這裏。赤壁西南部的山裏,坐落著我的祖居地蓮花塘劉家和我生活過的萬古堂小學,兩者緊鄰,中間隔一道山崗。
重回故地,觸景生情。往事歷歷,時光倒流,一幕幕地復原了鮮亮的顏色。
那是我心中溫暖的回憶。

一
出赤壁城,望西南角,田疇寬廣平展,遠處山線隱約,這一大片沃野叫大田畈。春日綠秧無邊,夏秋稻浪翻滾,冬雪皚皚連天。大田畈的西南邊角,幕阜山的北麓深處,有一處簡陋的校舍,土磚白墻黑瓦,有塘有井有林。這裏原本不是學堂,而是一座鄉賢祭堂。傳說在若幹年前,一位姓萬的法師曾在這裏積德行善、護佑生靈,當地百姓為了感念他的恩德,在這裏修建了一座五開間的祭祀堂,供奉萬法師的泥塑像,取名「萬古堂」。若幹年後,祭祀活動稀少了,祭堂衰敗了,改作學堂,取名「萬古堂小學」。
再過若幹年後,萬古堂小學迎來了我們一家。
來萬古堂小學之前,我的母親在一個今天叫神山鎮的神山學校當公辦代課教師。學校附近有山,因為從不被水淹而稱神奇,山曰「神山」,水曰「神山湖」,湖裏盛產蓮藕菱角魚蝦。母親本是城裏姑娘,因出身封建家庭,被下放在這個貧瘠卻不乏魚米滋養的湖鄉。父親當年從北師大物理系畢業後,分配在武漢的一家兵工廠工作。忽然有一天,地方教育部門就出台了一項政策,規定教師各回原籍。母親原籍在城裏,但出身問題回不去,只好選擇了父親的原籍為原籍,拖兒帶女地從湖鄉到山鄉,落戶在更加貧瘠的蓮花塘劉家。
那是一段註定要烙進我生命裏的日子,整十年。

孩童的眼裏,所有的山都是高山。蓮花塘村坐落在山坳之中,三面是山,一面是田壟。村口有一塊丘田叫桅桿丘。劉家祖上曾出過翰林,丘田裏的桅桿是供翰林回鄉省親時系馬用的。門前有塘,塘裏有魚,田田的荷葉擠擠密密,紅的白的荷花高高低低,或含苞未放或花蕊盡綻,像倒插的毛筆、燃著的火炬、挺舉的標題。一條淺溪,從頂上塘流過中和塘,註入了蓮花塘。
秋冬時節,整個山坳草木過霜、山色凝重,寒蟬淒切噤聲。遠處的關山尖、平山尖獨立寒秋,山抹微雲、天黏衰草,居高傲視群巒、平視天公。落雪封山的日子,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撲打雪峰盡頭的冬日。屋檐冰掛如簾,港汊冰柱如瀑,天地猶如雪窖冰窟。及至春夏,後坡草葉蔥蘢,林木競長,溪邊花開灼灼,藤蔓纏繞。村後早鶯爭暖樹,檐下新燕啄春泥,松竹桃在排隊,枝頭花在聚會,喜鵲斑鳩在現場直播。萬紫千紅,綠了又黃,紅了再青,青綠是山裏四季的主色。
萬古堂小學在山的那一邊。從蓮花塘到萬古堂的山腰,隱約有四條小路。第一條路,從塘塍上陡坡,迎面是一棵大梨樹,樹身上吊綁著大垛的幹稻草,是牛兒們過冬的草料。懸在空中,不渥堆,不腐爛,總有太陽的味道。牛兒揚著脖子,用嘴撕扯樹幹上的草們,不多吃,不搶吃,想必是知道須留些個,待大雪封山、草料短缺的日子再吃。過了這棵大樹,是一棵棠棣,樹上有刺如錐。小時候爬樹,胳膊腿兒虬在枝丫間嬉戲,誰的屁股不小心被刺紮著了,一定是錐心地疼、嗷嗷地叫。棠棣春末開花,艷艷灼灼,花簇緊致,禿禿的果兒不大,卻是成雙成三地紮在一起。讀到【詩經·棠棣】裏的「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方悟古人以棠棣喻兄弟之情的由來。經過這兩棵樹,沿山脊一直走,順坡下去就是小學的菜園子。地裏的青黃瓜、紅番茄們等不到成熟,就被孩子們摘了充饑解渴;第二條路,從村牛欄屋的側面上斜坡,一片桐樹林,連著一片李樹林、梨樹林。不上課的夏日,爬上粗壯的油桐樹,四仰八叉地橫躺在闊葉粗枝間讀書,有知鳥聲陪伴,可以忘了時辰,不聞大人疾呼聲。春雨蒙蒙,小路上李樹開花一片白,含煙帶雨,嬌翠素靜。清明時節,早起上學,忽見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花瓣雨,春泥路,顧盼貪玩不思學。這條路可以一直通到學校的公廁——山村現代文明的稀有標誌,廁所內外滿是孩子們的塗鴉;第三條路,爬蓮花塘後山坡,上竹林,翻山包,沿山腰荊棘路,走過一片墓地,直達學校的背後。盛夏之夜常有鬼火遊動,據說還追人跑。過年前夕,家家戶戶往山上的墓地送祭燈,寄托對祖輩親人的思念,溫暖逝去的魂靈,算是天上人間兩廂牽掛了。遠遠地望去,漆黑的夜空宛如天界,隱約的天燈照著天街。這條路雖近,孩子們卻很少走,一分窄,九分怕;第四條路,從塘堰出發,順小港走上百米左拐,直通小學門前的萬古塘,塘裏有睡蓮、水藻和魚兒。一條平路連線兩口荷塘,走的人多。也有害怕的地方。路的左坡有一片菜地,菜地的上方有一座墳,裏面躺著的是我小學三年級時的女同學桂兒。放學打豬草,見山坡上的供電變壓器間有茂盛的豬草,她一伸手,被強大的電流吸住了。桂兒媽每天下午在墳前淒厲的長哭,持續了好多年。這生命的悲歌,成了全校師生心酸的記憶。

其實,不止這四條山路。
鄉下孩子,有腳就有路。有家住京廣線邊上架橋鄭家的同學,每天能看到京廣線上的火車「況且況且」地開過來,「胡吃胡吃」地開過去,我特羨慕他們,還專門到鄭姓同學家裏夜宿,聽火車的聲音。他們上學路遠,要穿過寬寬的田畈,一不小心被漫天的油菜花、無邊的紫雲英、滿畈金黃的稻海麥浪牽絆了眼和腳,或者一不小心被路邊小港小汊的魚兒蝦們逗起了玩興,或者一不小心想在泥塘邊的溫泉氹裏洗個澡,上學一準兒會遲到;也有走得更遠的,有一個男生,家住茅山張家,總是打赤腳或穿草鞋——除非是落雪結冰淩的天兒才穿球鞋。放學路上要翻幾座山包,沿清澈可見遊魚水草的南渠走一陣子,過橋後拐進山谷,沿碧綠的水庫一側山路上行,再順著曲曲折折的溪溝上坡,在青石板台階上呱嗒呱嗒地獨行,緣長長高高的天路登頂,回到修竹茂林中的家——一個高得不能再高、深得不能再深的「山以」。這個詞重音在「以」,赤壁話裏大約是指大山深處的意思。山窩裏有終年不化的雪,頭頂上有飛機飛過的聲音,滿目山外山,離天三尺三。這一路上會不會踩到蟲蛇,會不會遇到野豬的襲擊,會不會一腳踩翻了石板,或滑溜掉到深澗裏,不知道。只知道這位同學憑著一雙赤腳,在縣裏運動會上取得了田徑計畫的好成績。
當然,更多的同學家住附近,老屋任家、新屋任家、月亮井任家、大塘壩任家、角塘灣李家的孩子多,遠一點有高井畈劉家、新屋費家、畈裏杜家、顏家鋪黃家、老屋鄒家、鴨棚梁家、楊家灣盧家、牌坊盧家的。再遠一些,是坡裏童家、鎖石嶺童家、架橋鄭家的,最遠大概是馬鞍嶺盧家的,跋山涉水十幾裏。
道阻且長,年復一年,行則將至,路在前方。莊稼青黃接繼,孩子們接茬成長。他們腳下的路,只有一個指向,那就是萬古堂小學。
那個時候,簡陋的萬古堂小學,是山裏孩子觀望外界的唯一視窗、聯通世界的唯一平台,是他們的唯一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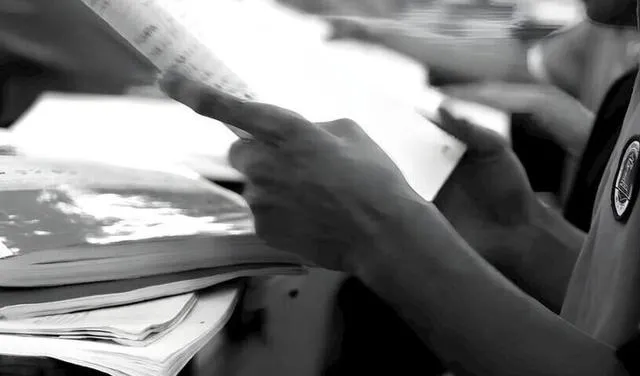
二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得清這條路。
於是,就有了家訪。
老師們白天教課,像農民一樣日出而作,晚上常常要走村串戶,跟家長們說說孩子的事,讓家長少給孩子們派重活、多給時間寫作業。孩子們則害怕老師告狀,挨家長揍,提心吊膽。不少老師像張桂梅那樣,費盡周折地追回逃學、失學的孩子。天晴不怕路遠,落雨不怕泥深,常常是苦口婆心一晚上,深更半夜才回家。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歸的是老師們。
這樣的夜晚,我就和妹妹、弟弟小手牽小手,牽著家裏的狗,站在漆黑的山頭等媽媽。仲夏的夜,蛙聲如鼓,山蚊子兇猛,伸手不見五指,擡頭不見月牙。兄妹仨越等越害怕,默不作聲,不敢看不遠處的墳山,怕山裏的鬼,不敢動彈,怕腳下有蛇。思念在恐怖的夜海裏掙紮,等待在巴望的夜風中硬撐。偶爾有光,分不出是近處的螢火蟲在閃躍,還是遠處的手電筒在尋路。等到光亮漸近漸大了,兄妹仨壯著膽大聲哭喊「媽——」,有回應了,卻是男聲,也是家訪的老師,「我從程家回來,你媽媽到高井畈劉家去家訪了!」這樣的夜晚,這樣的等待,常有。
萬古堂小學有校沒園,只有小菜園。校舍是四排平房,四方四正,泥磚黑瓦,屋頂有幾片玻璃亮瓦,但光線不甚敞亮。大門對著萬古塘,後門有陡坡上山。放學了,眾聲四散,喧鬧歸零,只剩下我們一家四口。以及角落處,住著的一位做飯種菜養豬,兼守門的工友——毛子嶽師傅。
大門一關,後門一閉,再頂上一些木頭柱子,以防盜賊撬門,萬古堂小學便在巨大的夜幕包裹下睡去。比夜更靜的是萬古堂的夜,比夜更黑的是小學的四周。萬古堂夜空的星子,卻是非常的明亮而幹凈,像山裏孩子純真的眼。滿天的星鬥,熱鬧的星語,是寂寞的我最貼心的玩伴。那時正癡迷於讀【十萬個為什麽】,書裏描述的神奇太空令我向往,仰望星空發楞,想象的翅膀在星際間翩躚。若幹年後見到航天員楊利偉,我對他說,「我兒時的夢想,就是長大後成為現在的你。」

小學裏也有熱鬧的時候。每到暑假,這裏是鳥們、貓們、蛇們、鼠們的樂園,也經常上演貓撲老鼠、蛇吞小鳥的慘劇。山裏有最藍的天、最白的雲,以及最凝滯的時空。晴空裏盤旋的鷹或者鷂子,會突然一個俯沖下來,叼走禾場上睜著無辜雙眼正看它的小雞。有村裏的孩子們貓著個腰,悄悄地把校門卸下,或者把木窗的柱子掰開,偷偷地溜進教室,輕手輕腳地把長板凳扛到山坡上,翻過來當滑板,一溜到坡底,一滑一下午,一個個放肆地大笑,於是好多板凳面被磨得奶昔大哥的。
山裏最黑的分時是夏夜,最白的季節是在年末歲頭。冰天雪地,蓮花塘、萬古塘裏的水被凍縮到塘底,再包裹一層冰毯。寒塘孤影,冷月攝魂,天地之間寫滿一個字:冷。碩大厚實的雪被,把校舍內外蓋得嚴嚴密密,不留一點黑,沒有一絲縫,不冒一息熱氣。校內空曠處,雪面完好,只有三兩道餓鳥尋食的細爪淺痕。此時的此地,是童話的世界,是孩子們趴雪人、滾雪球、堆雪人、打雪仗的樂園。再冷,也凍不住孩子的腳,凍不住快樂的心。
天地為屋,山川作家,與萬物為伴,受風雨洗禮,汲日月之精華,與自然無限貼近,這是山裏孩子的福分,何苦可言?他們像林中的綠葉、坡上的微塵、山間的小草,紮根在廣袤肥沃的土地,附著在堅實挺立的高山,蘊涵在湖塘港池河渠之中,土地、山川養育了他們、呵護了他們。與城裏孩子比,他們沒見過電車,沒上過影院,沒有零花錢和漂亮衣服,沒住過蛇鼠爬不到、風雨淋不漏的樓房,但小有小的茁壯,弱有弱的頑強,落地生根,微而不卑,都是山的赤子、泉的音符,是自然的精靈、錦繡的顏色,每一棵小草都有自己的春天,有自己的歡歌。自然是最好的老師,教他們在苦難中成長;生活是最好的打磨機,讓他們在磨礪中成熟。老師則是最好的陪伴,不光是知識的教授者,更是人生的路標,是澆開他們夢想之花的園丁。
人在福中不知福,身在苦中不覺苦,這大抵是人生的常態。那個時候的我,和其他孩子一樣,沒有覺得是在過苦日子。
但大人們不這麽想,老師們不這麽想,政府也不這麽想,他們在努力改變萬古堂的面貌。

於是有了初中部,萬古堂小學更名為大田學校,教學條件、生活環境改善了。廟宇校舍被推倒填平,山坡上新起了一橫兩豎三排房子。老師、學生多起來,路遠的學生和老師開始住校。每一條路線上的學生都有老師護送,一直等到孩子們各回各家、各找各媽。
我記得這樣的情形,有自習課的晚上,孩子們在教室裏或悄無聲息地做作業,或嘰嘰喳喳地爭個不休。誰家的狗兒跟進教室,趴在課桌底下,老老實實地不吭聲。老師們聚在隔壁大屋裏備課,燈光如白晝,門窗漏著風。屋外是雪光輝映的天,寒風呼呼地吹。人往團裏縮,拿粉筆的指頭僵得有些不聽話。凍得住呵氣,凍不住思維和話語。面黃肌瘦的老師們熱鬧爭論著的,似乎是一道方程式式。認真、執拗,直率、幽默,不時夾雜幾句鄉俚粗話。屋中央一盆塌爐,劈劈啪啪地迸著炭火星兒。偶爾有煙冒出來嗆人,便有人搶了火鉗扒扒捅捅。黑板旁有一煤爐,直角拐彎的煙筒直接伸到屋外,爐上吊一銅壺,壺蓋嘟嘟地奏著歡快與生機。屋裏有火,心裏有主,話題也暖和。一挺懶腰伸腿兒,把誰家媳婦捎來的排骨熬湖藕小瓦罐差點兒踢翻了,趕緊賠笑臉兒。
我記得這樣的情形,勞動課是在山上采油茶,或者砍柴、開荒,忽然間就風雨交加、電閃雷鳴。老師們拼命地招呼學生往回跑,孩子們卻歡天喜地,在風中叫、雨中跳。所有樹葉兒亮出了灰白的葉背兒,在風中狂舞,在雨中洗澡。低沈的天霎時就暗下來,像黑夜。屋頂的瓦片被吹得哢嗒哢嗒響,窗上的油布被吹得沒了蹤影,孩子們這才有了一些驚慌,縮在座位上不敢動,任憑風啊雨啊黑暗啊鬼怪啊從黑洞裏沖進來,那是一種從沒見過的黑。「哢嚓——」,一聲炸雷,扯一道閃電,把雨簾下的世界刷成一片慘白。一剎那,只見老師端坐在教室門口的板凳上,神情嚴肅得像那位護佑生靈的萬法師,孩子們這才穩住了神。校舍像一尊靜坐山坳的佛,風雨不動安如山。就這麽靜靜地待著,像鬧鐘停擺,直到驟雨初歇,山野一片寧靜,一片清亮。「哎喲——」坐在最後一排的高個兒女生長籲一口氣,「天亮啦——」,有人喊。教室裏立刻像鴉雀兒潑了蛋,恢復了打鬧。
風雨過後的天,依舊是孩子們的天。

三
樹兒黃了,有回綠的時候。青絲洗白,如霜如雪,卻返不了青。
一批批一代代學生走出萬古堂小學、大田學校,走向廣闊的田野和工礦企業,走向縣城、市裏、省城,到了沿海、京城,有的走到了國外,老師們依舊守著那一道山溝,山溝裏的那一片校舍,校舍的那一角寒風苦雨。
只是,老師們都老了,老得記憶的照片都殘黃了。
語文老師任豫章是大田學校最老的老師,家住大塘壩任家。他是萬古堂小學的創辦人,是所有老師的老師。我叫他舅爹,因為他是我父親的親舅舅。記得他當時經常犯胃疼,不得不偎在學校的竈膛邊烤火取暖。但他很長壽,他84歲高齡那年,我去看望他,給老人家帶了一件寧夏產的羊毛坎肩,穿上像個老羊倌。他的三兒子任三治在大田學校當過老師,是我的表叔,在我眼裏他什麽都懂,還教我練過拳。三治老師有個弟弟叫任四維,是我的同班同學,我也得叫表叔。我一直對兩位表叔的名字很好奇。儒家講「人治」,法家講「法治」,道家講「無為而治」,這「三治」是中國古代的三種治國思想。管仲說,「禮」「義」「廉」「恥」乃「國之四維」,是治國的四大支柱。以「三治」「四維」等聖賢思想為兒子命名,可見任豫章老師是有見識、有格局的文化人。兩位表叔沒有辜負父輩的期望,三治表叔後來當了趙李橋中學的老師,四維表叔和我一起參加那年中考,整個鄉所有學校考取重點高中蒲圻一中的,只有包括他和我在內的五個人,我還考了個第一,大田學校當時很是風光。進蒲圻一中不久的一個中午,我倆想媽想哭了,幹脆溜號,翻山越嶺一路狂奔跑回家,我卻被媽媽揍了幾巴掌,揣上兩個煮雞蛋,又趕回了學校。如今,當中學教師的四維表叔是赤壁有名氣的詩人,經常在全國性媒體上發表古體詩詞;李傳海老師是老校長,家住角塘灣李家,翻過學校東邊的山嶺就是他家,他的妻子叫寶兒,不識字。李校長有兩女兩子,大女兒李紅英、二女兒李秀英跟我是同學,大兒子叫李建文,跟我妹妹是同班同學,小兒子李建武患小兒麻痹癥,從小離不開拐杖。李校長得了一種佝僂病,背駝了一輩子,像個問號。學生們懼怕李校長,怕他責問:「你怎麽又遲到了?」他每次假期到武漢治病,都住在我父親那裏,他們兩個大人擠滿了大床,我被擠在角落,記得李校長的駝背總是躺不直,只能側著睡。李校長在學校工作時間最長,一輩子勤勤懇懇任勞任怨恪盡職守。有一次,狂風暴雨把屋頂的瓦刮壞了,教室漏雨,李校長爬長梯上屋頂撿瓦,一腳踏空,從屋頂滾落下來,昏了過去,我媽和老師們都哭了。當時我天真地想,這一跤要是把他的腰背摔直了,那該多好啊。李校長的四個子女沒考出來,但一向表情嚴肅的他,為本校那年能有兩個孩子考上蒲圻一中而興高采烈;陳俊德老師是教務主任,教數學,臉上有兒時得天花留下的銘印。陳老師家跟我母親家是一個家族,是過去縣裏封建家族「陳半城」陳東華家的後代。陳老師家是陳家六老爺家的,我母親家是陳家八老爺家的,說起來是沾親帶故的。學校有幾位陳老師,所以陳俊德老師稱呼我媽為「二陳」。陳老師是公辦教師,家住很遠,只能在周末回家,在我的印象裏,他是樂天派,成天笑容滿臉,不曾有過生活的苦,俏皮話一肚子,在輕輕松松中把難事就辦妥了;任友元老師是學校唯一的一任女校長,年輕、漂亮,開朗、潑辣,能管得住一學校的老師和學生,經常能聽到她爽朗的笑聲。任校長的愛人叫歐陽寶清,是軍官,英俊、瀟灑,好像在福建某個機場駐防,老師們叫他「歐排長」,軍裝四個口袋,還佩了手槍。歐叔叔是我的偶像,我總盼著他回來。他大概每年回幾趟,給每家都帶了禮物。我見過歐叔叔在照相館拍的一張單人照,很酷,照片上題有一行他的手寫體名字。我一直納悶,那字是怎麽寫上去的。任校長後來調到了縣教育局工作,她的外甥女廖琴跟我同班,廖琴有個弟弟,跟我弟弟一般大。鄉村學校就是這樣,十裏八鄉的老師和家長大多熟識,許多老師之間、學生之間、師生之間是盤根錯節拐七拐八的關系,濃郁的友情、親情、師生情有利於互幫互助、彼此關愛,但成績要好、考上學校,還得憑學生自己努力。

家住牌坊盧家的盧赤宇老師,既教數理化,又教語文,性情超凡不俗,才華令人贊嘆。他的下巴上長有一粒黑痣。他不茍言笑,言辭犀利,很少聊天,旁人畏他三分。他寫得一手好字,曾經寫滿一黑板的粉筆字,是一首詩,後來我才知道,那是【紅樓夢】裏的【好了歌】。學校的黑板報由他主筆,有一期最底下一行錦句,讓我記了一輩子,那句話是「學習的敵人是自己的滿足」;童波靜老師家住鎖石嶺童家,她有一個兒子,但還有「第二個兒子」,是我的弟弟。有一天早晨,童老師來我家,撩開蚊帳幫我媽給我們穿衣服。三四歲的弟弟賴床不起,迷迷瞪瞪地以為是我媽,就喊了一聲「媽」,童老師答應了一聲,弟弟不好意思,童老師卻高興壞了,從此就讓我弟弟叫她做「媽」。這媽真沒白叫,她經常從自家帶菜給我們家,她家自制的腌菜尤其好吃;任民權老師家是月亮井任家的,教代數,經常寫一黑板的方程式式,討論起代數題來非常投入、專註、較真,有一次竟然不知不覺地把皮帶從腰間抽下來,叩打桌面,重一下輕一下的,眼睛卻始終不離桌上那道題,嚇得我們不敢喘氣兒;邊一山老師是城裏人,長得面大耳闊白白凈凈,他是從縣文工團下放到大田學校當老師的,是不是教音樂不記得了,但他的笛子吹得很好。他喜歡我弟弟,弟弟還沒上學,但心算很厲害,邊一山老師時不時地把我弟弟捉到跟前,兩腿一夾,加減乘除地出題,讓弟弟口答,弟弟的「母算家」外號就是他給起的。後來聽說邊一山老師落實政策返城,當到了市財政局局長;任海泉老師教語文,他的妹妹桃英、弟弟泉元跟我是同班同學,他們家住山坡下的老屋任家,我經常去玩兒,門對門,房挨房,進哪個門穿哪個廊、哪個是堂屋哪個是廚房,門兒清。任海泉老師後來考上廣西郵電學校,畢業分配到了縣裏的郵電局工作。離開學校多年後,見到過一次任泉元同學,他在家鄉做鋁合金門窗業務,說姐姐桃英已不在了好些年了,我聽了一陣傷感;陳金平老師教幾何,人長得帥氣,舉止有風度,穿翻毛皮靴,很洋氣。家住荊泉山裏,周末回家要走很長的山路。他曾給我的試卷打了一個滿分,還用紅筆字寫了很長一段鼓勵的話,我至今記得;劉凱華老師教數學,本是高井畈劉家的人,嫁到了月亮井任家,記得她是天生卷發,非常和藹熱情;劉東林老師教什麽課不記得了,但記得他家住在高井畈劉家,每天獨自沿水港走回家;杜林生老師是畈裏杜家的,他的父親是鄉間名中醫杜家少師傅,有祖傳土方,治疑難雜癥,很神秘、有口碑。杜老師教語文,是不多見的「老三屆」高中生,知識功底紮實。聽大人們說,他還響應計劃生育號召,做過結紮手術。不同的人走到了一起,每個人有不同的故事。這些老師本色、本分,樸實、樸素,像林間的一片葉,葉綠葉落任自由;像山裏的一條溪,枯豐人不知,喧默無人曉。但孩子們的成長缺不得他們,鄉村的風景裏少不了他們的顏色。

大田學校後來調來了劉紹先、黃國華夫婦,不記得他們教什麽課。他們家在校舍的最角落上,後門外是他家的菜地,永遠是郁郁蔥蔥地長滿瓜果菜蔬,經常分享給我家。他們有四個子女,兒子分別叫劉建平、劉愛平、劉永平,女兒叫劉衛平,最小的兒子永平比我大幾歲,我倆是同班同學,還是武術隊的拳友,散打、角力、棍術的老搭檔,經常比誰下腰動作快。據說永平在蒲紡工作過,不知道近況如何;我的二叔劉元先、二嬸龔益珍也住在學校,二嬸跟我的舅媽龔三元有親戚關系。二叔拉得一手好二胡,後來當了縣師範學校的校長。二嬸調到另外一所建在山頂上的小學去了,繼續當老師,繼續住學校。去二叔二嬸家有兩條山路,都要穿過茂密的山林。當年的二嬸年輕漂亮,聲音甜美,說話像唱歌。如今雖然老了,風韻猶在,愛好舞劍,手機微信玩得順溜,常在我們的「老劉家」群裏,發各種表情包。老兩口在城裏散步,常碰到昔日的學生,桃李滿縣城。
鄉村學校雖偏遠、規模小,學校之間教師的調動交流卻頻繁,這裏來去過不少老師,像教代數的童樹貞老師、塗立勛老師,當過海軍的項木清老師,後來去當了兵的體育老師項清明,學校當時還有唯一說武漢話的,是羅順芝老師,據說也回武漢了。
我的這些老師們,大多出身農家,家世寒微,沒有顯赫的背景,沒有富裕的家資,沒有過硬的學歷,也沒有見過太大的世面和受過足夠的禮遇,但他們是山村裏最有文化知識、最斯文,也是最有責任心、最具職業精神的一群人。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不圖報酬,只顧耕耘。從不奢求什麽,也不苛求別人。一批批的學生畢業,就像一茬茬稻谷在成熟,教完他們,再教他們的孩子,一代接一代。他們視講台為神壇,視教師職業為神聖,擇一業、終一生,竭力地發著光,像草叢間的螢火蟲;努力地燃燒著自己,像竈裏的火、爐中的炭,照亮山裏孩子們前路,溫暖了這個世界。

我的這些老師們,是富於理想、富有才華,卻也安於現狀、甘願忍受寂寞的一群人。他們大多是民辦教師,走下講台就是農民。有責任田要種,有工分要掙,幹體力活比不過身強力壯的男勞力,掙工分趕不上人多勢眾的大家庭。到了年底分紅少,有的老師家庭還要借錢抵物還超支款。村幹部說了,你們家今年超支,今天你得給我簽了這欠條,要不我拉走你們家的豬!遇到親戚朋友有婚喪嫁娶大事,本來收入就不高,還得送情隨禮湊份子,難免有些糾結;遇到左鄰右舍雞毛蒜皮的事,打不過,罵不過,難免斯文掃地。他們在精神與物質、理想與現實、使命與命運的漩渦裏,不斷地調適姿勢、調整心態,努力以最好的狀態面對這個世界。「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我親眼見過,不止一位老師在自己的日記本上抄寫過李商隱的這兩句詩。它是詩,更是誌。
我的這些老師們,雖然在學生面前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知無不言、傾其所知,但見到城裏人,卻有些靦腆甚至自卑;見到上級領導、幹部,想提學校的困難、自己的難處,卻難於啟齒,甚至面紅耳赤語無倫次。民辦轉公辦,是很多民辦教師的夢想,想給曾經是學生的鄉裏社群幹部送點兒什麽,一是沒什麽可送的,二也舍不下臉面。
只有回到三尺講台,往學生面前一站,一切都放下了。
放不下的,是兩個字:責任。
最在乎的,是兩個字:斯文。
他們或許在心裏默念,我本是高山。
他們都是張桂梅,是李桂梅、陳桂梅、童桂梅……是一張張泛黃的老照片。
老照片裏,他們是否依然桂香馥郁、梅綻霜雪,是否依然風景無邊、風光無限?
耳畔響起韓紅唱的【只要平凡】,「沒有神的光環,你我生而平凡」「此心此生無憾,生命的火已點燃」。
一份隱隱的傷感,升騰在我的心底,向鼻尖、眼角處彌漫。

四
是的,前面提到,我的母親在這裏當民辦教師,整整十年。
當時的學校師資不足,一些教師不得不教幾門課。母親從小學教到初中,教過語文、音樂、物理、化學,她教物理課時,編了關於磁力線「N極穿過手板心」的兒歌,很多學生會唱。我家有一台電子管收音機,是父親自己裝的。一開機紅綠發光管奇彩閃爍,節目不多卻熱鬧,孩子們常圍著看。村裏誰家有婚娶、添丁、孩子滿月等喜事,我家的收音機會被借去一用,成了喜事標配。母親總是既熱情又不放心,因為調諧器上的羊腸線被粗魯的手們扯斷了好些次,最後光聽旋鈕的軲轆聲和噪音了。
那一年,由於學校經費不足,老師們不得不自制課桌,不是用木材,而是用沙子、牛糞,摻和著水泥,砌泥磚課桌。母親和老師們成了泥瓦匠。有一天,一塊松動了的泥磚砸傷了母親的腳,傷得很重,送到了城裏醫院。一見到媽媽打著繃帶、拄著拐杖的樣子,我頓時哇哇地哭了。從那次起,媽媽落下了病根,有時傷痛復發,疼得走不了路。
貧瘠的土地,也會盛開美麗的花朵;蹇澀的生活,亦不乏生命的歡歌。和山裏孩子一樣,我的童年也有快樂和自得。五歲起,我就開始上學,母親教幾年級、哪個班,我就上幾年級、哪個班,稀裏糊塗懵裏懵懂地跟班讀,所以班裏同學大多比我大。母親下鄉時帶了一大箱書,是蘇聯小說,成了師生爭相借閱的讀物。後來才知道,那本被借閱最多、破損嚴重,我一直不知道名字的書,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讀過一本書叫【從鴿子谷來的孩子們】,長大後沒再見過。我曾在一篇小文裏提到這件事,沒想到收到各地素不相識的讀者寄來了十多本,有四位熱心讀者竟然跑到圖書館借了書,影印了寄給我,厚厚一大本,讓我感到沈甸甸的情誼。這些書不光是使我受益,也豐富了山裏孩子的文化生活。家裏辦了圖書角,同學們免費借閱,我也可以用書換書,甚至可以換彈弓、自制玩具火槍和小狗崽什麽的。那時的我,不知道什麽叫痛苦、磨難、貧困,一切天然,一切自然。

像張桂梅老師一樣,母親對學生,就像對自己的孩子。我清楚地記得,我的褲子經常被她拿給尿褲子的同學換上。有的學生家裏沒有米吃,母親就把米缸裏所剩不多的米,舀出大半升,裝進孩子的書包裏,囑咐回家交給大人。有個地質勘探隊駐紮在學校附近,子弟在大田學校借讀,兩年後移駐其他勘探點。撤走時,一位叫尹彩仙的女生跑回學校,抱著我媽,舍不得走,哭得像個淚人兒。
當時的鄉村學校沒有醫務室,學生有個頭疼腦熱的沒法看病,附近村莊的老百姓看病打針,得去幾裏外的黃家嘴診所。母親便自學了醫學知識,參加了赤腳醫生培訓,免費為師生和村裏人看病打針。我親眼見到母親嘗試著在自己身上打針、針灸,學會了再為村裏人服務。周邊村莊誰家有人生病了,來找我媽測個體溫、量個血壓、打個針,是常事。把註射針管針頭裝在醫用鋁盒裏,用紗布蒙上,蓋好了在熱水裏煮沸消毒,這是母親交給我的一個經常性任務。那時候的家裏,充滿醫用酒精的味道。量血壓的牛筋橡膠管,常被我悄悄拿出來做彈弓,因此沒少挨揍。老屋任家的幹芳爹,臥床好多年,母親風雨無阻地為他打了多年的針。為了表示感謝,幹芳爹的兒子用泥磚幫我家砌了一個小廚房。
那些年,那些村,母親給看過病、打過針、刮過痧的人,家家都有,不計其數。母親落實政策舉家返城時,父親所在的大學派一輛貨車來幫忙搬家,村裏人聞訊趕來送行,來了一群又一群,送了一程又一程。有的人家送一升米、一籃菜,有的人家用手絹兜幾個雞蛋。幹芳爹的兒子挑來一擔柴兜,說是城裏什麽都貴,燒這個柴兜烤火。我媽感動得淚水漣漣,這件事一連念了好些年。
回到故鄉,獨自在一些村裏轉,沒有人認識我,但只要說到母親陳老師的名字,自我介紹是「陳老師」的老大,就有人來打招呼了。
回蓮花塘和萬古堂,是母親最風光的事。車沿四通八達的村道開,任意停在一個村口,只要年邁的老母親一下車,一定有人圍上來喊「陳老師」,自報姓名,說是陳老師某某時期的學生,家住哪個村,叫什麽名字,我媽竟然還念得出一些人的名字,說得出一些人的故事。有的人順便對我說一句,「我是你的同學」「我抄過你的作業」。我端詳半天,好像沒有找到記憶的線頭。但母親的陶醉,令我陶醉了。
老師授業一陣子,學生受益一輩子。天底下最偉大的職業,是教師。母親的自豪,讓我執信這樣的理念。

五
小時候的我,也有自己的心事,只不愛說話。
前面提到,萬古堂小學有一位老工友,叫毛子嶽。
那年春節,母親領著我和弟弟妹妹,在武漢與父親團聚。正月初十,回到鄉下。
那年的雪,好大。下了火車,往大雪深處的家走去。砭骨雪風步步寒,鵝毛飛絮揚紛紛,雪暴一陣緊似一陣、密似一陣,大地上白茫茫一片。一家人深一腳淺一腳地在雪被裏尋著路。臉凍得沒了表情,雪水灌進靴裏,腳手都木了。
朦朧中見著了李家嶺上的兩棵大柏樹。翻過嶺,就是我們的家——萬古堂小學。
樹根下影影綽綽過來一行人。近了,隔著雪簾看去,雖然棉衣棉帽捂得緊,卻辨得出是月亮井任家的人。隨便問候了一句,一個男人說:「毛子嶽死了!」
啊,毛子嶽死了?一家人楞住了。
還沒進小學的大門,就聽見人聲嘈雜。
堂屋中央,停放了一口漆黑的棺材。有人說,毛子嶽已裝殮了。母親讓人掀開棺蓋,望了一眼,淚便簌簌地落了。
我家緊挨堂屋,四角漏風。淘氣的我曾把墻縫掏成一個杯口大的洞,往外看人。此時再從裏往外看,正是漆黑的棺材。我駭怕,挪過櫃子擋住那墻洞。擋不住的,卻是毛子嶽的影子。
黢黑的後山坡上是墓地,夏天有螢火蟲和「鬼火」忽閃,冬天有稀疏的墓燈,陰森瘆人。聽說有人鬼迷心竅,四處夜遊,一覺醒來竟躺在墳溝裏。誰家孩兒病了,做娘的便去「收嚇」——沿著漆黑的山路,喚著孩兒的乳名,喊「兒啊回來喲」,也叫收魂。每每聽到夜風中,傳來這淒慘的聲音,我早嚇得不敢吭聲了。也不知人家孩兒的魂,真的收回了沒。黑暗的屋角,偶爾竄過一只黑貓,常嚇人一跳。萬古堂小學像荒地曠野的一盞孤燈,被黑幕籠罩,四周遊蕩著鬼的故事。

好在有毛子嶽。毛子嶽是一位老人,寬厚的背,有些駝,下頜有顆豌豆大的痣。眉須濃黑,豎得像刺,像打鬼的鐘馗。很少說話,開口有湘音。在萬古堂小學負責種菜、餵豬、做飯。多大歲數,哪裏人氏,哪年來的,有沒有親人,沒有人知道。在萬古堂小學,他是我家唯一的鄰居。
毛子嶽為人和善,老師們喚他「毛師傅」,附近村民不論老少都直呼其名。有人來借米、借菜、借鹽、借洋火,往往是有借無還,他也不催人還。有人把豬和牛趕進菜園子,青菜被糟蹋一大片,他也只是摳塊土巴扔過去,再罵上一聲。村裏有婆娘怕走夜路,喊一聲「毛子嶽,你送我一腳」,他二話不說就跟在後面斷路。毛子嶽識草藥,滿山坡采集魚腥草、金銀花、七葉一枝花之類的熬藥,送人。還捉了蜈蚣、蛇什麽的制成藥吃。一旦中了毒,腿腫得像魚鰾。
經常有蛇溜進空場,或者纏在某棵蓖麻樹的根上,或者有蛇鉆進床角,我們總是驚慌失措地喊毛師傅來打蛇。毛子嶽的菜園很豐產,萵苣、韭菜、茄子、絲瓜、扁豆、南瓜,四季不斷,經常送到我家。家裏偶爾煨湯,母親總是盛出一碗,叫我端給毛子嶽。
毛子嶽似乎對我感興趣,偶爾跟我說些什麽,眼裏像有話,我似懂非懂。很少有人能進他的屋,但我是例外。我見過他寫毛筆字,寫在報紙上,報紙被他拿去燒竈引火了。見過他哭,好像是一張小孩的照片。我答應不告訴大人,這是我和他之間的秘密。有人戲謔他:「毛子嶽,你家堂客呢?」他很惱怒。兩個壯勞力到廚房裏搶他斫齊的柴,罵了他,他看了我一眼,一直不還嘴。我轉身走了,隨後聽到廚房裏動靜大起來了,那兩人慌慌張張邊跑出來邊叫喚,「毛子嶽是條瘋狗,咬我了,咬我了!」我聽了有些暗暗得意。那次,他送我們一家趕火車,走大田畈的田埂,我趴在他寬厚的背上,睡著了。
有天清早,聽得塘邊上一陣叫喊:「毛子嶽被人打了!」趕過去一看,毛子嶽一身泥水地躺在溝邊。原來是在淩晨分時,有人偷小學的豬,毛子嶽追出來,被賊打倒了。
春節到了,母親帶我們去武漢。臨行前對毛子嶽說:「我家就托付給您照看了,雖說沒值錢的東西。」從武漢回鄉下時,我爸媽還特地備了一份禮準備送毛子嶽。萬萬沒想到毛子嶽竟然說沒就沒了。
村裏人是正月初五拜跑年時,發現毛子嶽不在的。可能又是吃什麽中毒了,村裏人說,不知道我們一家這麽早回學校,棺材放我家隔壁不合適,要不找間教室放。母親說,不怕。
第二天,老師們和村裏人把毛子嶽熱熱鬧鬧送上了山。隱約聽大人議論說,從毛子嶽的木箱裏發現了什麽,有的說他是從湖南逃荒來的,有的說是從國民黨軍隊裏跑出來的。
飛飛揚揚的鵝毛大雪,掩去了那座,那座沒有花圈的新墳。
世間總有一些東西,值得珍藏。譬如,永遠不可復原的記憶,永遠難以報答的恩情。

全家搬到城裏後,回去的機會少了。教學資源調整,學生集中到了更好的學校,老師們分流到其他的學校,大田學校不復存在了。再往後,土地被征用,村莊被遷移,村路改道,池塘易容,舊校舍變成了被廢棄的蘑菇房,終成一片廢墟,早已是荒草齊腰、殘垣斑駁,一片雨打風吹的衰景罷了。
殘敗,也是一種風景,是讓人更加刻骨銘心的鄉愁。
我惦記的是,學校什麽時候解散的,老師們到哪裏去了,現在生活如何,是否都健旺?能否再相見,是否還記得當年我這個黑黑瘦瘦的頑皮孩子?
故鄉有萬千遊子,遊子只有一個故鄉。那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日子,融入了我的記憶、我的血脈。故鄉記不得遊子,遊子卻忘不得故鄉,我成了故鄉的客人了。思鄉的羽翼,常在夢裏振翅,從京城起飛,向著我的南方,我南方的故鄉,我故鄉的蓮花塘、萬古堂,飛去。
「我生來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於群峰之巔俯視平庸的溝壑。我生來就是人傑而非草芥,我站在偉人之肩藐視卑微的懦夫!」這是張桂梅老師教給學生的誓言,是天下老師對學生的期許。
我想說,老師是真正的高山。
沒有桂梅馨香,何來桃李芬芳。師恩如山,恩高義廣,情深誼長。春暉不以時過,銘恩不以境遷。
萬古堂作證。
(劉漢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