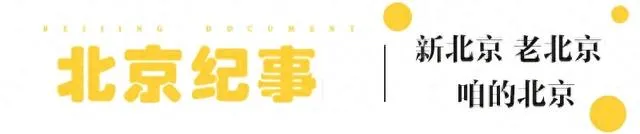

收藏圈的人如果不熟悉琉璃廠的前世今生那等於還沒入門,若是搞個書畫碑帖不清楚琉璃廠上「馬王爺」何許人也,說明段位還欠些火候。
筆者了解這位爺是早年跟史樹青和郭紀森兩位先生嘮嗑時所知,不久結識了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產計畫傳拓技藝代表性傳承人馬國慶先生,他出生在琉璃廠並在此度過了幼年、童年、少年、青年。細聊後得知先生正是「馬王爺」的幼子,衣缽傳承人。筆者雖然不能穿越時空與老先生相識,後來卻沒少從國慶先生那聽到有關「馬王爺」的「獨家爆料」,既窺聽書與畫的鑒定真經,又能光明正大地詢問老先生生前那些驚天動地的家國情懷。適逢琉璃廠改建恢復營業40周年,「馬王爺」逝世20周年,特書此文。
01
生於1911年的馬寶山曾用名馬保山,是從琉璃廠成長起來的書畫碑帖鑒賞大家。馬國慶憶文寫道:「父親可以說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他在無常的環境中為祖國和民族做出了不平凡的事。」這些不平凡的事足以構成馬寶山先生一生的傳奇,以至於在整個琉璃廠甚至古玩行都知曉馬寶山有「馬王爺‘三只眼’」之稱。筆者了解後認為,馬寶山的確具有馬王爺的特征,即專心、忠心、愛心,明辨的不僅僅是書畫碑帖的真假,更有人間的是非善惡。
河北省衡水縣南謝漳村(現衡水市桃城區南謝漳村)是馬寶山的出生地,他從小喜愛畫畫,7歲時進村私塾讀書。「我爺爺見我父親是塊料兒,在他16歲時經他堂叔馬金力介紹,來到琉璃廠的墨寶齋學徒。」馬國慶道出了父親來琉璃廠的契機。

馬寶山與師兄弟在琉璃廠留影,左一為馬寶山
舊時傳拓技藝植根於北京琉璃廠,且以「墨寶齋」和「古光閣」兩家店鋪最為擅長,被稱之為「金石兩大家」。馬國慶說,前者側重於石,後者側重於金,其他從業者都是這兩家師徒關系的分支。歷代皇家禦拓的國寶【三希堂法帖】即由「墨寶齋」應召傳拓和裝裱。店鋪掌櫃侯榮齋是清代末年的北京遠郊人,在京城繼承祖業以經營碑石傳拓裝裱為主。經過三年零一節的學徒,馬寶山才開始正式接觸業務,因為學徒期主要是搞衛生做雜務,伺候掌櫃的,還要恭維著師兄,若想學東西只能靠晚上或偷學。學徒期間所學裝裱、捶拓,記碑帖名,辨別原拓和翻刻,幾乎都是幹完一天的活兒後利用晚上所學。
碑帖的傳拓與裝裱是門技藝,馬寶山在墨寶齋勤學苦練已經掌握了,但碑帖的真偽、好壞鑒定卻又是另一門學問,侯掌櫃看不明白。馬寶山又尋覓機會到街上的敬文齋拜了善於精鑒碑帖字畫的掌櫃蘇提莆為師,出師後又拜了大學者、金石學家羅振玉先生為師。
墨寶齋由於掌櫃成天遊手好閑,最終因債主逼債不得已把兩間門臉房抵了債,夥計們被遣回老家。已經掌握了字畫裝裱與鑒賞的馬寶山,即便是回到老家也沒閑著,竟慧眼花6塊大洋從鄰村一位老太太手裏收了一件【白雁雙梅圖】,他反復觀察確定此畫出自明代四大畫家之一文徵明之手,後被徐石雪開價200大洋。
這事讓侯掌櫃對馬寶山是另眼看待。其實在他遣散店裏夥計時,其師兄穆蟠忱就曾對他說,馬寶山是個難得的人才,散誰都成就是不能讓他走,要保住墨寶齋這塊匾,非得把他請回不可。
馬寶山重回琉璃廠接手墨寶齋,時年20歲。很快召回了兩個師兄,白天同他們一起裝裱碑帖拓片,晚上仍就挑燈夜戰學習碑帖字畫鑒定,有時天不亮還會跑到曉市去淘寶撿漏。
02
從此,馬寶山成了琉璃廠最年輕的掌櫃。
盡管馬寶山當了新掌櫃,但資歷尚淺,加上鋪子縮小,參加京城的一些大型買賣活動略顯資格不夠,比如「封貨」,這是攛貨場的一種主要的買賣方式,就是看上一件玩意兒,人們分別寫張小紙條藏在器物下方,賣主當眾拆開,誰給的價高,東西就歸誰。攛貨場是行業內的交易場所,沒點身份的人進不去。非常器重馬寶山的琉璃廠古玩行商會會長孫耀庭對他說:「你要想試試水,我帶你進去。」
果然,馬寶山第一次進去「封貨」就露了臉兒。
【書畫碑帖見聞錄】 馬寶山 1997年 北京燕山出版社
那天,賣家要出手的全是碑帖拓本。馬國慶介紹說,在古玩行中,碑帖拓片的真偽很難辨識,真本偽本長相都差不太多,基本一個樣。偽本行話叫「贗品」,就是照著真品仿制,也有透過作假手段把晚期版本變成早期的版本。還有用移花接木的手法,題跋是真的,正文拓本是假的。凡此種種都為謀得暴利,有許多商家若買錯一本,即刻傾家蕩產。因此,古玩行內稱碑帖為「黑老虎」。常讓內行人一不小心就「打眼」——買了假貨,這不僅經濟上受損,名譽掃地更為可怕。
眼瞅著這一堆堆、一摞摞成本成堆的拓片,難免讓人會眼花繚亂。馬寶山雖然年輕,但眼很尖,在眾多拓片之中,一眼看中了其中的一本王羲之【聖教序】。「他沒資格在前面翻看拓本,因為在前面慢慢翻看的都是有名望的長者,就在這些人的後面看,別人是一本一本地看,他是一眼掃三五人手中的拓本。當大家都看好‘封貨’之後,他最後一個也把寫好的條子遞了過去,把身上僅有的35塊大洋全部押了上去。」馬國慶很形象地描述著父親第一次「封貨」的情景。
由於馬寶山出價最高,「封」到這本字帖。「小夥子,沒見你上手,就敢出大價錢呀?」這位賣家當著眾人問馬寶山,正當納悶地等待回復時,馬寶山只是沖他淡淡地一笑,麻溜地把這本貼文放入包中。「因為他斷定這是南宋拓的王羲之【聖教序】,高高興興地出了攛貨場。」馬國慶說,不久這件拓本被一位譚姓先生以350塊大洋買下。
沒過多久,馬寶山又陪琉璃廠英古齋七十多歲的賈掌櫃到西單宏兆當鋪看「死當貨」,這次花了20多塊大洋買下了幾本碑帖,其中一本是翁同龢舊藏北宋拓【聖教序】,後以600塊大洋成交售給某銀行經理。
馬寶山慧眼識碑帖撿大漏,一而再,再而三,使他在琉璃廠的名聲大漲,琉璃廠的同行們喊出了「馬王爺三只眼」。從此,馬寶山的墨寶齋擴大業務,擴招夥計,擴張門店。他也成為北平古玩業同業公會最年輕的理事。
03
俗話說「不給你點厲害看看,你都不知道馬王爺長幾只眼」。如果說馬王爺豎著長的第三只眼是玉皇大帝所賜,那麽馬寶山的第三只眼則是憑借著勤學苦練自己「長」出來的。他在書畫碑帖面前目光如炬,不但一眼能辨贗真,且在善惡面前同樣是人見人怕,人見人敬,不好惹。

【琉璃廠原貌圖】馬寶山畫
馬寶山站穩了琉璃廠,叫響了古玩行,但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生意驟然蕭條。有的人為了生計竟把收上來的重器(國寶)賣給了外國人,對其恨之入骨的馬寶山告誡徒弟們,好東西一件都不許拿出來讓洋人看,多少錢都不許賣給他們。馬寶山不僅不把國寶售賣給洋人,還經手搶救收購和轉藏了大量名貴字畫。馬國慶認為,父親一生最露臉的當屬搶救長春小白樓的珍貴名字畫,這其中又以挽救隋代展子虔【遊春圖】影響巨大。馬寶山在自己的著作【書畫碑帖見聞錄】的開篇中寫道:「長春偽滿帝宮小白樓事件,是中國遺世歷代法書名畫的最大一次浩劫。」
「長春小白樓」在書畫文物界大名鼎鼎,這是末代皇帝溥儀散佚國寶的藏身之所。1945年日本戰敗後,溥儀等人逃離時篩選出一些帶走,其余被偽軍哄搶一空,有的被埋在地下因受潮爛作一堆廢紙,也有的被低廉賣給古玩商開始大量流散。

小白樓
小白樓國寶被搶很快就傳到了千裏之外的北平。一些琉璃廠的古玩商紛紛前往長春,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北平圖書館趙萬裏更是心急如焚,他們找到馬寶山。
「你知道嗎?」
「看到報紙了,很是擔心。琉璃廠已經有兩撥人前往去了長春。」
「有何打算?」
「現家中有事,一時走不開。收購需要大量資金,現在沒有計劃去。」
「我們相信您的眼力,更了解您的為人,我二人來的目的就是煩您跑一趟。只要認為是有價值的,就想辦法為我們收上來,錢不夠,我們給您做後盾,我們希望您早日動身。」
「你們的意思我明白了,有您二位這麽說,我心裏也有了底兒,我立馬準備。」
以上是馬衡、趙萬裏同馬寶山的一段對話。行事一向雷厲風行的馬寶山帶上行李坐火車直奔長春。到了長春,他了解過情況後做出了一個決定:趕到報館登報,代表北平故宮博物院高價回購偽帝宮流出的字畫。
登報後,出售字畫古籍的人多起來,古玩商也紛紛來長春搶購,一時洛陽紙貴,價格飛漲。那些埋入地下的字畫也帶著傷痕和土氣味出現了。
馬寶山的明智之舉讓一批珍寶擺脫了厄運。但隨著大量字畫的收購,資金越發緊張起來。情急之下,馬寶山向銀號借高利貸,采取速買速賣的方法,並與收藏家約法三章:「這些國寶必須自己收藏,如果出讓,絕不能賣給外國人。」馬寶山在【搶救已佚書畫概況】一文中稱:「經手了三十多件名貴字畫,如晉顧愷之【洛神圖】、隋展子虔【遊春圖】、唐杜牧【張好好詩】、元朱德潤【秀野軒圖】等,有的賣給了故宮,有的轉給了收藏家或同行,但沒有一件珍品流出國外。」

展子虔【遊春圖】
這其中以隋展子虔【遊春圖】最為重要。據悉,展子虔是經歷了北齊、北周、隋三朝的著名畫家,創立了中國畫山水畫科,所畫【遊春圖】在宋代就入了宣和內府,並有宋徽宗趙佶的題簽,後又經歷代名家收藏,且完好無失真。該畫在中國歷史上有著重要地位,也是現存最古老的一幅山水名作。
當年,馬寶山到長春時,他的師大爺穆蟠忱早到了一步,與琉璃廠的馬霽川、馮堪如三人用很低的價格,從當地人手裏「夥買」了這幅名畫,帶回了北京放在馬霽川手裏。
張伯駒得知【遊春圖】下落後,極想把它收藏下來,但與馬霽川不識,便托寶古齋的邱振生幫忙協商,馬霽川索價800兩赤金,即港條。這對於張伯駒而言是個天文數位。無奈之下,張伯駒又轉請馬寶山出面幫忙。馬寶山非常欽佩張伯駒的愛國熱情,便慨允全力促成。
二馬雖是同行,又同屬古玩商會理事,盡管在琉璃廠一條街上擡頭不見低頭見,但從未有過業務往來,若直接找馬霽川多半會碰釘子,於是便找來自己的至交李卓卿,李在琉璃廠同行中很有威信。李與馬霽川初談的結果是,因有洋人要出黃金800兩,告知張如出此價可以給他。幾次商談未果後,馬寶山隨同李一起去找馬霽川,說:「常言道撿來的黃金隨市價合理,但是,這件東西不同一般,是國寶中的國寶,如果你為了厚利賣給了洋人,不管日後誰當政(當時國共兩黨在交戰),落下個國難當頭變賣國寶的罪名,你是跑不掉的,請兄三思。」同時,張伯駒也將【遊春圖】要賣給洋人的訊息到處宣揚。在這種情況下,繼續與馬霽川商談,他才吐口決定以200兩黃金的價格賣給張伯駒,須一手交錢,一手交畫,不可拖欠。
盡管降到200兩,張伯駒也不是一兩日就能湊出來的。
這時張大千聞訊來到馬寶山家,說:「聽說【遊春圖】由800兩港條降為200兩了,有人願出200兩赤金一次交付,40兩禮金送你算是幫忙費。」馬寶山說:「你發大財了?」張大千說:「受老鄉張群(國民黨行政院院長)之托,求讓【遊春圖】。」馬寶山說:「張伯駒正在籌款買下【遊春圖】,只是款項大些還要再等些時日。你同張伯駒先生也是好朋友,這樣辦不妥吧。再說他們(國民黨)把大批文物都轉去台灣了,這件還是應該留在這邊為好嗎!」
這時張伯駒為了籌巨款竟把自己的一套大四合院賣了。這一天,張伯駒帶著200兩黃金,馬霽川帶著【遊春圖】,李卓卿帶著一位鑒定黃金成色的師傅,如約來到馬寶山家。當場,透過檢驗黃金成色六成多,合計130兩。馬寶山又從中撮合說:「大家看這樣成否?130兩你們先收下,余下的張大爺陸續補足,【遊春圖】交給張大爺帶走,我來作保人,如何?」雙方同意後做了交換。張伯駒拿到畫後,馬寶山才算是松了一口氣,總算把這幅國寶中的國寶留在了這方土地上。日後,張伯駒又補了約40兩黃金,仍欠著30兩。
此時,解放軍和平解放了北京,張伯駒將【遊春圖】與其他一批國寶級文物捐獻給了故宮博物院。
04
新中國成立後,馬寶山繼續為國家搶救和鑒定文物。「公私合營」時,馬寶山被安排在琉璃廠西街的北京市文物商店慶雲堂碑帖門市部,「文革」後期曾為第一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展」上的部份文物進行傳拓。「文革」結束後,馬寶山作為北京市文物局文物管理處聘請的骨幹力量,從事碑帖字畫鑒定工作,時年已近60歲。
馬國慶說:「當時有整車整車的書畫、碑帖、古籍被當成廢紙拉到通州一個造紙廠化為紙漿。父親看到這種情況後痛心不已,就從一座一座書山中攀抓著、挑選著,還千叮嚀萬囑咐那些工人,只要看見紙變色的字畫、碑帖、書籍請手下留情,都挑出來讓我看一眼,再往化紙爐裏送。一次,一位姓徐的師傅推來一平板車古籍和字畫,我父親讓他停下來,就從這車準備化為紙漿的‘爛紙’中,扒拉出唐代【經書】五卷,其中就包括唐閻立本手書的【蓮花經】,後來被故宮博物院收藏。」
晚年的馬寶山被聘為首都博物館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每天顧不上吃飯睡覺,一門心思就是憑著自己的眼力和超強的體力與毅力多去搶救那些失之交臂的文物。

說到父親的成功以及成名,馬國慶說,包括父親在內的琉璃廠人了解行情,見多識廣,做學問的學士教授們大多是從書本中得來的學問,琉璃廠人則是真金白銀的在買賣實踐中積累,再加上讀書做學問、勤思考、善學習,所以在文人眼中,他們不僅是商人,而且是朋友、學者先生。你沒見過的物件兒,他們見過,你只知道真,琉璃廠人還知道真的大概存世數量、都在什麽地方。更知道假,是什麽地方造的假。
2004年3月6日傍晚,馬寶山安詳地走完94歲的一生。馬國慶飽含熱淚地說:「父親從事文物事業達80年,生活一向很規律,走的頭天晚上卻跟我聊得很晚才睡,從學徒到接手墨寶齋當掌櫃,從抗日戰爭時期做地下工作到搶救小白樓珍稀字畫。從他表情和語氣中能夠得知他最自豪的事,是在國難當頭之時,沒讓一件寶物從眼皮底下溜走,對此他所承受的壓力和委屈卻像講故事一樣,無怨無悔。」
馬寶山的一生,名不虛傳,是名副其實的「馬王爺三只眼」。
作者 ✎ 劉仝保
【文章來源:【北京紀事】10月刊】












